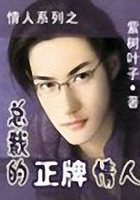二萧与裴馨园
黄淑英 口述 萧 耕 整理
1932年的时候我家正住在哈尔滨。那时我大约有二十二三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丈夫裴馨园比我大十四岁,是一个很文静的,沉默寡言的人,他个头儿不高,体格也不大好,很瘦弱。平日他是忙忙碌碌地去上班,回到家里,就一头扎在他的书房里写东西、翻报纸、看稿件、校样……因为我是个家庭妇女,没念过几年书,在家里的地位虽然是主妇,但是一切“内政”和“外交”都是由丈夫和他的一个管事人来操办的,就连孩子们的日常用品,也都是由丈夫亲自买来交给我的。我也没有什么亲戚或朋友,所以也很少出门儿,对外界的事儿也就知道得很少,就连我们家住的属于哪道街,街名儿叫什么,也弄不清。
丈夫当时的职业是什么呢?我只知道他是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同时还兼任《五日画报社》等报纸的编务。《国际协报》是属于商办性质的报纸,每天出一张,共四版,文艺副刊占据了第四版二分之一的版面。在这副刊版的版头,我丈夫用“老斐”作笔名,开设了一个“老斐语”专栏,他几乎是每天都要用这块“老斐语”的专栏,写上三五百字的杂感或散文,用比较隐晦的语言来揭露、讽刺当时黑暗社会的弊病;表达在日寇铁蹄下人民的痛苦心声;失学失业青年的苦闷;评论评论国际上发生的新闻、丑闻……有的时候,与哪家报纸发生了矛盾,他也用这个专栏来打“笔仗”。
他很喜欢安静,他的书房平日是任何人不许随便进的,孩子们总是躲得远远的。他有个习惯,就是爱在床上、桌上、凳上……到处都堆放着书、报、稿件、校样……我每天去给他收拾房间,整理床铺的时候,就爱随手翻看翻看他那些书报稿件之类,他用“老斐语”专栏与别的报纸打“笔仗”,我就是这样看到的。因为我对《国际协报》文艺副刊也很感兴趣,所以就很留心读那上面所刊载的文艺作品,许多后来成名的文艺作家的初期作品,我也是在这个时期读到的。
每天一到下午,就陆陆续续地有读者、朋友和同事来找他了,这个时候是他在家“办公”的时间,就是我,他也是不欢迎去打搅他的,把房门紧紧地关着,很是繁忙……
记得在他接手编辑《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版时,他曾向报社提出过一个条件:“如果让我负责主编,就不许可任何人来干涉我,也不受任何检查。”(当时其他报纸的稿件是要经过满洲特务机关检查的)所以,这个副刊的选用稿件就都是由我丈夫很仔细地一篇篇地亲自过目,不管有多忙,他也必须亲自看校样,一校,二校地看……对一些爱国的、有民族自尊心的、有才华的、能反映时代风貌的青年作者的作品,他也总是尽力给他们以发表的机会。
一天,我见他拿着一份读者投稿在那里反反复复地看,还不住地表现出赞许的样子,显得很高兴。我便问他是什么高兴的事,他说:
“我发现了个人才。”还不住嘴地夸赞这个投稿者“有才华啊,有前途!……”
“你认识这个人吗?”我问。
“不认识。”他说。
“你既然喜欢他,为啥不把他找到家里来见见面呢?”我说。丈夫很同意我的建议,一天,他便把那个“有才华”的投稿者请到了家里来,他叫——三郎——也就是后来的作家萧军。(据萧军说他在《国际协报》副刊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名为《飘落的樱花》——耘注)
初见到三郎的那时期,我们家人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首先从他的穿着来看:记得他当时穿着一件蓝色不蓝,灰色不灰,被阳光晒褪了色的粗布学生装,领口、袖口、肩、肘等处凡是容易磨损的地方,都露出了断布丝的毛茬儿;下身穿的是一条西式灰色裤子,不但没有笔直的裤线,而且还补着补丁;脚上穿着一双开了绽的沾满了泥迹的旧皮鞋;一头不加修饰的自由生长着的直直竖立着的寸发,很黑也很浓……生活显然是不富裕的,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五官轮廓很分明;体格虽然比较瘦但样子还精神,结实,个子不高,是个中等身量的人。他也从来不讲什么“客套”,也不和人寒暄,总是来了就直奔老斐的书房,一谈就好半天,谈完了,手里拿些什么稿件或书籍抬腿就走了,第二次来了,仍然如此。所以家人们背后议论说:“看不出三郎是个吃墨水的……可裴先生可是斯斯文文的……”
只有我丈夫老斐是很看重三郎的。他认为三郎是个质朴的人,有才能的人,他不但请三郎帮他整理稿件,校对校样,最后《国际协报》文艺副刊就索性让三郎来选稿、编辑,代他去跑印刷厂,联系一切难于办理的事务……老斐就只签签名,或看看报纸的版面安排就又忙于其他报刊的编辑事务去了,他对三郎的工作,是完全信任的。
时间长了,接触了解的多了,三郎以他那特有的坦率、真诚的性格改变了别人对他的议论,逐渐地成为了我们家毫不拘束的常客。又因为他那热忱、直爽、淳朴、不怕吃苦受累的品格使他与印刷厂的工友弟兄们很快地就成了朋友,他们都不把他当外人,看成是自己人,因此每次跑印刷厂的任务三郎都能完成得又快又好。老斐就时常背地里在我面前夸奖他说:“三郎不但文章写得好,人缘儿也好啊。”有的时候他两人一谈就谈到深夜一两点钟,天太晚了,他就留三郎住在我们家里,后来干脆就请三郎搬来我家住了。经常看见他们在那里谈得兴致勃勃的没结没完的。
以前老斐的书房总是静悄悄的有人似没人,来了客人谈话也是低声细语的。自从认识了三郎之后,他的书房可是热闹了起来,不但能时时听到他们大声地在谈论在笑,而且还经常有一些进步青年朋友来聚会,三郎有时高兴起来,还要拿起他那把挂在墙上的宝剑练一趟,或者放开嗓门唱一段儿他最喜欢的京剧《打渔杀家》呢!这个时候我要进去凑一凑热闹,听他们说古道今的,我丈夫是绝不阻止的。听他们提到过黑人(舒群),也知道有一个翻译俄国小说的金人,但是这两个人来没来过我们家,长得什么样儿,我是一点儿也记不得了。还听他们讲起过一位朋友,被日本人抓去了,他从狱里逃了出来,但是因为他没有穿鞋,又被日本人抓住了……(当时被抓去的犯人,一进狱,日本人就没收了他们的鞋,市面上的鞋店,也不卖鞋给光着脚的人。)这个人是谁呢?生死如何?我都记不清了。
在三郎等诸位青年朋友们的大力协助之下,《国际协报》文艺副刊越办越生动,越加活泼起来,在整个东三省的报界来说,这个副刊也是很受读者欢迎的,确实起到了它一定的进步作用。
“你就大着胆子办吧!”大家鼓励我丈夫说。
“有了你们,我就不怕,只要你们敢写,我就敢登!”老斐的劲头更足了。后来又编辑了《儿童专刊》和《新年特刊》也同样受到了读者的关心和喜爱。在这个时期里由于老斐对青年朋友们的真诚的信任,他用了自己的最大努力给予这些进步的青年作者们开辟了文艺斗争和习作的阵地,像后来有成就的作家萧军和萧红(三郎和悄吟)等人,就都是在这《国际协报》副刊上发表了许多篇练习的初期作品之后,开始正式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的。(还有作家山丁、金剑啸、罗烽、白朗、舒群、金人等——耘注)
大约是在松花江发大水之前,1932年的夏天,我丈夫告诉我说他收到了一个女读者的来信,在这信里这个女读者似乎是指责了老斐,并写了“我们都是中国人”等样的话,老斐觉得很有趣,一边笑一边说:“在中国人里,还没碰见过敢于质问我的人呢!这个女的还真是个有胆子的人!”后来又听说这个女人因为欠了旅馆很多的债,被困在了旅馆里……这就是后来的作家悄吟(萧红)。
老斐把信交给三郎看过之后大声地说:“我们要管,我们要帮助她。”我只知道三郎去看望悄吟了,怎么去的?我记不清了。(据萧军说是由老斐写了封“介绍信”,并带上了几册悄吟要借的文艺书籍于7月12日去道外正阳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二楼,一间放杂物的、发着霉气的房间里看到悄吟的。她当时处境很危险,因为欠了旅馆六百多元的债,旅馆蓄意将她卖到妓院。——耘注)
就在我们商量着如何救出悄吟的时候,松花江水暴涨了,哈尔滨道外一片汪洋,人们要乘摆渡才能通行。想起了被困在道外旅馆中的悄吟,大家很焦急。三郎说他自己会游水,也能爬高,身体也结实,能把悄吟救出来……于是就同意由他带着香肠和面包赶忙游水到悄吟那里去了。当天,当悄吟到我家来了一些时候了三郎才赶了回来。(据萧军说当他游水到旅馆时,悄吟已搭乘一条柴船按照萧军前几天留给她的老斐家的住址先走了。——耘注)由三郎介绍着,悄吟与我们大家一一相识了,我们也像对待老朋友一样热情招呼着悄吟一起吃晚饭……悄吟当时穿着一件旧蓝布旗袍,脸色苍白,神情也显得有些紧张,光着脚穿着一双半旧的鞋。也许是彼此生疏的缘故吧,她不太爱讲话。当晚,便安顿她在我家客厅住下了,老斐一再嘱咐家人说:“不要去打搅她,让她安心休息……”所以我也就很少去客厅,也没和悄吟在一起单独地长时间地谈过话。这时三郎几乎每天都来看望她,看样子两个人很谈得来,三郎一走,悄吟就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捧着本书在那里读,甚至一天一天的也不出房门外去走动走动,也不太愿意主动和别人讲话或打招呼。天长日久,我家里人(除了老斐)就经常在我的耳朵边上嘀嘀咕咕地说悄吟孤傲、不通人情世故,甚至还埋怨我说:“真是没事儿找事儿,让这样一个人住在家里,吃在家里……”(当时悄吟正怀着孕)因为我太年轻了,太幼稚,听了这些煽动性的话之后也没仔细地想一想,对悄吟也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就在悄吟从医院分娩回来后不久,忘记为了一件什么事,(好像是我在三郎面前说了悄吟的闲话)说着说着就与三郎争吵了起来。年轻的三郎脾气是很火暴而执拗的,我年轻时口头也很是不服输,俗语讲:“骂架没好口,打架没好手”,越吵越凶,就这样彼此伤了和气,第二天吧,三郎就带着悄吟离开了我们家……事情过后我也时常后悔,但是已经如此了,也无可挽回了,所以至今我还记得这件事。自从这次争吵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悄吟,有时在副刊上倒是经常看到她发表的文章,觉得她确是位很有才气的人,我丈夫也经常说她有才华,并说她和三郎是“一对流浪儿,还满对脾气的呢!”
三郎虽然仍像往常一样与我家常来常往,只是因为感情上有了隔阂,他只是与我丈夫谈论稿件和出版的事务,并不与我打招呼,我也赌气地想:“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就这样彼此僵持了一段时间。一天,我丈夫提议带着孩子们到野外去玩一玩,同时又邀了几位平日经常来往的好朋友同去。当我们走到一个大水槽附近的时候,别人都从临时搭起的独木桥上迅速地走了过去,丈夫也带着孩子们走过去了,我看着那悠悠颤颤的独木板儿桥,心里真有些发慌不敢前往。这时只听我丈夫在对面喊着:“三郎,快把你嫂子扶过来。”(其实三郎还比我大二三岁呢!)我一回头,才看见三郎默默不语地正站在我的身后,听见了老斐的喊声,三郎便快走了几步到我前面,侧过身来,伸过手将我扶过桥去,从那天以后,我们便和好了。
虽然三郎和悄吟搬到外边去住了,我丈夫还是经常地关心着他们,帮助着他们。他觉得从三郎身上可以得到一种鼓舞人的力量,办起事来就不发愁,信心足,有三郎在身边儿心里就踏实了许多,没有犯难的事……所以他几乎是时刻离不开三郎,总是叨念他,提起他,大事小事都要和他商量商量。到了1934年的夏天,听说三郎夫妻要离开哈尔滨了,几天来我丈夫的心情都很低沉。我问他:
“三郎他们要到哪儿去?”
“准备到上海。”他说。
“干什么?”我问。
“去见鲁迅先生。”
“你身边儿既然离不开他,为什么不留留他呢?”
“那怎么行呢,他们有他们的前程啊……”丈夫无可奈何地感慨地叹了口气,就再也不说话了,独自回到他的书房里……三郎他们的路费据说是朋友帮助凑齐的,什么时候从哈尔滨动身的我就不知道了。
1935年三郎的《八月的乡村》和悄吟的《生死场》出版了,我丈夫高兴地说:“总算看到他们开花结果了……要是能见见面有多好。”此时他的写作热情也似乎随着三郎他们的南去而逐渐消失了,他越来越懒于动笔,身体也越来越衰弱,后来又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终于离开了哈尔滨到了北京。
记得他曾收到过三郎写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他不知道读了多少回,并把它小心地放在自己随身带着的钱夹子里。一天不小心让小偷把钱夹掏了去,为了能寻回这封信,他特意花钱请了一次客,请诸位到场的警方人员千万帮他找回这封信。一直到1957年裴馨园去世之前,他都念念不忘当年《国际协报》投稿的那些朋友,特别是三郎。老斐没能够再见他一面,这是他最感到惋惜的事。
1979年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召开了,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萧军(三郎)的名字,心里很高兴,很想去看望他,可是又顾虑重重,怕他不愿意接待我。几十年不见了,彼此生疏了,我的丈夫老斐去世了,四个孩子也都死掉了,只剩下我这个孤零零的老太婆,谁还会记起我呢……我的一位老朋友很理解我的处境和感情,她一再热情地动员我给萧军写封信,也许萧军能回信呢?就在我发信后的第三天下午,我刚刚走进院子的大门,就有邻居的孩子告诉说有二位来客在等我。这时只见一位头发花白、面色红润、体格很壮实的老人在那里低着头用笔正在写着什么。他听见我回来的声音,立刻就走到我的面前,乐呵呵地说:
“你不认识我了?我正要留个条子给你。”
“不认识了……也不敢认了。”我确实认不出这位胖墩墩声音透亮的老人是谁?
“我是萧军,这是我的女儿萧耘。”
“啊……”我因为一时心情太紧张了,也不知说什么好了,脑子也一下子乱了起来,手也抖起来了,开了几次才把门锁打开请他们进到屋里,想说些什么呢?我万万也没有想到萧军接到我写的信当天竟冒着那么热的暑气来看我,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尊重友谊的人。
临走的时候,他告诉我生活上如有些什么困难不要发愁,只管写信给他,不要客气……我说:“我什么也不用你担心,我今天能见你一面也就知足了,老裴临去世之前还在叨念你,今天总算代他了结了这份心愿。”
选自《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四辑,1982年
“牵牛房”忆旧
袁时洁
作者介绍:袁时洁同志是黑龙江省爱辉县人,少年丧父,稍长考入哈尔滨女一中附属师范学校。后与黄之明结婚,新居之室谓之“牵牛房”。1937年她只身投奔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在抗日军政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工作,后到白区工作。解放后一直在北京民航总局工作。
“……奇她们已经安定下来了吧?两三年的工夫,就都兵慌马乱起来了,牵牛房的那些朋友们,都东流西散了。”这是萧红1936年11月2日由日本东京寄给上海三郎信中的一段话。信中的“奇”,就是指的我。我当时名淑奇。时光流去四十多年,现在,由我来回顾“牵牛房”那段令人难忘的往事。
“牵牛房”的主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沈阳,当年年底进入哈尔滨。当时我是哈尔滨女一中附属师范的学生。“九一八”的炮声促成我与爱人黄之明结了婚,住在哈尔滨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的一个大院内。大院的深处有木工作坊和一些职工家属宿舍,我们家靠近大院大门附近。房子宽大,窗门向南,屋内客厅、住室、书房、厨房、厕所等俱全。我同老黄住客厅的西面,隔成两间的寝室里。客厅的正南面有两个大窗户,窗户中间放着一个大写字台,上面放些文房四宝,多是画具等。客厅的正中央安放着一张方桌,桌面上铺盖着和室内颜色调和的带深浅方格子花纹漆布,桌子四周放有六七把椅子。这所房子正面的门窗迎着过往出入大院的人们,我们感到这对来往的朋友们聚会的时候很不方便,我们就在窗前种了许多牵牛花,这样一来,我们的房舍不仅装饰得美观,也达到了可以遮挡过往行人向室内张望的视线。
牵牛花盛开了。一天,老黄下班回家,看着粉白色、红白色和紫里衬白的牵牛花,爬满了所有的窗子和风斗门,老黄兴致勃勃地建议:“把我们这个房子叫‘牵牛房’吧!”大家听了,高兴地拍着手说:“好哇好哇,对啦,你就当这房子的老黄牛。”老黄听了美滋滋地笑着:“这个命名我倒满意。”后来,凡是来我们家串门的或聚会的朋友们,都得了沾“牛”字儿的外号,如“胖牛”,“瘦牛”,“傻牛”等等。“牵牛房”就成为当时有进步倾向的青年们聚会和活动的地方。
“牵牛房”的客人
来“牵牛房”的人们,有作家、有诗人、有画家、有职员、有教师和学生等。
常聚在“牵牛房”的人们,起码都具有着爱国主义思想,有着希望中国共产党将来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一个革命的新社会的向往,渴望着中国共产党迅速唤起全国人民觉悟起来抗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大家都明白,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彻底翻身做主人的日子的出现。在“牵牛房”里,有的实际就做着秘密抗日工作,宣传着共产党领导“东山里”抗日游击队的胜利,宣传着抗日游击队的胜利消息,主要是工人和学生援助抗日和参加抗日的消息,宣传着中国共产党反围剿胜利的消息。
当时,来“牵牛房”的三郎(萧军)和悄吟(萧红),算是“职业作家”。他俩在物质生活上是一贫如洗,常常饿着肚子。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下,萧军的名字上了黑名册,但仍秘密地写着《八月的乡村》;萧红写着《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等小说,稿酬微薄,他俩顽强地、不懈劲地向恶劣环境搏斗,大家称他们是硬骨头。常来“牵牛房”的朋友,还有白朗、罗烽、舒群等。这些人,是我的启蒙老师,又是一起学俄文的同学。当时我的年龄是17岁,萧红给我起名叫“小蒙古”。我思想是简单的,头脑是单纯的,唯独接触了这些老师,我学习不少革命道理,并阅读了他们带来的不少进步书刊,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祝福》、高尔基的《母亲》、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等等。悄吟对我说:“一个女人要想翻身,必须自己站起来,参与革命事业,不给男人当‘文明棍’,不给男人当‘巴儿狗’。”由于“牵牛房”的朋友们的启迪和影响,使我这个无娘的受苦人,后来竟毅然舍掉了所谓小家庭的幸福,舍下了独生女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投奔了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牵牛房”的画家,是金剑啸,他是有才华的画家。剑啸是一位主要画电影广告和商业广告的画家,由于宣传抗日,后来竟被日本特务逮捕,英勇就义,牺牲时才26岁。
“牵牛房”的鲁大哥和孙教师
孙教师夫妇,是做秘密工作的。他们夫妇两人,一位是中学教师,一位是专科学校的教员,经常在“牵牛房”客人稀少的情况下来作客,来后默默地交给我和老黄几张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山里抗日游击队”打击日寇的胜利消息。我当时非常喜爱和羡慕那约有二毫米的字体,非常干净漂亮的油印抗日宣传品,幻想有一天也会写,也会那样做下去……常同他们夫妇接触的是唐达秋,他是哈尔滨第二师范的学生,从政治上和学习上与孙教师夫妇联系密切。他是“牵牛房”的“小弟弟”。
“牵牛房”的老大哥名叫鲁少曾,是哈尔滨铁路局的职员。他是一位谨慎稳重的大哥。他常对大家说:“出入‘牵牛房’的人要注意提高警惕,我觉得大门外来往的行人有些不对头呢!”于是,在必要时,老黄就让我抱着“小姑娘”(邻家女孩名)从室内往窗外瞧着“狗”(指特务)。
“牵牛房”是日本占领哈尔滨以后,朋友们聚会和活动的地方。听了鲁大哥的建议,大家警惕性高起来。我们在客厅方桌上放上瓜子、花生、糖果之类。每在朋友多时,若来了不速之客,由在座的一人宣布:“为黄大哥、大嫂的‘石头婚’祝贺!”或者在桌上摆上麻将、扑克之类,特意玩起来给查户口的,给走错门的,给那些“狗”们看。鲁大哥给大家的教育是很大的。
当年“牵牛房”的朋友,萧红、黄之明、唐达秋(即唐景阳)、金剑啸等人,一个接着一个的先后早已去世了,缅怀往事,令人痛心。活着的萧军、舒群、白朗、罗峰等从落实政策以后都很好。我在四十年前舍下的唯一独生女儿名叫黄鹂,13岁参军,在革命队伍中成长为一名女高音,她没有辜负父辈们的期望,我也就得以欣慰了。
1980年4月29日
选自《哈尔滨日报》,1980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