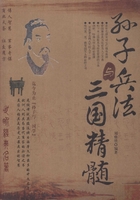二零零五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我开始有意识地做一些国际性的案子,如果可能,我想离开美国,至少离开纽约。我没有告诉Lyle我的打算,我们还是在一起,贪恋着彼此的身体。与此同时,来自工作上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我吃得没有从前香,睡得不如从前好了。有的时候,一次登峰造极的高潮才能让我放松入睡。只有Lyle。不过,我知道,他扮演的是浮士德当中恶魔米费斯特那样的角色,送我礼物,打扮我,给我很多很多亲吻和爱抚,一直到达最深处,腐化我的意志,渐渐地让我陷进去,直到有一天不能自拔不能停止。
某天,我跟Nick说起想去别的地方工作,香港、新加坡,或者上海,任何和这里有十二个小时以上的时差的地方。他说会帮我留意合适的机会。之后就开始有猎头的电话和邮件陆陆续续地过来,虽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谈成,我还是请他吃了一次饭算是感谢。
吃甜点的时候我问他:“你跟Alice怎么样了?”
他在我的香草冰激凌上加了好多糖霜和巧克力浆,回答说:“不是Alice了,现在的叫Young-na,韩国人,来纽约读MBA的。”
“你怎么也这样啊?”我笑起来,鄙视地看他。
“还有谁是这样的?”他没有笑容,看着我的眼睛问我。
我愣了一下,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加这个“也”字。不过我很快就反应过来,推了他一把说:“我呀。”
他没有理会,兀自发了一通感想:“男人其实很奇怪的,最喜欢的永远是一见钟情的那个女孩子,总是跳不出那个类型了。”
“你肯定你的Yong-na不是整容整成你一见钟情的样子的?”我很不厚道地嘲笑他。
“这有点像你们女孩子买衣服,最喜欢的那件没有了,总想找相似的,其实不用找了,找不到的,最喜欢的已经没有了。”他拿手机出来,给我看他和永娜的合影,东方女孩,笔直的黑头发披在肩上或是梳个马尾。他自己也看着,过了一会儿说:“她有点像你。”
如果换在从前,我肯定不会再说下去,触到那个总是若有似无的雷区。不过那天晚上,我还是有点义无反顾地对他说:“如果我哪一天离开纽约,一定让你知道。”
“当然要让我知道。”他轻声重复。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我拿到过两三个明确的工作合同要约,条件开得不坏,但是我总是犹豫,故意拖延那个离开纽约的日子。直到夏天眼看快过完了,一个新案子交到我们这一组,所有人都在躲,而我走进Rona的办公室说我想去。于是,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天,印度东北部持续了待两个月的骚乱尚未平息,我和另外一个男同事一起抵达新德里。
签证总共花了二十几天时间,直到出发的前两天我才告诉Lyle我要去别的国家出差,至少在那里呆两个月。在那之前我们还没有分开过那么长时间。他有点不高兴我没有早点告诉他,而且又是去这么个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新闻里面,炸弹游行不断的地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一点伤感,至少我有。因为在内心深处,我希望在这两个月里面忘记他,然后开始新的、更简单的生活。
跟我同行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高级律师,名叫Rydian,很严肃的一个人,看起来就像上个世纪好莱坞动作片里的硬汉。刚知道我会跟他一起去的时候,这个硬汉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直到我签证下来,并且拿到事务所投保的国际意外险保单,他才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跟我说他去打过预防针了,写给我诊所的地址和接种疫苗的名字,叫我也记得去打。霍乱、痢疾、登革热、脑炎、肝炎,疟疾……要打多少针啊?我一直很怕医院,小时候打针总是要想些悲伤的事情,怀着一种想死的心情才敢把胳膊伸给护士。那个时候,悲伤的事情现成有的是,我却决定对自己好一点,同样怀着一种想死的心情,不去打针了。
路上总共二十几个小时,先是坐美联的航班机到新加坡,然后转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新德里。飞机降落在成集机场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凌晨两点。走出机舱,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时差、距离、截然不同的气候都在促使我做一些在纽约会很艰难的决定。等候转机的时候,我发出去两封邮件。一封是给Nick的,告诉他我离开纽约了,大概两个月之后回来。另一封给Lyle:“不要跟我联系,至少给我一个机会忘记你。”虽然知道不会马上收到回信,我还是赶紧关机,害怕毫无准备地看到这样那样的字句。
继续往印度飞去的时候,天黑下来,遇到气流和一点坏天气,一路上飞机颠簸得很厉害。直到现在,那都是我经历过的最惊险的一次航程。乘务员穿着蓝色纱丽,装作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一边微笑一边派发冰激凌,给我一支梦龙雪糕,我说谢谢不要,转头才发现,那个在纽约不可一世的硬汉Rydian正在舔一个粉红色单球冰激淋。我闭上眼睛,认真地考虑了一下如果真的出了空难能拿到多少钱,又想如果这个官司由我来打的话一定可以多敲一笔,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死了,我爸妈会很伤心很伤心。Nick也会伤心。而Lyle,我想让他伤心得死掉,当然只是个希望而已。
空难发生的可能性毕竟很小,晚上九点多,飞机降落在英吉拉?甘地国际机场,除了累得要死,我们一根头发都没有少。穿过机场门口由无数乞讨的女人、老人和小孩组成的人群,找到来接机的车子,直接去酒店。我们住的地方是客户定的,一间坐落在市中心的四星级宾馆,本身看起来跟中国小城市的四星级酒店没什么两样,但四周的道路和建筑破败不堪,接下来的一整个月,每天晚上都有人在方圆一公里之内修路或者拆房子。清晨天还没亮,不知道哪里的清真寺又响起早祷的声音。我一连几个晚上睡不好,白天的工作又宛如肉搏战一样艰难。一个星期之后,Rydian因为喝了一口办公室里的桶装水(之前我们都是喝Evian或者Badoit的瓶装水),连拉三天的肚子,留了我一个人跟众阿三肉搏。可能我的身体真的很好,我没有生病,就是嗓子哑了。
工作的时候,我好像真的忘记了纽约发生过的事情。不过,每天夜里,包括每个稍稍安静一些的独处的时刻,思念向浪潮一样涌过来,吞没我,我还是不停地想他,虽然他很听话地始终没有跟我联系过。
我在MSN上跟Nick开玩笑说,终于知道《西游记》是怎么写出来的了,吴承恩一定是来过印度,九九八十一难全是真的。Nick老老实实地回答,他只看过一个缩略版的西游记故事,而且还是英文的。我说,我也没看过书,只不过在中国像我这么大的孩子每年暑假都会看一遍《西游记》的电视剧。他没有继续说唐僧孙悟空,发了一张图片过来,用画笔程序画的,歪歪扭扭写着我的中文名字。过了一会儿,又是一张,然后又一张,又一张。我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回了一句:是不是中病毒了?他回了一个吐舌头的笑脸。
九月二十日晚上,Rydian来敲我房间的门,给我一盒巧克力,说是Rona放在快递过来的文件里的。盒子上插着生日卡,因为那一天是我二十五岁的生日。我故意不去想起,但却从来没有忘记过。只是随便怎么样也没想到,会是Rona给我一份生日礼物,Rydian跟我说生日快乐。我蜷在床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那盒巧克力,比利时产的总是甜得有些过头了,但还是一块接一块地吃。其中有一种是酒心的,咬下去,甜辣的朗姆酒味儿瞬间就在嘴里漾开来。我躺着,耐心地等着睡着,不知道几点钟,门铃又响了。
我已经换了睡衣,一身在本地买的男式的棉布裤褂,长裤已经脱了,立领上衣长到臀部,刚刚遮掉内裤。我以为敲门的是Rydian,打开门,身体躲在门背后,只露出个头。红色地毯和米色大理石的走廊里,灯光有些幽暗,门外的人展开熟悉又不熟悉的微笑,对我说:“你到底是为law firm还是FBI工作?”
是Lyle。一种即欣喜又悲伤,有点开心又很委屈的感觉涌上来,让我不自觉地皱了一下眉头。我不想让他进来,只怕将近一个月的煎熬又要前功尽弃。但又跟自己说,Rydian就在隔壁,给他听到了不好。没等想出个头绪来,我就伸手把他拉进来,关上房门。
他可能误会了我的举动,一下子把我抱起来,在我耳边喃喃地说,他非常非常想我。我说你放我下来,口气很冷。他放了,但是放在床上,告诉我,我有点沙哑的声音更好听,我的印度褂子很性感。然后就开始解我衣服上的扣子,一直解到腰际。当中我推了一次,不太坚决,也根本没有用。他根本没有压到我,也没有开始吻我,虽然嘴唇离我很近,我还是没理由地觉得透不过气来,眼睛的余光看得见自己裸露出来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他似乎不急于做下去,倒是我先放弃了,翻身起来把他压倒在床上。那可以说是我最主动的一次,带着一点恨意。
如果不开心,高潮之后总是会觉得沮丧而且压抑的。我出了一点汗,没有让他抱我,把混在被子枕头里的衣服内裤找出来穿好,然后跟他说:“你自己开个房间,我不想跟你睡在一起。”
他摸摸我的后背,告诉我他住在政府区的香格里拉,那里环境要好一些,如果我愿意也可以去跟他住,或者我们也可以搬去奥伯罗伊17,那里有高尔夫球场,很好的SPA,还可以看见胡马雍王陵墓。
我觉得自己又做了一回笨蛋,他随身什么东西也没带,根本没打算要住在我这里。我回答说:“不用了,客户公司的车子每天早上到这里来接我们上班。很晚了,你回去吧。我明天一早还要开会。”话说得很平静。
“我可以送你上班。”
“我要睡觉了,拜拜。”
我躺下去背过身闭上眼睛。感觉得到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静静地穿衣服,静静地离开。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对我说生日快乐,他出现的日子可能只是一个可笑的巧合。他走之后,我一直醒着,心跳快到浑身颤抖的地步。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能跟他走,为什么要找这样的不痛快。黎明时分,远处清真寺的大喇叭又开始播放我听不懂的赞歌,我突然想到,如果有一天,文明覆灭,而我和他能够幸存,我们之间或许还可以有一点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