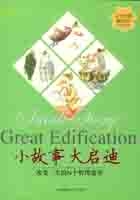前面说的那件让我发愁的事情发生在九月。
那一年的中秋是九月二十五日,到那个时候,我跟Lyle的分居协议已经期满,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应该已经离婚了。对于离婚两个字,我似乎有些钝感,很久都不能确定在那之后,自己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所以,一半是因为有差不多两年时间没有回过上海了,另一半是为了尽可能地让自己好受一点,我决定休假,回家去过中秋节。毕竟,隔着整个太平洋,和十二个小时的时差,无论什么事情都会显得不那么要紧了。
我打电话给Lyle,想问问他,我带Caresse去中国,他有没有意见。一开始是打到他家里的答录机上留言,等了两天没有回音。又打去他的办公室,Mayer太太告诉我,他不在本城,可能下周才能回来。我犹豫着要不要直接打他的手机,很久没打过了,有事情不是留言,就是请人转达,要么就趁接送Caresse的时候顺便说了。纠结了一晚上,觉得老这样憋着太傻了,而且还要抓紧时间给Caresse申请旅行证件。勉强等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半,想他应该起来了,就在办公室里打了他的手机。电话响了很久才他接起来,说“喂”,声音听起来明显刚刚睡醒,还在床上。
我对他说:“你好。”
他听出我的声音,说:“嘿,e。”
“在睡觉吗?我吵醒你了?”我问。
“没有,已经醒了。”他回答。
有短短的几秒钟时间,他的声音和语气让我忘记了早已经想好了要跟他说的话,恍然间觉得自己是为了谈别的什么事情才打电话的,究竟是什么,却也说不清楚。
于是,我稀里糊涂地说:“能不能见一面?有些事情想跟你谈。”这跟原计划完全不同,本来是想在电话上几句话解决的。
他停了一下,才回答:“我现在不在纽约。下周回来,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
我想告诉他:好的,我等你回来。话没说出口,就听见电话那头传过来很轻的女人的声音,好像是问他在干什么。
“你不是一个人?”我问。
他没回答,捂住电话跟那个女人说了句什么,然后又回到线上。
“我打电话来的时间不对,真的对不起,”我连忙道歉,回到原计划上来,对他说,“九月下旬我想带Caresse回家,回上海,需要你的同意。”
“你一个人带她坐飞机没问题吗?”
“应该可以,我朋友送我们到机场,我爸爸会在上海那边接。也没有很多东西。”
他沉默了一下,说:“好的。我暂时没办法回来。如果急的话,我会把需要的东西交给律师,授权书或者别的什么,你肯定比我清楚,你今天下午就可以跟他联系。”
我回答:“谢谢,再见。”
他也说:“再见。”
当天下午,他的律师给了我正式的授权,明示享有共同监护权的一方同意另一方把被监护人带出境。不过那份东西不光是那么简单而已,上面还仔仔细细地列明了附加条件:在国外逗留多长时间(要有两个人往返的机票作证明),每隔多久通一次电话,另外还要求我为这次旅行提供抵押,房产外加银行户头上的存款。我不知道那究竟是Lyle自己的意思,还是他接受了律师的建议。抛开一本正经的法律术语不提,那些条款让整件事情看起来跟小学生在桌子上画三八线差不多,同时又多少显得有点冷酷。我全部照办,不管怎么样,我走定了。
本以为我们会在九月十七日再见,因为那一天是分居满一年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签字离婚的日子。不过,十四号上午,我接到MacDenton的电话,跟我说,Lyle人在苏黎世,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他那方面的律师打电话来询问,是照原来的计划十七号签字,还是等一等,直到他回来。我回答:“照原计划。”
签字的场面没什么特别,两个人甚至都用不着见面。我在MacDenton律师行的会议室里签字,Lyle隔着一个大西洋和六个小时时差,所以,用的是传真。
于是,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多,带着Caresse在肯尼迪机场登机的时候,我刚好过了二十七岁的生日,也刚好了结了我的婚姻。我们坐了差不多十四个小时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转机,到达上海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晚上十点多了。这条路线跟我五年之前初到美国时走的刚好相反,那个时候是上海——北京——纽约,然后坐长途汽车到波士顿。走出国际到达口的时候,我甚至有点紧张,怕看到爸妈会哭,但事实是,隔了太久了,就不会再哭了。
我跟爸妈拥抱,把Caresse介绍给他们,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小朋友的真人。刚开始Caresse还是笑笑的,但无论如何都不让外公外婆抱,碰一下也不可以。他们总想抱她,她索性放声大哭起来。几次这样下来,大人们也只好放弃了。
“这样哭法,马路上人家看到还以为是拐来的咧。”我妈有点失望,小朋友不喜欢她。
第一夜,因为时差的关系,Caresse很是兴奋,坐在床上玩了大半夜。快到两点,才在我身边睡着了。我还是睡不着,在房间里乱转。我出国之后,爸妈搬过家了。我和Caresse睡的是留作客房用的一间屋子,完全陌生的房间。没有衣橱,沿墙一溜书柜,摆得都是平常不太用到的旧书,只有那里有一些我熟悉的东西:我小时候的影集,上中学时同学间寄来送去的贺卡和信件,还有一纸盒旧玩具。里面有一只发条水晶球,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是我外婆梳妆台上的摆设,应该是她年轻时买的,玻璃球体里是一匹身披鲜花的白色旋转木马,摇一下,就会有晶莹剔透的雪花扬起来,再很慢很慢的落下。原本只要上紧发条,还会演奏“鲜花华尔兹”,那个曲名用德语写在底座下面,只是很久以前就被我弄坏了,现如今只会发出嗒嗒的声音。我看了它很久,不能相信自己曾经弄坏了这么美的东西。
第二天我和Caresse还是日夜颠倒、昏头昏脑的样子,直到下午三点多午觉睡醒才又精神了。我从房间里出来,刚好听见爸爸在客厅里接电话,拿着听筒,含含糊糊的说:“没有,工作忙吧,呵呵呵呵。”电话那头是在问我有没有带老公回来。
等他电话挂掉,我对他说:“谁要是问起来,就实话实说吧,又不犯法。”
爸爸点了点头,妈妈插话说:“你奶奶高血压,要气死了。”
这倒是真的。这是个大家族,表兄堂弟数不清的亲戚,往上数三代也只有一个嗜赌的堂房叔叔离过婚,而且我曾经是这一辈儿里最好的。我们正商量着要不要索性大大方方地把我的婚姻状况讲出来,结果却发觉这所有踟蹰都是多余的,尚在彼岸的Victoria已经免费替我宣传过了。我不太清楚最早的版本是怎么样的,反正甲告诉乙,乙再说给丙听,慢慢的也不知道原来是怎么说得了。几天之后,有个亲戚很关切地看着我,问:“现在怎么样了,事情都处理好了吧?”我以为他指的是离婚,就说已经好了。搞了半天才明白,他听到的版本是,我在美国被人骗了。
在上海,Caresse这样肤色的小孩总会吸引许多人的注意,引出更多关于她身世的问题。我说的“许多人”包括邻居、物业管理员、商店店员,甚至公园里同样带着孩子的陌生人。大人们喜欢逗她讲话,引她笑,叫她“洋娃娃”,转身却又在感叹:现在没爹的小混血真是到处都是。孩子们则是更加公开讨论她的发色和眼睛的颜色,大一点的小孩还会说出“血统”这样高深的词,好像她是一只半比熊半贵宾的宠物狗似的。
我以为自己会受不了这样的场面,但实在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忍受不了的,也没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我不回避那些问题,不少说也不多说一句。而且,尽管看起来跟别的小孩不太一样,Caresse也有她自己的魅力,融入到他们当中去。她很快就跟外公外婆混熟了,也喜欢跟小朋友玩,很愿意跟人家手牵着手走路。那些小孩子也逐渐喜欢上她,刚会讲话的小信很远看到她就大声叫她“咔咔”,六岁的诺诺调低滑板车的扶手,让她把着扶手站在上面,推着她在花园里转圈。她在阳光里面,笑得快乐无比。
几天之后,在餐桌上,我爸刚放下碗,Caresse突然说:“阿拉饭饭吃好了。”说得很响很清楚,那是她第一次说出一个句子,用上海话,不是英语。
第二天我跟Lyle约好要通个电话的。约在上午十点,因为那个钟点Caresse总是醒着的。九点半之后,我不自觉地看了好几次时间,突然发觉自己怀着一种几乎按捺不住的兴奋的心情。可能我只是因为高兴,想要把快乐的事情告诉其他人,也可能还有别的,却不愿意承认罢了。
电话很准时地响了,我们互相问候,我把Caresse新学会做的事情、说的话,讲给他听,然后把小孩儿叫过来,听筒放在她耳边,说:“Caresse叫爸爸。”
“妈——咪——。”小孩儿一边笑一边叫得很响亮。越洋电话两头,所有人都笑翻了,连带Caresse自己。
她能说一整句话,却一直分不清楚称呼。对她来说,“妈咪”是对所有照顾她的大人的总称,我是“妈咪”,Lyle也是“妈咪”,保姆还有外公外婆都不例外。
等我回到电话上,Lyle似乎有点无可奈何,问我:“你说要不要带她去看医生,育儿专家之类的?”
“等我回来再说吧。”我回答。
“告诉我回程的航班号码,我来接你们。”
“你来接Caresse吧,另外有人会来接我。”
“好。”他答应了。
挂断电话,我妈看了我几眼,好几次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忍不住了,问我:“你们两个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啊?”
还能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妈接着盘问:“看你们好像还蛮好的样子嘛……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爸爸则开始循循善诱:“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你老是喜欢一手抓着爸爸一手抓着妈妈,一边走一边跳啊?你女儿要是也想这样,你一个人是抓她左手还是右手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