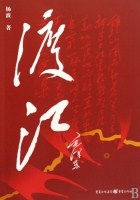议论暂告一段落,我先将那一过程叙述一遍吧,它快成我这篇文章的一块心病了,甚至可以说我一直把它当成了这文章的“核”,我甚至隐隐构思成:当我的身体高潮来临时,也便是我这段文章的高潮!现在我发觉这是一个俗构思,大可不必。
30
我们在街上确实吵了一架。她说了什么我忘了,反正是怪我在一边躲清闲。我只记得她的行为就是急得直跺脚,我则有些大怒,心说不就是个“鸡”吗?敢跟大爷这甩脸子,简直没了王法,我不会别的,只会拂袖而去,一走了之,想来我当时的行为心态也够小人的。但我也没走远,大约也就走出去五六十米吧,我当时只是不想再看见她,除此之外,胸中便是充斥着气愤、嘲笑、报复,充得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坐在马路牙子上,呆呆地望着橘黄的大街、树影……
过了会儿,彭小玲溜达着过来了。她见我依然闷坐,说,好了好了,赶快打车吧。我抬头瞟了她一眼,她直立在我身边,眼望街道,显然她的急躁情绪依然在,脸上还挂着些不耐烦,好像说我太难伺候……
来车之后,我自顾自坐进了前座,一言不发。坐在后座的彭小玲倒是过了劲,她开始跟我没话找话。我发觉我们的位置调了个个,她变得轻松,我倒坠入愚蠢的生闷气的境地。
冥冥中,我终于掉进了某个圈套……掉进来了,就好了。
31
我采取跪式。我们选择了两张席梦思中离窗户较远,靠墙的那张。
彭小玲开始在看电视,我挡住了她的视线。她没想到我会这么坚强地进入。她闭眼,咬着嘴唇。她一声不吭。她渐渐皱起了眉。我分不清她是在受罪还是在满足。
我在满足,我们的身体条件非常合适。
她两条细长匀称的腿轻松而富有弹性地高扬,我的两肋像生出两只翅膀;也有时我像世界杯上韩国或日本球迷那般举着两根喝彩用的棒子……
她始终没说话。我也没说。也就是一支或两支烟的工夫吧。
我想我是很愉快、很满足,像一截木头一样倒在了彭小玲的身边。除了肉体上的愉快满足,似乎更像是完成了某项使命一般的愉快满足。
我终于可以嫖了!我终于可以做一名合格的嫖客了!而争做嫖客,算怎么档子事呢?
我就是那么愚蠢地像一截木头倒了下来。彭小玲似乎夸了我一句:“你好硬哦!中午怎么就不行呢?”
就当是夸吧。做强暴的男人,做以强力实现自己欲望的男人,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一个男人的流行标准。
我费了牛劲,最终还是落了俗套。
我当时还挺美的,沉浸在某种了了一桩心愿的四体通泰中,我也没心情跟她说什么话,她也一切正常,接着看她的电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我无疑又抽了根烟,喝了两口啤酒,似乎脑子里可以什么都不想了。
一场简单的肉体行为将我头脑中的胡思乱想统统驱除了吗?
我就是这么着什么都不想了。爱情不想,肉体也不想了。我无意再来一次。我穿上衣服,溜溜达达下楼吃夜宵去了。彭小玲倚在枕头上,保持着看电视的姿势,睡着了。我无意跟她打招呼,我也没轻手轻脚,她应该也并不知道我的离去,在那片刻,我们俩几乎互不存在了……
在日后的这些年里,我们就更不可能互为存在了。我湮没在她所接触的诸多男人之中,肯定对面不相识。我是一件“小活儿”,虽然比那“一锤子买卖”大点,但也大不到哪去,作为我的特点,“假性阳痿”肯定比“假性近视”要多,甚至这根本不是特点,在这个开放大潮初起的时代,“假性阳痿”没准是中国男人的通病呢。
而彭小玲在我的记忆中只不过是一个日趋淡薄的影子,之所以要提到她,完全是因为那件事,那件发生在我身上的金钱/肉体交易,而这种交易于我是罕见的,所以我记住了,但和我一起干这事的人,却很模糊,按传统文学观点,属于“性格特征不鲜明”,没法鲜明,稿酬标准那么低,但“炮费”却高得惊人,发表个三四千字才够打一炮的,而且流行按名气论稿酬,像我这样第一没什么名气,第二又是专攻中短篇,且对文学采取精益求精宁缺毋滥的严肃态度的“作家”,嫖一次容易吗?而且我得着什么了?既献身又现眼,而且不惜以“献身现眼”为题材在这搜肠刮肚地乱抖落,这一切的一切,还不是好文学这一口儿吗?我可以了我!当初妄想跟彭小玲谈恋爱,没准潜意识里就是为了日后塑造个“性格鲜明”的新时代杜十娘,但我跟冯梦龙可没法比,他那什么时代?我这又是什么时代?
无论什么时代吧,我在国庆前夜,离开十多层的那个宾馆房间……我经过灯火通明的大堂,我走向紧闭的电动玻璃门,门向两侧听话地打开,我走进有些凉意的夜色中……
32
我绝对没有彳亍街头,按说焰火过去,人迹阒无的深夜街头或许是产生诗意的绝好氛围,尤其是对于我这个刚“失了身”流落异地的孤独男子,可我当时却无论如何没想到这么一景,我的心态多少像一个携款潜逃的贪污犯因慑于人民政府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巨大压力,索性破罐破摔肆意挥霍花钱花红了眼一般无知无觉地又进了一家高档酒楼,说它高档,无非是灯火辉煌,门脸儿雕梁画栋飞檐走壁大红灯笼高高挂,门口无疑有两位身材高挑穿大开气儿红旗袍的漂亮小姐……
厅堂内人并不很多,却也并不很少,我拣了张桌子坐下,立刻有一位穿民国式印花蓝布小褂系绣花围裙的小姐捧着小本立在我身侧柔声问“先生吃点什么?”同时又有一位穿天蓝色西服套装戴小船形帽斜披红缎带笑容艳丽的小姐立在我对面和蔼可亲地亮给我看她手中的啤酒:“先生您要不要尝尝我们公司新推出的金装青岛啤酒?”此刻又有一穿超短裙魔鬼身材的“登喜路”小姐捧着个盒子游到我身边,我从盒子里拈出一支登喜路,她躬身为我点火,我说谢谢……
当这些小姐散去,只见店堂的此一角落,一张锃亮的黑漆方桌前,坐着我这么一位面色苍白两眼发木的男青年,此人左手夹着根登喜路,右手攥着杯泡沫丰富酒体晶莹剔透的金装青岛啤酒,面前是两碟价格不菲的小菜,象牙筷子,盛在小竹筐里的热手巾卷……
我喝着爽口的冰啤酒,将那支同样爽口且爽心爽肺的登喜路抽完,我好像有点缓过神来,我对正给我上菜的小姐着急地说:“哎小姐,刚才我都点什么了?”
33
大约凌晨了,我依然坐在那间酒楼里。我感到城市似乎已是一片黑暗,只有这间酒楼尚在灯火通明。我的脑子僵硬麻木,好像已运转失灵。有那么一个瞬间,厅堂里一切的人与物,除我之外,均静止不动了,定格了——
穿旗袍的小姐侍立各处,脸上涂着虚假的红胭脂,微笑僵在脸上,如一具具蜡人,有小姐微微稍息,旗袍开气儿处露出长筒丝袜的上端;穿印花蓝布小褂端盘子的小姐以各种杂技般的姿势肃立于桌边及过道;与我相邻的一桌坐着一男二女,男人是个穿花格T恤的胖子,大约正在神侃,一脸的表情固定在闭眼挑眉嘬嘴的状态,二女浓妆艳抹,对胖子的聒噪充耳不闻,正张开血盆大口生吃冰镇活虾,一只被生剥了皮扭了头的玉色虾体正卡在一女的红唇白牙间;另一桌上,魔鬼身材天使面容的登喜路小姐正弯腰伸臂为一穿白西服的汉子点烟,火苗亦静止如画,白西服汉子欠臀嘬烟,双臂微张,二目不看烟头直盯小姐胸部,整个身体重量竟只靠那弯曲的双腿,其状如一只发现了猎物的大怪鸟……
只有黑漆方桌后面的我尚有微弱的喘息,此外一切均静止不动,整个世界似乎都已死掉,除了这间行将消失的仿古酒楼,或许还有公园里焰火过后正在弥散的硝烟……我也只不过像是一个因生活失意而沉湎于吃喝的饕餮之徒,守着一桌的好酒好菜,满怀绝望,除了陷入不可救药的贪吃症则此刻别无出路……我就要举筷饕餮了,但我觉得我也正在凝固几乎动弹不得,一种即将被这个世界一同带进死亡的恐惧让我惊悸过来,我几乎使出浑身力气挣扎着发出了声——“小姐买单!”
杯筷声人声瞬时又涌入耳畔,各色小姐各色食客纷纷活动如初,那欠身点烟的白西服汉子终于挨过了他那尴尬的一刻,他利用那001秒的瞬间将登喜路小姐那隐约的双乳印在心头,现在他可以漫不经心又不失绅士风度地说声谢谢,然后喷云吐雾扭过身去与同伴畅谈生意了,我注意到他坐下来的瞬间对那登喜路小姐看也不多看一眼,仿佛街头与陌生爷们对火一般随意,此公平日里弄不好是个老古板呢。
34
让我来叙述一下彭小玲的最后一瞥吧。首先就是苍白空洞,但我无论那时还是现在,都特想从那一瞥中琢磨出点什么。
十月一号的早晨,我们竟都醒得很早,我们是分床睡的。我拉开窗帘,天空晴朗,很符合国庆节早晨的要求。我们各自洗漱完毕,当着对方的面一件件穿衣,她是自己将后背的拉链拉好的,我们谁也没求谁。我给她留了我的呼机,她给我留了她的一个女友的呼机。我们各自坐在各自的床上,她不多看我,我一直盯着她看,我不是留恋,我就是纳闷,就是还有点不甘心:怎就没点事发生呢?
就是没事发生。她的眼神始终回避着我。她站起来往外走,她的身躯现在想来仍是我喜欢的那种细长,但当时我对此也毫无留恋。她说:“走喽,拜拜。”我说:“拜拜。”
她开门出去的时候,我说“哎”。她扭头给了我一个苍白的探询的面孔,以及一个苍白空洞的眼神。我说:“没事,拜拜。”她说:“拜拜。”她不紧不慢地开门,带门,消失了。
我脑子里闪过:她在走廊里走着,走向电梯……我跑出去将她揽进怀中她也正不想走因而与我紧紧拥抱重燃爱火……我怎么竟滥俗至此!我心中痛骂自己几句,起身去清点我钱包里的钞票。清点的结果是我有点心疼,显然我花多了,我点着剩下的钱,心说:愚蠢到此结束!
35
此后的几天,我还是多少在意了一下我的呼机,尤其是在夜晚灯火辉煌的酒馆里,喝到半酣时刻,多少还会想到彭小玲,但也仅是想想而已。钱如流水般离我而去的心痛感觉让我无所作为。这有点像一个对赌博还未上瘾的新手刚上赌场就被抽立了一回,弄不好这辈子就跟赌博无缘了。
关键是,我没钱。我想,倘若给我足够的金钱,我仍会疯狂地去赌、去嫖,我爱这些腐烂的东西,原因是“腐烂”是别人说的,我没体验到,我体验到的是人们所说的“魔鬼般的诱惑”。
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只有“坏东西”才有诱惑力的年代?小时候电影里的女特务,以及《南征北战》中的“张军长李军长”,后来有一部片子叫《侦察兵》,我们喜欢王心刚也是因为他披了身国军制服……后来,凡是我们认为好的,社会就认为坏,手抄本,毛片,早恋,旱冰场里的少男少女,地下文学……现在是:黄赌毒。
说句实话,我们没法再信了,即使这次你们说得对,我们愿意为了验证你们这次“终于对了”而不惜自我毁灭……别拦着我,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就让你们的正确建立在我们的牺牲之上吧。
36
那一天一夜,我漏掉了很多,有些我想不起来了,有些我没兴趣提。她曾说过“老公哦……”,她曾说过“你不修边幅”,她曾跟我打赌,她说电视里的女演员是胡慧中,我说不是,最后演员表中果然没有胡慧中的名字,但她赖过去了……这些细节都像是只露了一点头的线索,我抻不住这个头,无法从中拽出真正的她,我毫无信心,就不再多抻头了,就是她吧,彭小玲,鸡,少女,瘦长,性格偏内向,心性善恶不明,很可能是新手,体力衰弱,证明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行当,或说像她这么干是不轻松的……
我,嫖客,酒鬼,读过很多书,理想主义者,愤怒青年,爱写作,被人生意义折磨得脑子里一塌糊涂,因而为人处世无一定之规,忽而挥金如土忽而抠逼嘬手指头……
数年过去,我仍没什么出息,比如我有时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我将重回深圳,于茫茫人海中寻找瘦长身影,我游魂般准确到达烟花柳巷,我将不嫖不醉,我的目光明亮,有礼貌地回绝一次次妖艳淫荡的招引,我的嗅觉灵敏,在一阵阵劣质香水的浓香中不作片刻停留,我的心被肤浅的牛逼感充盈,只因为我正在实现这么一个滥俗的理想,这理想可概括为:人世沧桑,时光无情,嫖客寻旧,物是人非,结局是:无论她已成深圳名妓还是继续饱受凌辱地瞎混,总归对面不相识,我费尽唇舌无力救风尘,于是只得满含一腹辛酸离开这灯火通明的花街柳巷,孤身一人走进茫茫黑夜……这就是我可怜的、令人作呕的想象力。
那么牛逼一点是不是就这样:多年之后,我去某中小城市出差,我在某小卖铺买烟或在某小饭馆吃饭或在某服装店陪有暧昧关系的女同事买衣服甚或在某格调清幽的小音像店挑打口CD……总之你猜到了,这些第三产业的女老板,就是那多年前我嫖过的彭小玲!彼情彼景你去设想吧,无论是初中女生、“青春美文”作家,还是电影局新闻出版局的审查官们,给你们一次文艺创作的机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