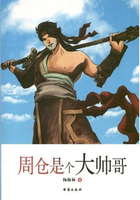又一个清晨,我回到波士顿,试图把过去三天里发生的事情统统留在身后,却不知道一切还远未结束。一打开手机就听到梅森的留言,说她人在纽约,形势一片大好,所有会走路且穿得下四号以下衣服的姑娘都能找到工作,叫我快去。在一种奇怪的自毁念头的驱使下,我觉得这个时候跑去跟梅森鬼混,肯定会比回去上课好受得多。我回宿舍洗了澡换了衣服,然后给她打去电话,说我随后就到。她在电话那头疯笑,说昨晚刚好有人崴到脚,我去了一定可以顶那人的缺。于是,我立马开车过去,中午之前到达纽约,当天下午就开始在一个有些名气的设计师那里做试衣模特。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真正的时尚圈子里混。用梅森的话来说就是:“咱俩头一遭在时尚圈里闯荡,结果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然后就吼吼的一通狂笑。所谓“灾难”发生在我到纽约的第三天。那个服装系列的打版工作基本完成,工作室的负责人让我们留下联系方式,说会考虑留用几个人。梅森很兴奋,我说:“我就算了,明天还是回去上课吧,缺勤太多了会不及格。
”梅森做依依不舍状,见劝不住我就说:“那今晚带你去玩吧,我给你搞张‘入场券’。”她说的是一个当天晚上派对,很多时尚圈里的人和社交名流都会参加,也就是说那样的场面,像她这样的末流模特是不会被邀请的。那么所谓“入场券”又从何而来呢?后来,我才知道,她不过就是勾搭了一个保安大哥。我说:“我除了T恤和牛仔裤什么都没带。”她眨眨眼睛,回答:“这里这么多衣服,挑两件借一晚上没人会管的。”于是,傍晚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趁人不注意,在工场间旁边的小房间里,一人拿了一套小礼服。我后来才意识到,自己生平第一次做了回小偷。晚上九点多,我们两个被梅森的保安大哥从酒店后面的小门放进去。就像是一次探险,从黑乎乎潮湿湿的小巷开始,经过简陋的员工通道、休息室、洗衣房,最后,他推开一扇两面开的沉重的胡桃木大门,对我们说:“就是这儿了。”梅森咯咯笑着给他一个吻,拉着我的手走进去。
里面是另一番天地,灯光微暗,空气里飘散着香水和酒精的味道,隐约可以听到低音吉他性感的节奏声,有人在演唱戴安娜·克劳的《让我们坠入爱河》。我们走过一面镶满落地镜的影壁,我偷偷瞄了一眼镜子里自己的侧影。梅森穿了件黑色裙子,V领一直开到腰际,毫不羞愧地露出美丽的胸部。我穿的是件长到膝盖上的酒红色裹胸式礼服,同色的鞋,鞋跟足有三寸。脸上化了妆,看起来那样陌生。梅森很快勾搭上一个穿着体面的男人,做出一脸崇拜的样子听他吹牛:去哪里哪里看了多大的房子,认识个朋友去年赚了多少多少钱,好多的数字,好多“百万”、“千万”。我靠在吧台边上,连续喝下三四杯叫不上名字的酒之后,注意到角落里的一个栗色头发的男人,深紫色衬衣黑色西裤,慢慢地饮着浅浅一杯疑似威士忌的棕黄色液体。我对自己说:就是他了。随即选定,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一个侍者托着酒水盘子从旁边经过,我连盘子一起拿过来,托在手上,走过去。
梅森看见我行动了,对我做口形:“哪一个?”我朝那边甩甩头,她看了一眼,撇下那个“千万先生”,颠儿颠儿地跑过来说:“丫头,你看男人眼光还真好,他是这里最好的了。”被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倒没底了,不过那个时候的我还真有点不怕死的劲头。我径直走过去,那人也注意到我,转过头看着我,脸上却没什么特别的表情。我走近他,看着他的眼睛,发现他虹膜的颜色是一种非常深的蓝色。我有点喜欢那颜色,于是就轻轻慢慢地对他说:“曼哈顿,玛格里特,还是我?”他笑了一下,贴近我耳边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有关系吗?” 我反问。“你从哪儿来的?” 他又问。“从一个我正想忘掉的地方。” 我回答,把托盘放在旁边桌子上,伸出手抚过他的脸颊和他下巴上一个可爱的凹陷处。微醉状态下,觉得自己像一个真正的情场老手。不到十五分钟的调情,一杯西瓜马天尼之后,按照“情场”上心照不宣的套路,男人提议:“让我带你去看曼哈顿的夜景,我的房间在三十五楼。”我猜得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却还是朝他笑了一下,点了点头。
他带我穿过人群,在一个僻静的白色大理石铺就的小厅里等电梯。清脆的“叮”的一声,电梯门开了,他牵着我的手走进去,在电梯门合上之前就开始吻我。我就任由他去吻。两秒钟过去,门却没有关起来,有人伸手挡住了,我回头,那个人竟然是林晰。他没看我,对那个男人说:“对不起,她还未成年。”伸手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出电梯。男人愣了一下,然后满不在乎地笑笑,对我说了声:“不要玩你还不懂的东西。”走掉了。“你干什么?”我一下甩掉林晰的手,挑衅地看着他问。他很难得地穿了件看上去价格不菲的铁灰色衬衫,应该也是来参加派对的。不同的是,他是受邀的,我是混进来的。他不跟我废话,又来拉我的手。我没想到他这么秀气一个人,个子并不比我高多少,力气却很大。我挣不脱他的手,就放开喉咙大喊大叫,很多人过来看,他只好放开我。我气呼呼地走回宴会厅,头也不回,心里却很清楚他就跟在我身后。他看着我一杯接一杯地喝酒,把所有接近我的男人赶走,直到我脚下打晃,估计无力反抗的时候,把我架出去,扔上车。
我趴在汽车后排座椅上,头晕脑涨,睁不开眼睛,隐约觉得手摸到的是细腻的皮套,不是记忆当中那辆旧雪佛莱上的绒布套,突然害怕起来,勉强撑起身子,大叫:“你在哪儿啊?别丢下我,别丢下我不管啊!”恍惚间,有人从前排驾驶座上探过身子来抱住我,用熟悉温和的声音说:“我没走,我就在这儿。”我又平静下来,躺在位子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车子停下来了,我稍微清醒了一点,觉得胃里难过得要命,也不是胀也不是痛,说不清是什么感觉,就是很想吐。林晰打开车门,刚准备抱我出去,就被我吐了一身。他拍着我的后背,让我吐,等吐完了,把我从车里抱出来,一直抱到房间里,放在床上。我拉住他,一下把他带倒在床上,看着他的眼睛问:“你喜欢我吗?”“不喜欢。”他冷冷地回答。“我就知道!”我恨恨地说,眼泪流下来。我松开他,转过头把脸埋在枕头里,安安静静地哭。一直哭到他把一只手放在我头上,轻轻地抚弄我的头发,叹了口气说:“我喜欢你,你一直都知道的。”听到这话,我又有了精神,翻身坐起来,却在他眼睛里看到伤感的神情。我讨厌这样的表情,借着未退的酒劲儿说:“我不知道,你证明给我看。
”说完就把嘴贴在他的嘴上,又笨又粗鲁地吻他,手也不老实,解开他衬衣的扣子,在他胸前摩挲着。我做得很差,但却可以感觉到他身体的反应,变得既紧张又敏感。但他还是推我,低声说:“你放开我。”动作和声音都很坚决。“我不放,今天就是不行。”我好像也很坚决。“放开我。”他又说,“我去买避孕套,我这儿没有。”我终于放开他了,仰面倒在床上,看着他走出去,居然觉得有点得意。先是看着天花板等他,头晕得要命,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痛,我撑不住闭上了眼睛,眼前晃过纷乱的场景,分不清谁是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出五分钟,我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仍旧头痛欲裂,勉强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林晰的床上,一个人,身上只套了件半旧的男式白汗衫。回想昨晚发生的事情,只能想起个大概。林晰走进来,嘴里嚼着吃了一半的早饭,见我看着他,说:“看什么看,我什么也没干。”“我还以为你喜欢我呢。”我说。“我也一直以为你多少有点喜欢我。”他突然变得有点严肃。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他没去买什么避孕套,只是在门口站了半小时。之后又花了高得多的价钱买下我和梅森偷走的那两件礼服,摆平了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