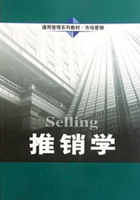十二月三十日一大早,我就开始反复地打周君彦家的电话,想告诉他我在纽约的号码,但他家的电话还是没人接听。我算了一下,已经差不多有一个礼拜没有联系到他了,有点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忐忑不安地过了一天,到了晚上,林晰不知从哪里搞到两张小范围试映的电影票,带我去看。那是一部欧洲电影节上获奖的影片,换而言之,是一部诡异的电影,银幕上充满了浓郁的颜色和激烈的情感冲突。当女主角脱得光光地在树林里悲愤地乱跑时,我突然意识到此时在上海已经是十二月的最后一天了。我在黑暗里不声不响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对林晰说:“我要回去接个电话。”不等他说什么,我就站起来挤出去,一路跑出电影院,到街上拦下一辆过路的出租车,上车对司机说了学校的地址。车子发动,我回头隔着车窗玻璃看见林晰也出来了,正站在电影院外的霓虹灯下朝这里眺望。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不过,的确有那么一会儿工夫,我很想让司机停车,下车跑回去,跟他说一声我要去哪里、去干吗。
但是,一生当中就是会有这样的时刻,你不想将来或是过去,甚至根本不能思考,当时周围的一切都失去意义,你一心去做一件事,哪怕到头来觉得自己蠢得可以。几年之后,我在有线电视台又看到那部电影,终于记住了片名--《希拉里和杰姬》,中文名经常被译作《她比烟花寂寞》。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已经将近十二点了,我在黑色的铸铁大门外面按了很长时间的门铃,没有人应门。出租车早已经掉头开得很远了,我只好沿着积雪的细石车道走回公路,站在黑黢黢的路边上努力分辨方向,然后向西步行了一刻钟左右,在遇到的第一个电话亭里打电话给学校值班的大妈,随口瞎掰说:“抱歉哈,飞机晚点了,刚刚到学校门口,麻烦来帮我开开门吧。”放下听筒,犹豫了一下,又拿起来,拨通林晰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却是个女声,是洛拉。她听到我的声音就叫起来:“上帝啊,瑾,你在哪里啊?”“我回学校了。”我说,奇怪她干吗这么大惊小怪的。“林在警察局,他以为你回我们那里了,等到十一点钟还没有看到你就报警了,他记下了你坐的那辆车的车牌……”洛拉还在不停地说,我打断她,说了声再见,挂掉电话就拼命地朝宿舍跑,怕林晰再打来电话发现我不在宿舍里。
进门的时候,电话铃果然在响。我来不及开灯就接起来,黑暗里,突然发觉自己有点害怕他的反应。“你回学校了?”他问,声音很平静。“嗯。”他轻轻地笑了一声,说:“那早点睡吧。”他先挂断了电话。我知道他生气了,一秒钟的内疚之后,我也生气了。我跟他说过我回去了,是他自己误解了,怪谁?第二天,一觉睡到中午,周君彦的电话来了,对我说:“上次忘了说是美国时间还是中国时间了。上海马上就是新年了。”听声音,他好像挺开心的,又好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等我分辨出那背后是什么,他突然很轻地说了一句:“你走的那天,我应该亲你一下的。”很长一段时间,那句话一直留在我脑子里,在右耳边上一遍一遍地重放:“你走的那天,我应该亲你一下的。”可能是吧,我在心里回答。那个时候,我们总有那么多事情想要做,却总也做不到。我走的那天,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单独说什么,更不用说吻别了。唯一留下的纪念只有在机场拍的一张合影,底片还在我爸的照相机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去洗出来,又会不会想到寄给我。我只能靠记忆想象那张照片的样子:他对着镜头微笑,我漠无表情(那就是我在那个年纪最经常的表情),他的右手搭在我右边肩膀上。
整整四个月过去,我仍旧清楚地记得那个不到两秒钟的接触,隔着T恤和一件薄毛衣仍旧可以感觉得到手指哪怕一丝一毫细微的动作,手掌的温度,不热也不冷,却是一种无名的引力。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想到那天的事情,心里却莫名其妙地觉得很难过。我仰面躺在床上,打断他,问:“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啊?”话一出口,眼角就湿了。就是这一句话让我回想起所有的事情:一个人拖着五十斤的行李在洛杉矶机场狂奔赶去纽约的飞机;节日里被遗弃在这个鬼地方;凌晨独自在雪地里走,手和脸冻得快没知觉了……在这些事情发生的当时,我并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现在却觉得委屈得要命。他沉默了一下,回答:“我已经申请了波士顿大学了。不是很好的学校,肯定可以录取的。”“真的?怎么不早告诉我。”我高兴起来。“这个就是保底的。”“那我放完假也去波士顿看看。”我说,“前几天打你家电话都没人接,怎么回事啊?”“没什么,就是亲戚家有点事情。”“我挺怕你突然说不来了。”“如果我不来了,你怎么办?”“当然回去找你算账啊。”我说,“你会不来吗?”电话里传来焰火和鞭炮的声音,星球的另一面,新年已经来了。喧闹声的间隙,他说:“不管怎么样,我肯定会来找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