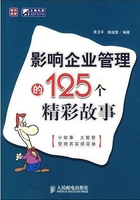第二天早上,几个女孩子天没亮就起床了,简单地梳洗一下准备出门。我手忙脚乱地赶不上她们。不一会儿,林晰也来了,挨个儿和每个人吻了脸颊。轮到我,他坏笑了一下,也两边各亲了一下。出了门,我发现大家都是分头去不同的地方,林晰告诉我:“她们那个行当现在是忙季,主要就是不停地面试,还有给设计师当试衣模特。”因为时装周在秋季和早春,这帮姑娘,以及其他一干人等,就得在夏天和冬天的极端天气里四处奔走。春天的这一次主题是秋冬服装,只不过是早早地为下一个冬季打算了。整个上午,我都在林晰工作的那间广告公司的摄影棚里度过。他关照我在一边站着,不要出声,不许动任何东西,要是有人问就说是跟着他的。他自己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拍摄一组静物照片。他拍照,一个女孩儿测光、举反光板,还有一个衣服上印着波士顿红袜队标志的男孩子在旁边打杂。我探头望望,发现三个人当宝贝一样围着的东西,不过就是小型摄影台上放着的几颗类似螺栓的东西。好不容易等到午休时间,他才有空跟我讲话,告诉我,这是给一间公司做产品目录用的。
他自己在外面接的活儿比较有趣,也就是他晚上在忙的那些事情。他在报纸上登分类广告,不时会有需要摄影师的人打来电话,大多是不太出名的设计师,还有想当模特的姑娘要拍面试用的照片,当然有时也会有百无聊赖的女人请他去拍内衣照甚至裸照。说到这里,他半真半假地笑笑,我鄙视地看看他。他带我去公司附近的一个小餐馆吃饭,说一会儿有个人在那里跟他接头。那人也是要做一本目录,不知道是嫌价钱太贵还是对他有意思,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谈了好几次。我心里说,自我感觉还真好咧!然后就愈加鄙视地看他。十来分钟之后,来了一个头发理得很短的男人,三十几岁的年纪,穿着打扮都很正常。走进餐馆看到林晰,朝我们这里小小地挥了一下手手,女里女气的,说不了几句话就不自觉地脸红一下。我不得不承认,他可能真的对林晰有意思。林晰招呼他过来坐下,对我说:“这是安德瑞。”然后转向那个男人,指着我说,“我女朋友杰妮。”名字是编的,身份也是胡扯的,我在桌子底下狠狠一脚踢过去,他面不改色,一脚踢回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出现断了那个安德瑞的某种念头,他们很快谈成了。最后,安德瑞问他:“你女朋友能不能来当模特?”我愣了一下,林晰也没立刻回答。看我们都不表态,安德瑞补充道:“她很不错,一半摇滚,一半学生气。”那天我穿了件黑色的粗呢大衣,里面是衬衣、毛衣和牛仔裤。大衣是校服没错,脱下来扔在旁边位子上了,而且实在没看出摇滚在哪里。不过,我还是很得意地朝林晰吐了吐舌头。“只要价钱合适就行。”林晰回答。“我最多只能出五块钱一个小时,再多我就破产了,一个晚上拍完。她也不是专业的不是吗?”“干吗?”林晰问我。“行啊。”我托着下巴,懒洋洋地说。于是,在我想起来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五块五之前,我就把自己给卖了。我后来才知道,有媒体把模特评为十大垃圾职业之一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当你的小时薪水只有五美元时。我质问林晰,为什么只有五块钱他也没帮我讨价还价。他回答:“你做事只是为了消遣,安德瑞说他要破产了,是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拍照片的日子定在三天之后,地点就在林晰的那个半地下室里。
因为,一直要等到那个时候,管理员才会过完他的圣诞节回来上班,才能修好那里的暖气。也就是说,在那之前,林晰还得带着帽子将就三个晚上。那天傍晚,安德瑞很早就到了,带来十几套罩着透明防尘袋的衣服,一手推着一个带滑轮的铝合金衣架,一进门就忙不迭地把衣服一一挂好,仔细地整理。林晰躲在暗室里忙他自己的事情,我一个人横躺在沙发上翻一本画册。过了一会儿,另外两个模特也到了,化妆师也来了。化妆师是女的,名叫埃里卡,穿一身黑色,装扮里面带了那么一点点不易察觉的朋克味道。她打开一个黑箱子,花了差不多两个钟头在三个姑娘脸上涂涂抹抹,时不时地抱怨晚上光线不好,还说多云天气时,下午四点钟左右,窗边的位子,才最适合她工作。我们化妆的时候,安德瑞就坐在旁边的地板上跟我聊天。他告诉我,自己在布鲁克林一个纺织成衣业者聚集的街区有个小小的工厂间,倾家荡产全都压在那个满是线头零料的地方了。说完就远远看着他带来的那些衣服,看了一会儿突然跳起来,跑过去摆弄其中一条裙子的滚边。
发型师迟到了一会儿,名叫法彼安,人很矮小,白衫黑裤,除了左手上戴了好几只镶着半宝石的银戒指,整个人看起来异乎寻常得正常,跟我想象当中干此类营生的男人完全两样。他一边弄头发,一边埋怨说妆化得不对。埃里卡跟他争论起来,安德瑞也过来凑热闹。三个人一直吵到林晰听见了,从暗室里出来,让他们挨个儿说出自己的想法,然后又说了他的意见,大家都点头,争端解决了。我像个傻瓜似的坐在高脚凳上,看着接二连三发生的新鲜事情,惊讶地发觉自己竟然有点佩服林晰了。钟走到九点,终于开始拍照片了。到那个时候为止,我已经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腿都快麻了。画眼线的时候流了好多眼泪。头发看起来很好,摸起来又黏又硬一手的发胶。我第一次知道做模特原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而更难的事情还在后面。倘若换了有经验的姑娘,摄影师可能只需要说一句:“你自己动。”然后按按快门就行了。碰到我这样的,就麻烦了。怎么站,手放哪里,眼睛朝哪里看,林晰几乎是一个一个动作地教我摆的。十多套衣服全部拍完,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其他人都走了,林晰把拍摄时用的拨拉片拿给我看,一列两寸大小的照片上,我看起来居然还不坏。
他也在旁边一起看,一本正经地评价:“你有一点蛮好的,就是不管镜头对着你还是不对着你,你都是一个样子,不会一看见镜头就变得很僵,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一点。”我得意起来,他看见我欣喜的表情,又一盆冷水倒下来:“不过,你做不了模特这一行,太放松了,没有腔调。”我不服气,反驳他:“这些照片不是很好吗?”他立刻回答:“因为是我拍的,换了其他人老早把你骂死了。”这个,我倒是承认的,换了其他人真的要被骂死了。几年之后,有个模特经纪看到过那些照片,他告诉我,那时的我其实非常适合在纽约混模特这个行当,因为我看起来有些“边缘”,又不是很“边缘”,刚好介于伦敦的瘾君子风格和巴黎的经典美人形象之间,而这个中间地带,就是纽约。对于模特来说,这是个再好不过的地方,不必太瘦、不必太坏、也不必对自己太苛刻。但是,这种折中对摄影师来说就不是好消息了。林晰总是觉得纽约太过中庸了,他始终不太喜欢这个地方,却不知道为什么待了很久很久。而我则花了更长的时间,才慢慢搞懂林晰的意思--为什么我不适合做模特?我太固执于自己了,神态、表情、动作,不愿意妥协或是改变,可能只有最宽容、最耐心的眼睛才能发现我好的一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