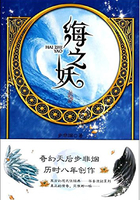今春雨水好多。
这一日,夜空劈下数道凛冽电光紫,云层里有惊雷滚过。雨水迟疑片刻,浩浩扑落下来。
顾佳音自房间走出。穿香奈尔小桃红上装,奶白蓬蓬裙,腰间有本季风靡时尚界的硕大蝴蝶结夸张至动魄惊心。
起居室内她站定了,咳嗽一声。
傅琳琅便好配合地从沙发中探出头来,回顾一眼,却立即惊笑道
——佳音,你扮成生日蛋糕做什么,可要我来将你切开。
顾佳音原为博她一个喝彩,不料得到这个反应,十分气结,叫道
——傅琳琅,你少刻薄,我不信你不曾为一个男子盛装地逢迎过。
说罢她自蝴蝶般扑出门去。
琳琅便重又捧住一册书,徐徐将自己埋进大堆抱枕里头,只作什么也没有听见。
的确。不是没有逢迎过。
傅琳琅幽黯内心似有柔光照来。
不得已地,她记起那男子温厚手掌摩挲过她细洁脊背,而床第间散落他替她罗致的衣裙。记起他说,你好瘦,接着嘴唇吻下来,滚烫如烙铁。记起彼时她是多凉薄的女子,然则再凉薄,亦抵不过柔爱二字。
傅琳琅探身取支烟来吸。一扭头见她新写篇小说刚开了头尚在电脑屏幕上,光标闪一闪。
她走往电脑前,最末一行写着
——身体是我们仅有的衣裳,始与末,初与终。
呵,是。即使众人背约了离弃了,爱憎屠戮过毁伤过,仍有肉身与我同在,如主我的神。
我应爱重应信靠,因它是我的唯一。
突然地,世间退后,天地当中只余傅琳琅及她的身体。
她愣怔着抱一抱臂。外面雨声大起来。
几日后有顾佳音一台公演,傅琳琅携大捧白色香花去贺她。
顾佳音生得美,且是真正的舞者。细骨骼,面部线条清晰妩媚。
跳起舞来似玛莎?格兰姆,有近乎透明的肢体感觉。状态好时,可以三组收腹跳横越整个舞台。
在舞中,她是未定型的肉身,存在诸多变貌。一时她冰静如尼,森然如神佛,一时又爆裂如情欲,沸沸将身化作绕指柔。
傅琳琅一向嘉许她的舞。演出结束后,便往后台寻她。
亦不过隔着一重幕布,不察觉竟换了人间。
在后台,舞者猫般来去,双双足趾皆隆起如弓。舞衣为轻薄黑纱长裙,行动间洁白脚踝闪一闪。看上去十分玄远诡魅。
一抬眼见有男子站在佳音面前,抱血玫瑰烈烈似一团火。
琳琅素厌红色,嫌它太放,嚣艳全无节制。然而那个红在这个人怀中,不知为什么竟显出伏帖样子。
宫花寂寞红。
佳音把他介绍给琳琅,蒋广捷,她说。
琳琅于是便知,这就是那令到顾佳音盛装逢迎的男子。
呵,他值得。
傅琳琅每周末在市立图书馆做义工已半年有余。
馆内员工皆知,这个傅小姐手脚是极勤快,人却静得很。
平常无事,便捧住一只热水杯慢慢喝,杯中有植物茎块,色泽如血污,问她,她便说是药。
又喜在沉暗旧书架间,小木梯上,猛烈日头光斑里翻看线装书。
日常与人疏淡,只与书亲近。
图书馆专用小车轮子长久未上机油,有点锈,推起来嘎咕嘎咕的。
傅琳琅将满车书推去楼梯间拐角,坐在台阶上,点一支烟来吸。
坐在那里她听到已近闭馆时间,渐有桌椅推动,脚步踢踏,本来不多的人,不久散尽了。
这时她便起身,水槽内切切摁灭了烟头,将车推去出纳处,同老李交割清楚。
老李五十岁上下,生着一张皱巴巴的小面孔,抬头跟她讲
——琳琅,你是我所见义工当中,最勤力的一个。
她就笑一笑,也不说话,自去衣帽间取了外套穿上。走时又听见老李说
——外间落雨,等我找把伞给你。
她只说不用,径走往雨地里去。
是黄昏,因着有雨,四下行人稀少。
痛经是在这时候开始了,自体内浩荡涌起来。
琳琅起初还只管耐受着,放慢了脚步,等痛楚过去。
谁知它竟不依不饶,愈演愈烈,一浪高过一浪如海啸,直要吞了她。
小腹处似有钝刀子旋转绞动,疼痛寸寸侵入七魂六魄。
琳琅双腿颤抖,支撑不住,只得握牢人行道栏杆,缓缓蹲下,满额是汗,满手都是雨水。
她这才有点慌,疑心自己将要死了,赶忙拨一记顾佳音电话,却是对方正在通话中。
昏迷前那片刻,傅琳琅仰头看见长风来,高大乔木叶片随之倒伏,闪出银绿背面如大片夜光海。
梦中,傅琳琅惊见黑马自天际线上猎猎奔来,巨大马蹄不知如何滚雷般踏上她的前额。
她头痛欲裂,在口渴与不安中醒转。
醒时她觉一切熟悉。
白床单,被子麦白色,枕边一册和合本《圣经》,正翻开在《马太福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