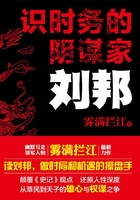——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这不是她的床么,她的书,还有她昨夜的阅读。
傅琳琅简直吃惊,只好当自己仍在发梦。
于是翻一个身,重新合上眼,跟自己说,再睡一会儿便真正该醒了,醒来若是仍在大街上,就要打一辆车回家。
这时顾佳音见她睁眼翻身,长吁一口气
——琳琅,你好吓人,竟在马路上晕倒。幸亏有同事送你回来。
傅琳琅这才认定自己是在现实世界,将心神收拾拢来,把身体缩一缩从床上坐起。
而顾佳音提及的那名同事此刻正站在门口,白衬衫牛仔裤,干净挺拔,独一双眼黯黯明黑,有无数暗涌。
呵,琳琅认得他。他亦是在市立图书馆做着义工。有时书架间逡巡,彼此遇上了,也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然而他今次又是如何,自城市的荒凉海中打捞了她,且又这样精确地送了她回这间房这张床的?
真正匪夷所思。
当然,对那男子却是轻易
——图书馆有每个义工详细档案,查一查便晓得。
接着他又道
——傅琳琅,至少你应该问一问我的名字。我叫乔海烁。
乔海烁认识傅琳琅已有很久。
他知每个周末她是如何骑一架破旧男款脚踏车去图书馆,有时也步行,手指间总离不得一支烟,
他知她读六朝志怪小说,每回是怎样以指甲印子做了记号,归还架上,下次有空接着读。
他知放工后她亦去撞球室玩两杆,最善击中袋,其间要一瓶啤酒来喝,不理会搭讪,不同人交际。
琳琅只是黯淡往来,但自有一环光在她的身上。
她不自知,却被乔海烁看到。
——琳琅,初见时你予我印象只是瘦。那么瘦,乃至叫人担心图书馆蓝色大罩衫会得压坏了你。长一张清水脸,没有血色,擦身而过时,闻得见你头发里烟草味道,及衣裳间中药气味,我想你是生着什么病吧,又不敢问,又羞怯于接近,只远远看着。看着已经很好。
——辗转才知你写小说,我便尽数找了来读。是自第一行这些文字就困囿了我,使我再不能坦然去看去思考。即使我不认识你,我也要说这写字的人太残忍,对读者,对自己。你是生生将繁丽城池废毁成荒原了,还不许人为之一哭。我掩卷只希望你能够快乐一些。
——我不知自己这样是否已算是爱着你。但我想爱这种关系充满悲伤,不小心便痛彻肺腑,远非吉兆,反倒不祥得很。又且事实上,我并不确定自己还有那个能力来爱上一个人。我把一切都告诉给你,由你来裁决。我甚至庆幸于你这一场急病,因除开它,我找不到其他结识你的方式。
琳琅接受乔海烁这一番表白,温和看着他。
这男子眉目疏朗,最难得是眼珠漆黑如沉和夜海。呵,只是他出现得实在实在太晚。
傅琳琅只觉疲累不堪,更一早厌倦了再去摸索着了解一个人,继而决定爱他或不爱他。她没有力气了。
这倦殆的症状是从早先就开始。
当曾经有男子在微暗天光中抱着她杏仁白身体,对她说
——琳琅,不如我离婚,然后我们在一起。
而她回答他
——呵,不必不必。我没有爱你到那个地步,要背起破坏你婚姻的罪名。
是那个时候,她已患了乏爱的疾。
佳音上回演出时的舞台照已放大送来,霸占起居室整面墙。
巴洛克风格黑橡木边框中,舞者顾佳音吊起眼梢,眉上有妖丽胭脂扫入鬓角,跃起时如不在人间,大幅黑纱裙裾挥开如巫蛊般铺天盖地。
琳琅静观良久。
之后,叹一口气,她说
——佳音,我知,舞者其实有多寂寞。
舞者倾其一生关注自己的身体,塑造它,超越它。
她与自己的身体亦敌亦友,却要朝夕相处,即使厌倦,亦片刻不能离弃。
且舞源于巫祭,本为高蹈原欲而生,但真正的舞者却必要懂得控制,懂得如何使肢体摆脱大地的力,跃起,在空中停顿。
她用肉体创生一个城国,但她却不是这城国的君主,而是臣仆。
呵,多寂寞。
佳音近前搂一搂琳琅的腰
——我懂你意思,琳琅。你的身体可好些?前日几要把我吓杀。
琳琅便笑一笑
——呵,那时我也怕。但后来想一想,死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到众人中去。听起来也不算太坏,是不是?
——琳琅,你是看得通透了。但痛到那个地步,有没有想过来世要做男子?当然了,其实做男子唯一的好,亦不过只在于不会痛经罢了。
——呵,而连这一点也是他们以不能生育为代价。佳音你看,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两人笑一回,不知为什么都觉内心有深深空洞,对住里面喊一喊,会得传来幽怖回音。
然则她们所能做的,亦不过是柔和抱一抱彼此肩膊,自去洗个澡睡了。
事实上,女子间的相互慰藉,与男女之间的,一样少,总是不够多。
傅琳琅同乔海烁日渐熟识。
是她放宽了心,看清楚她跟他两个,亦不过是在浪荡浮世里,阴差阳错遇见,彼此伴上一程。
到几时,有多远,是否走在情字路上,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要知道。
于是图书馆内工作清闲时,两人便用海烁的笔记本观片。
傅琳琅看电影全无品位可言,烂片亦看得下去,闷片更吓不退她,而每每出现血腥暴力,海烁偏头看时,却只见幽暗中她目光灼灼,小扁面孔上甚至有几许兴奋神色。于是他知,她体内始终是有些好勇斗狠的成分在,不管她每一日是吃着怎样简素的饭食,带着怎样寡淡如尼的表情。
两人一道看情色片亦不觉尴尬。
一回,屏幕上出现男子自慰场面,傅琳琅竟转过脸来问他
——你呢,你习惯用哪只手?
而另一位则没有半点迟疑,坦荡答
——用左手多些。
琳琅奇道
——难道右手不是更灵活?平常又不见你是左撇子。
乔海烁便咧咧唇角给出劲爆答案
——但右手要拿鼠标。
闻言,琳琅简直绝倒,放肆笑出声音。
海烁便伸手掩住她的嘴。
已是苦夏,图书馆老式空调机发出轰鸣,冷气不足,他跟她都是一额细汗。
两双黑眼睛对望,那片刻,静到极,听见彼此鼻息。
午后的日光柱,弥弥尘烟涌入一排排书架间,要漫上他们胸口,要埋没他们,要摧毁他们之间摇摇欲坠的默契。
而乔海烁徐徐移开了他的手,吻下去。
顾佳音与蒋广捷的婚期定在下月。
他送她的蒂凡尼戒指,钻石过分的大,戴在手指上,石头歪在一边。
接连几夜,琳琅屈腿坐在椅子里,下巴抵住膝盖,隔着门听佳音在邻室来去,带出离散前最后的嚣闹。
夏日房间中十足的冷气冻到琳琅脚趾发白。
她以微弱音量播放Sophie Zelmani。这瑞典女子有一把嗓音纤细透明如玻璃。她所有的歌听上去都像是同一支歌,而她甚至不晓得自己是悲伤的。
琳琅不无怅惘地想,不久后,这间屋将又只得她一个人了,还有这些歌。
佳音敲敲门进来,对琳琅说,起居室墙上大幅舞台照留给她,且又和气同她讲
——它跟你在一起,我是放心的。
听她这么说,琳琅几欲堕下泪来,好歹吸一口烟,将那点酸楚压下去了,只说不出话,一双眼望着佳音。
这时佳音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