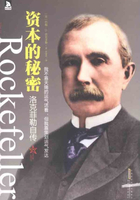——呵,良姿,我发现你多么像一个岛。
——傻话,这怎么说起来的?
——岛是天生孤绝,不落情缘,同你多么相似。
——呵,我眼前不是还有一个你,充其量算个半岛吧。
这样说时,温良姿探身自丁轻手中拿过那本《国家地理杂志》,翻一翻,然后对她说
——庄焰回来了,你可知道?
丁轻倒是极淡然
——呵,今早恰在杂志上看见。他终于有了名气。
——是。连绯闻女友一并有了。
男子,呵,男子通通如此。
温柔的话语言犹在耳,一转身他又爱了别人。
下一回,再下一回,他情归何处丁轻全然不愿去理会。她还不至于相信自己是那么大气的人。
——会否再爱上一次?
——良姿,难道你还不懂得我?对同一个人我只能够爱一次,若下回他卷土重来,呵,对不起,我的爱消失了。
多聪明。
鸳梦重温是这世上最煞风景的一件事。
七月,温良姿出席丁轻的毕业典礼。
去得迟了。
远远地,她看见丁轻站在同学老师当中,穿着宽大的学士服,显得较平常乖觉很多。
嘴角木木地亦懂得挂住一个笑容,见有人同她讲话,亦会得抬起头来寒暄。
望见良姿,神色却即刻生动起来。按住帽子朝她跑去,将所有人甩下不理。
那个样子似是在说,呵,其他的人通通可以去见鬼。
后来良姿便问丁轻
——为什么不把真实的自己表现出来,好让其他的人懂得?
丁轻漫笑一笑
——呵,我要那么多懂得来做什么?
那一日丁轻穿白衬衫,站在临河的露台吹河风。
七月的阳光照在她的黑发,她的尖俏的白面孔。
饶是摄影师温良姿一向阅人无数,此刻仍不得不在内心又叹服一回她的好气质。
一个女子若不小心长出了灵魂,效果就是有这么可怕。
停一停,丁轻又说
——良姿,你可知,因总是不被爱而生的自卑,在我这里它变成刺,使我不能靠近别人,而别人亦不可以靠近我。真正悲哀,可是?
温良姿并不料丁轻竟会同她讲出这样曲折深透的话来,仔细打量她面孔,却只见自嘲,不见哀戚。
于是良姿便知,丁轻对此是真正有五内俱摧的伤痛。
——但必定有人爱你,只是这个爱不被你知道。
——呵,良姿,或者如此。然而那种隐秘无望的爱,对我有什么用呢?又不能吃,又不能抱着取暖。
这一年温良姿已经五十三岁。
一年后,她因癌症去世。
遗嘱里将她的摄影工作室留给丁轻。
她的遗像却是三十年前的旧照,那么年轻,双眸如星子,面颊上一个梨涡当年必定曾颠倒过众生,那么销魂。
后半生中,摄影师温良姿竟没有为自己拍下任何一张相片。
呵,她不想记录时光。
是,时光永远较我们早到一步,对待我们,如猎人对待被诱捕的兽。
那么残酷。
但又不是不自然的。
葬礼当天的那个夜,丁轻走进良姿的暗室——
温良姿的私家重地,从来不放任何人进入。终年只见门开阖时有红光闪一闪。
像瑰丽诡异的秘密。像良姿的心。
红色灯光中丁轻徐徐深入,见四处凌乱,似是良姿明天便会回来。
头顶细绳尚晾晒着相片,那么多,通通蒙了细尘。
丁轻好奇,凑上去看一看。呵,这不是她么——
穿着笨重老气的学士服,站在茫茫人海,若有所待。
丁轻又看另一张,仍是她。又一张,再一张,每一张,呵,通通是丁轻。
这暗室内铺天盖地挂满了丁轻。
那一池显影液中潮湿的一张一张亦都是丁轻。
她对着别人说话,神色不耐烦。
她睡着了,表情甘美如一只婴。
她醉酒,皱着眉头。
她站在雪地里望天空,手揣在大衣口袋里。
她跑,脚线颀长如鹿轻捷如豹。
丁轻几乎可以看到温良姿是如何站在这显影液的面前,等待丁轻的形象慢慢浮现。
她亦可看到良姿的手势有多么温柔。
该刹那,丁轻突觉心痛。
她痛得蜷缩在地上,像被灼伤的虫。
终于她将额头抵住自己的膝盖,哀哀哭起来。
次日,丁轻自地板上爬起来,走去洗一把冷水脸。
她在心里对良姿说话,一如良姿在生之时
她说
——良姿,终于我想明白了。人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
不久丁轻做了一个梦。
梦中有漫天大雾。河对岸传来急促鼓点,并有一个身影,渺渺茫茫地朝她挥手。
之后,那身影退隐,远遁,消失。
醒来时丁轻听见街上夜猫凄厉地叫,又有水喉发出哮喘病人般的“隆隆”声。
她有淡淡怅惘。
她知,这世间的情缘加诸她的刑已经期满。
她再也不能爱了。
有一夜,回家时,我看见街角的小公园里,蓦然地开出几树红白樱花。
其下有褐衫老者静静坐。旁边搁一具无线电收音机,电台播一支陈旧的歌。
Seven Lonely Days。七个寂寞的日子。
我站在街头听完它。
月光里,花树有极清寂的形与影。我的心中涌起些欢喜及安静来。
这时候我想起这支歌原是白芙爱听的。
几年前一个将雪的黄昏,白芙找到我,要我替她接一些生意来做。
那一日,她穿式样极简的黑衣,一双眼懒洋洋看住我。
分明她是在求人,但半点不带哀恳,姿势是绝不讨好的。
我仔细地听她说完。她说话时若停顿斟酌,会以她的齿咬一咬下嘴唇。
之后,我抬头望了望天空。
这日的云层自天光时便压得极低,令人呼吸不畅。有一只白鸟振动宽大翅膀缓缓飞过。
一切都来叫我深觉生命冗长,至无以打发,
于是我便多嘴问她一句
——从前你是有经纪人的吧?
她怔一怔,旋即向我展颜笑起来,露出兽一样的白牙齿。
这突如其来的艳光几乎令我招架不住。
而她说
——是。但一年前我已枪杀他。
我不相信有这样坦率的杀手,当然不将她的话当真,只笑着接上去
——呵,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就此上岸?生得这样好看,做演员也活下来。转一份工,或者不必这样拼命。
白芙这个人倒有趣得很,只不过是初识,却也来同我讲笑,说
——恩。专演动作戏,连替身也不用,威亚都一并省去。
我觉这女子趣怪,伸出手背,让她写电话同地址在上面。
她租住不错的地段,是不肯薄待自己的人。
我与王家卫《东邪西毒》中的欧阳锋做着同样职业,有同样苍凉的心境,亦会得跟人说
——这许多年来,总有些事你不愿再提,或有些人你不愿再见,……
说时,疾风吹着我的头发。
白芙不是生手。相信她在十三岁已懂得拿枪杀人。
又晓得随身带小块湿润黑布,防开枪后拆卸消声器烫手,十分专业。
最憎毒贩。胸口上总是给多一枪,似泄愤,当然,或者是习惯亦未可知。
她从不伤及妇孺,是真正的杀手。
一开始我便同白芙保持着疏淡的关系。
我与她心照不宣,从来只在寥寥数语间,交割着旁人的性命。
但我对她十分公道,替她接生意,保守她行藏的秘密,当然,我亦抽取不小份额的佣金。
无疑我们是这妖兽都市中最和睦的工作伙伴,不用相互践踏,将对方肩膊踩烂,以求出人头地。
可惜我们极少见面。
走在暮春时节人潮涌动的街头,我与白芙亦未必认得出对方的面孔。
人生若只如初识。
一回接到一单生意,连续两日我拨白芙电话,长久无人接听。
呵,是否她又搬家,忘记通告我。
我所知,白芙的嗜好便只在迁徙。
三数月便要搬一回,其实亦不过是从一个出租房移到另一个出租房。
永远是睡在暂时的床上,看别人的电视机,用陌生的炉灶做饭来吃,它们甚至不称身不称心。一切都是不相干的。
呵,白芙要的就是这点不相干。
我明白在内心中她是欠缺安全的人。甚至时间带来的那一点熟悉跟眷恋亦会叫她害怕,忙不迭回避。
而她搬家的确可以说走便走。因身无长物。
收拾起来不过薄薄一只手提箱。衣服尽是黑色,甚至没有化妆品。
呵,她并不认为让警探走抵凶案现场吸一吸鼻子然后说,恩,这杀手用的香水叫做午夜飞行,这情节是多么的戏剧性。
在她看来它只会是荒唐,连趣味亦欠奉。
这样想时我便已走到白芙家门口。敲一敲,无人应。
我取锁匙开门。
即刻有歌声荡荡袭人而来。我听见那支歌,七个寂寞的日子。由女歌手一把厚且哑的声线唱出
——Seven lonely days I cried and I cried for you
屋内光线暗,有闷湿气,乱拳般打上面孔。
电话叫大堆杂志抱枕埋住,不留神我一脚踹它到沙发底下。
一台笔记本兀自忠心耿耿地播着那支曲,液晶屏幕反射幽幽微光。
转进卧室,至床边,我见白芙孵在被单里。
头发乱蓬蓬,几线发丝被她不顺畅呼吸吹动,滞重地飞一飞。
我俯下身去看她,尚未挨近已觉她烫,那热气迫近到我的呼吸我的面孔,我便也似要烧起来。
呵,是这样。
我以为她至少身中十枪八枪,正独自倒在床上抽搐流血死去,谁知竟不过是重感冒。
要到这时我才惊觉白芙原本亦不过是个女子,有血肉有病痛。
而许多年前,她更不过是个小婴儿,让父母抱在怀里,粉嘟嘟,似一团雪。不会有谁想到今后她操刀为业,杀人。
我做大缸红糖姜茶给她,又以文火煨了鸡丝粥。
她醒来,见到我,亦并不特别诧异,只看我一眼,眼神凉且薄,似我不过是屋中一件陈设。
她闭着眼大口喝下姜茶。
嘴唇这才涌上些血色,汗水濡湿的几弯卷发贴在颈项,她像布格罗画里的女子有慵懒精致的面孔。
她仍是闭着眼,但嘴角向上扬起,是一个微笑的样子。
我醒悟过来这个笑容原是给我的,就走过去,以手指轻触她的唇角,收取它。
这时我对她说
——白芙,不是每一个杀手都必须这样寂寞。
我想起我其他的合作者,哪一个不是鲜衣怒马,夜夜笙歌。
最懂得以己之所有换己之所无。
而他们的快乐又十分简单,皆是能够到手之物,不外乎香车美人,还有可以放怀一醉的好酒。
人生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自己造出幻觉,自己相信。
只有白芙,呵,始终我不知她要什么。
她是夜行的兽。擦身路过繁艳的梦境,却不肯现身不屑沉堕,连璀璨皮囊一并隐遁在暗地里。
白芙似倦极,对我的话没有任何反应。
于是我又说
——像你这样做杀手,已经过时。
她仍是不搭腔。靠在枕中,表情十分平静。
——甚至你连女性朋友也没有一个。
我接着讲,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要激怒她。
这时她却笑起来
——呵,要女性朋友来做什么,不外是得闲坐在沙发,捧住咖啡杯,互相说起自己有面首若干。
我听她这样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直要不寒而栗。
而跟着我竟然又问出一句蠢话
——难道你不怕寂寞?
她别转面孔,认真想一想,继而说
——有噩梦恒久来做伴,怎会寂寞。
四月暮春,我起居室中那一架荼縻终于已要开尽。
微黄的花朵干枯堕地,时时发出细碎声响,像脚步,像离开。
白芙开始往我处坐坐。不再同我生分。
但她永远心不在焉,有时同我聊天也睡着,醒来竟跟我说
——不知为什么到你家便有无限睡意。睡一觉,半个梦也没有,醒来清清爽爽,如同新生。
呵,我能说什么呢。总不至于要向她收取催眠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