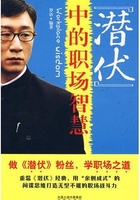我从黑暗中醒过来,浑身酸痛不已,刚想伸展身体,却发现朵朵躺在我的脚边,沉沉地睡着。
我敲着头,想出去找水喝,慢慢摸索着走到门口,出了房门,按亮了廊灯,我下意识的环视这间屋子,是熟得不能再熟了。以白灰为主色调,简洁而大气。只是到处摆放的毛绒玩具,陶瓷雕塑,使整个环境显得很是不伦不类,那是我的“杰作”。
我那时总嚷着这房子太空虚,太严肃,所以,时不时地鼓捣一些小东西来布置这里,一航每每看了,总忍不住皱眉,不过,倒也没有把它们扔掉。没想到,这些东西如今还在。
我转了个弯,才看见一航坐在沙发上吸烟。印象中只有一次见他抽烟,那是多久前的事了?我想不起来了。他是这样冷静自持,从不沉溺于任何事物的。
他看见我,掐了手中的烟,对我说,“染笙,过来。”
我径自向厨房走去,没理他。
不过去,我就不过去!
我喝了水,转身看见一航站在厨房门口,对我说,“染笙,你回来了。”
“多久?”我问他,没头没尾的。
他笑,“三年,你已经变成大姑娘了。”
原来才三年,我还以为已经三十年。
我想到这里,对他咧嘴一笑,大着舌头说,“我头痛,先睡了。”
他却不放过我,明知道我已经醉了,他还认真地说教,对我说,“染笙,醉酒是轻浮之举。只有浅薄的人,才会喝醉纵酒。人必自爱而人爱之……”
哦,我听明白了,他是在说我轻浮,说我浅薄。三年了,我努力改造,想把自己变成他喜欢的样子,却只得了这么一个评价。
我洁身自好,努力学习,天天向上。我不染恶习,我努力生活。我不能这么轻易就让人瞧低了去。
我对他摆摆手,说,“哦,知道了,我可以去睡了吧。”
再度躺回床上,我却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几次,惹得朵朵嘟囔着发出抗议,抡起胳膊没轻没重地一记打下来,疼得我眼泪哗哗直流。哭得累了,昏昏沉沉竟也这样睡去。
第一束阳光照进屋子的时候,我就醒了过来。我躺在床上,我开始反思。昨天真是太失态了,我修炼了三年,怎么一回来就差点泄功?不过,我立即给自己找了一个好借口:我不是刚回来吗?我不是三年没见一航了吗?所以我一时情绪激动也是情有可原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再没把那句话挂在嘴上,即使我昨晚喝得半醉我都没再说。我出去三年,明白的最重要的一个道理是,女孩子,绝对不要主动向男孩子表白,任何情况下都不要!
我犯规了一次,我绝对不会犯第二次。我不是顶聪明,但我是也很聪明的。我明白了,策略,策略。我再也不能如三年前那个清晨那样把一航吓跑了。
三年里,我很克制地没有如从前一般时时骚扰一航,我给他发的email少之又少。字里行间斟酌又斟酌,多半是异国他乡的风俗民情,其实,随便去书店买一本旅行杂志都比我写得有味道。到信的末尾,我会极简洁地带上一句,“一切都好”,“勿念”什么的。
他倒好,回信比我还短,不外乎,“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或者是一句节日的问候。
我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耐心地听着我妈唠嗑,张家的儿子娶媳妇了,王家的女儿有男朋友了,我不心疼电话费,我小心翼翼地把我妈往那个方向引,尖着耳朵细细地挑出我想要的消息。一航出国培训六个月,一航端午中秋春节都没有回家。当听到我妈说一航心绞痛住了两个星期院的时候,我告诉我妈,我要回归了!
朵朵很仗义,当下就决定放弃那个难搞得要命的德国佬皮特,和我一起奔赴祖国母亲的怀抱。飞机在东京转机的时候,我在机场转悠,买了一本好书,叫,《追男100计》,还是中文版的。我捧着它,从东京看到北京,研究了很多遍,直感叹我以前真是太没策略了。
书的扉页里写了一个笑话,说,“首先你要漂亮,若不漂亮的话你要温柔,若不温柔的话你要有内涵,若没内涵的话你要学会撒娇,若不会撒娇的话你要善良,若不善良的话你要有学识。若没学识的话你要有魅力,若没魅力的话你要主动,若不主动的话你要有妖气,若没妖气的话你要学会忍受,若不会忍受的话那只能看缘分了。”
我问了朵朵,她说,“阿笙你很漂亮,你真的很漂亮。”
我记得一航也说过,“我觉得你就是美女。”
哼哼,我是不会对别人说自己漂亮的,但我经常对着镜子说你好漂亮,你真的很漂亮。
所以,先决条件我就满足,至于下面的什么温柔啊,内涵啊,撒娇啊,善良啊……都是很重要的备用条件,虽然我没占全,但也有十之五六了。
《追男100计》中第一计叫作“欲擒故纵”,我趟床上又深呼吸了两次。决心下得差不多了,这才穿衣起床,去洗手间洗漱。
我开了房门,居然听见一航在阳台上讲电话。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大概是为了不吵醒我们,他把阳台和客厅之间的落地玻璃门也拉上了,一边的窗帘还没有拉开。我隔这么远,只能听到蚊子一般的嗡嗡声。
这么早的电话,肯定不会是公事,是不是那个李筝?我越想越觉得有可能,纠结了半天,终于情感战胜了理智,我蹑手蹑脚地靠近玻璃门,躲进窗帘后面。
我耳朵贴着玻璃门,一航的声音很清晰,“……昨天的事,你不用那么客气,我和于家也有生意往来的。”
……
“她是在我这里。”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一航没有说话,正当我惊慌地以为他已经讲完电话时,耳边传来一句,“李筝,你说的,我心里都有数。”
有数?他有数什么?我偷偷地扒开窗帘,只看见一航的背影,他面向远处,不知道在看什么东西,过了很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以为他就要进来,心都跳到嗓子眼,所幸,没有。
我连忙猫着腰躲进了房间,他到底有数什么呢?我想不出来,伸手推推边上依旧睡得沉沉的朵朵,却惹来她不耐烦的一阵嘀咕。
“好吧,等你醒来再请教你。”我自言自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