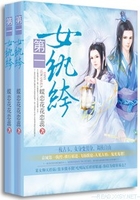这一去就是十几天。
我被推醒,睁眼一看,永璘站在面前,眉皱得紧紧的。我笑:“你怎么来了?刘公公不是说皇上最近忙得很么?”他不说话,我问:“怎么了?”小宫女已拿了椅子,他顺势坐下来,缓缓道:“你睡了在哭,自己不知道么?”是么?我伸手一抹,果然是泪水,忙擦干净了,道:“臣妾去给皇上沏茶。”他拉住我的手,道:“沏茶有宫女呢,你坐下来。”我坐下,隔了一会儿,他道:“朕这阵子事多,没顾上来看你。平姑姑几次说你挺好,你三哥也说你好,龙儿也好,故此朕便没在意。今儿从这里过,想顺路进来瞧瞧。你睡着,睡得好沉,朕不忍心叫你。可是你却哭了起来。朕怕你又给魇住了,这才推醒你。又梦到了……朕的其他妃子?”我摇摇头,梦到的是他。“不打算……告诉朕?”他又问。我摇摇头,不想告诉他,他盯着我看了好久,道:“那便随你吧,几时想说了,跟朕唠唠。你素来没有瞒朕的,朕盼着永远这样。”我低下头,孩子在腹中动将起来,一个劲儿地往他说话的地方踢。我拍拍它,它不理我,我抬起头看他,他诧异:“要朕?”我点点头。他将手放在我腹上,胎儿很欢喜的样子,一会儿踢踢这儿,一会儿顶顶那儿,似乎在逗永璘跟它玩。永璘也笑了,道:“唔,会玩了?好!”我低低道:“它想皇上陪它玩。”“朕就陪它一会儿。”永璘慨然道。我低低教给他如何跟它玩,他很快便学会了。逗了它一会儿,永璘道:“好龙儿,爹爹要走了,过一天再来陪你跟你母妃好吗?”胎儿竟慢慢安静下来,象是听懂了一样。永璘笑了,收回手,道:“朕走了,过几天来看你,不许哭了,朕在承庆殿听的见的。”我点点头,目送着他离去。
过了几天,刘公公过来告诉我,叫我去奉乾殿侍驾。我便去看永璘,他偶感风寒,靠在榻上,以手支额,正跟三哥下棋。我走过去,略蹲了蹲坐到他身边。
病中的永璘慵懒,随性,精神不如往日。连下棋也是懒懒的,三哥也知他精神短少,没有步步紧逼,每一手都留了余地,虽是如此,永璘仍是输了。内监端了药已站了一会儿,见是个空儿,便呈了上来,永璘饮完,放回碗,我拿了一枚荔枝,去了壳与核放入他口中,他慢慢嚼了吃了,道:“颜立本的事,该结了。”三哥道:“是,若无罪就该放,若有罪就当呈报罪状,这么拖着日复一日,万一他吃不了狱中的苦,就又是一件莫须有的案子啦。”永璘道:“唔,刘全。”刘公公应:“是,皇上。”永璘道:“你去传朕的口谕:明天叫刑部早朝后押颜立本入宫,朕要亲审此案。”“是。”刘公公去传旨,永璘推开棋秤,我忙让人收了去。永璘问:“稚奴怀了——有七个月了吧?”“回皇上,七个月零二十天。”“唔,才七个多月?”永璘道:“朕——有些等不及了,后宫——分了朕的心了。”三哥冲我笑笑,道:“是,红颜祸水。”我轻啐他一口,永璘亦笑:“不要开这种玩笑,没有你妹子,朕——不知生之趣。”他大概是生病的缘故,说话很慢,亦有点悲伤的神色。三哥轻轻道:“皇上疼爱她,亦需珍重龙休。勿陷过深,情深则不寿,古今皆然。”“情深不寿?”永璘看看我,忽地咳嗽起来。“皇上。”我忙去扶他,拍他的背,帮他顺气。三哥倒了杯茶,递给我,我喂永璘喝下,他渐渐止住咳,看了看我跟三哥,道:“你说的何尝不是呢?”下面的话却咽下了。三哥道:“皇上跟娘娘说话吧,在下告辞了。”永璘摇摇走:“你不用走,朕跟稚奴也没什么样话要说,她的心朕知道,朕的心她亦明了,朕叫她来,不过是想她陪在朕身边罢了。”我放开他叫人去熬燕窝粥预备着给永璘喝,再回身坐下,听永璘问:“你母亲可好?”“劳皇上惦念,家母甚是康健。”三哥道。“那便好。”永璘道:“过些日子,朕打算让她进宫照顾稚奴几日,也可让稚奴见见母亲。”我道:“谢皇上。”“你我还用的着这个字?”他颇嗔怪地看我一眼。三哥道:“那在下替母亲谢皇上殊恩。”永璘问:“四弟——浏阳王近日有没去过你家?”三哥答:“自皇上吩咐后,浏阳王对家里多有照拂,也常常去看望母亲,跟母亲在一起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永璘问:“你母亲——对四弟可有教诲?”三哥道:“母亲从未向在下等提过与殿下所说之事,便说殿下懂事,孝顺,率性,是性情中人,且身世堪怜。”“懂事,孝顺,率性,性情中人?”永璘喃喃重复,叹了口气,道:“四弟有老夫人教导,朕也算对的起母妃在天之灵了。”转头向我道:“你母亲似乎甚是喜欢四弟呢。”语气中有点酸溜溜的,似伤感也似嫉妒。三哥笑道:“母亲也疼怜皇上,说起浏阳王时还夸皇上爱惜弟弟呢。说天子之家,有这份真情亦属不易,母亲自我两个妹子代针线后,已多年不动针了,上个月做了一双鞋,本是要呈给皇上的,因多有顾虑,二哥又一力阻拦才没进呈,如今还搁在那里呢。”永璘脸有喜色,道:“让她拿来吧,朕也很多年没穿家里人做的鞋了。”我笑道:“皇上是拐着弯子骂臣妾懒呢,那明儿起臣妾就做双鞋,皇上可不许不穿。”他笑着拉起我的手,道:“朕没怪你,你身子重,朕也不要你伤神,以后再做便是,你做的东西,朕从来没不用过。这个等下你问刘全便知。”顿了顿道:“下个月是四弟的生日,你帮朕记得点儿,朕要去王府替他暖寿的,旧年就答应他的。”我道:“是。”又道:“皇上养养神,臣妾叫三哥抚琴可好?”永璘嗯了一声,我拿了靠枕放在他身后,扶他靠下来,让人给屋里换了水,重新沏了金山翠芽放在他手边的几上,又叫人去取永璘的琴来给三哥。“你不要忙。”永璘合着眼伸出手,对我道:“让他们去做,你坐到朕跟前来,陪着朕就行了。”我答应。接过扇子坐到他身边的椅上,给他打扇。“坐到榻上来。”他又道。我道:“皇上怕热的。”“朕让你过来。”他道。我只好移到他的榻边坐下。他仍是一手支额地侧睡,一手却放到我的腹上,嘴角带笑,听三哥抚琴。
永璘睡着的样子极其放松,象一个婴儿,我极爱看他这种神情,因此时他不是皇上,不是九五至尊,只是我的夫君,我疼惜他,更同情他,总盼着他一辈子都这么放松,不要忧心。一手打着扇,一手不时替他擦额上沁出的汗。他极少生病,若不是乏极了,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躺下休息,他一直是以国事为先。象今儿,生了病还要上朝,一头心里怨着,一头怜着他,若不是碍于三哥在,就要抱他在怀里,细细地疼了。
“娘娘,太皇太后来了。”太监进来低低地回禀。我推醒永璘,刚刚站起,太皇太后进来,忙请安,她仍是淡淡地:“都起来吧,皇上还靠着,德妃坐着,萧小哥儿仍抚琴。”她虽这么说,却是无人再放肆,各自坐了,她也坐下来,看了我们一眼,道:“我在宫里闷了,便出来散散心,听说皇帝病了,顺道儿进来看看,皇帝这会儿觉得怎么样?”永璘赔笑:“子风已经给孙儿看了脉,吃过药了。孙儿觉得身上松快了许多,不碍事了,倒劳皇祖母惦记。”太皇太后点点头儿:“皇帝从小身子骨儿好,这些年又常习练着骑射,不过偶尔感了风寒,我瞧着也是不相干的,德妃已经怀了七八个月了,皇帝不该折腾她来,让她再为皇上操劳。”我忙道:“不相干的,臣妾也不放心皇上,本也要请旨来侍候的。”永璘笑道:“是,孙皇本没什么大病,因好些日子没见她了,心里惦记,便用了这个借口接她过来,并没敢叫她侍候朕。”太皇太后道:“这才是呢。我瞧着德妃的身子,比前次见重多了,七个多月是个坎儿,皇帝留心着别早产喽。”我脸红。永璘道:“孙皇也怕呢,毕竟怀了那么久了,所以叫子风多进来看看脉,防着点儿,孙儿也吩咐了平姑姑,一应劳神的事儿,都劝着稚奴不要做,只让她安心养胎。”“这才是体贴人的孩子。”太皇太后赞。
语峰一转,仿佛不经意地道:“我听人说颜立本贪贿下了狱了?”“是。”永璘道:“奏他的本上说贪贿三十万两,孙皇正着人查呢。”太皇太后道:“户部是个肥缺儿,谁都想伸手。三十万两可不是个小数目,皇帝要仔细查清楚。这颜立本先帝朝时就见过,看上去是个老实人,没想到也这么贪。若朝廷的官员个个都象他,朝廷也完了,国家也完了,皇帝要小心。”永璘似有难言之隐,没接话儿。太皇太后道:“我知道皇上一向恋旧情儿,颜立本在奸党横行时又帮过皇上,皇上不忍心办他。可功是功,过是过,就好比一只狗儿,为了护主咬死了人,就不能说这狗有了护主之功就不追究咬死人的罪。皇帝,天下大了,事儿也多了,若是官儿有了错为了有功就放任不管,那以后就收服不住人了。所以这人该杀的还是要杀。”从也嘴里吐出这个杀字来,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就大了,忽然明白,定是有什么人已经在她面前告了状要治颜立本于死地了。永璘一向以孝治天下,太皇太后说要杀,他若不听便是不孝,这个大帽子一扣上,以后他的话就难有人听了。我一紧张,胎儿便动个不住,我死死抓住衣裙,拚命忍着,汗早如水一样淌了下来,太皇太后装没看见,似乎立心要永璘表个态,永璘低头皱眉想主意,屋中一时静得连根针落地都听得见。
三哥忽然叹了口气,道:“是该杀。可惜那三十万两脏款还没着落,那时抄家只抄出了十两的碎银子,还是成色不均的。找不出这三十万两,终究是国家的损失了啊。”“当啷”太皇太后手中的茶碗落在地上摔了个粉碎,她脸色一下白得要命,神情凝滞住,喃喃地道:“十两?”“是,”三哥从容地道:“那日刑部抄家,皇上也怕有人趁机贪昧这笔巨款,叫臣陪着抄家的官员去看看,颜家只有两间稍显破败的房子,墙上的石灰也只刷了一半,兵丁前前后后翻了十几遍,也只抄出了十两银子,成色不均,全是散碎银两,有一块一两多重的夹剪的印子还是新的。家产也不过寻常的桌椅床凳,也都是旧的,这些都是在抄家薄上登着的,臣并不敢欺瞒太皇太后。”他说着时,太皇太后的神色已经渐渐平静下来,知道自己是受了蒙蔽,听三哥说完,她方点点头,道:“我知道你不会欺瞒我,更不敢欺瞒皇上。颜立本与你父亲当时虽曾在朝为官,但因政见不同,并无私交,你也不用替他隐瞒。皇帝!”“孙皇在!”永璘忙应。“你打算怎么办?”太皇太后看着永璘,永璘道:“刑部已过了几次堂了,也用了刑,颜立本都坚持并未贪贿。孙皇打算明天早朝后亲自审问,做个了结。”太皇太后道:“皇帝的做法是个明白人的做法。这事儿闹得很大,是该由皇帝出面做个了结了,只是须防着杀人灭口。”永璘道:“孙皇知道,如今他虽关在刑部大牢,却是单独的监房,孙皇已有旨下去,无朕的亲笔旨意不允许探监,看守的狱卒也是浏阳王安排人派的,只要他自己熬得住刑,就无碍。”太皇太后露出赞赏之色:“皇帝做事越来越稳妥了,这样我也放心了。德妃,你怎么了?”永璘这才发现我的不对,忙扶我坐下,问:“哪儿不舒服?”我摇摇头。“德妃一向胆小,”太皇太后微笑:“想是刚才说杀人吓着她了,可怜儿见的,挺着这么个大肚子还要跟着皇帝吃惊吓。”永璘的手落在我腹上,道:“动得这么厉害?子风!”三哥应声走过来,看了看我,把了脉,道:“无碍的,有点惊胎,喝几口水歇歇就好了。”我就着永璘手里的杯子喝了几口水,心跳才慢慢缓下来。太皇太后叹道:“德妃的身子也太不济了,这以后要是遇上点儿什么事儿,岂非要出事吗?”我听着她话里有话,也不敢多问,只应:“是臣妾不中用,累太皇太后和皇上操心。”“这孩子怀得真久啊。”太皇太后又道:“不仅皇上等得心焦,连我也有点等不及了。”她的话跟刚才永璘的话差不多,我心中一动,又马上摄住心神,不敢多想。宫里的事太复杂也太可怕,此刻我还是保住自己要紧。三哥道:“要是太皇太后跟皇上心急,臣倒有法子让娘娘早日平安产下龙胤……”“胡说。”太皇太后撂下脸子:“这十月怀胎,足月生产,是天地常规,你怎么能仗着自己有几分本事就违背天意呢?”“是。”三哥笑笑,也不在意,道:“是臣考虑不周,望两位圣上恕罪。”
太皇太后一脸淡然,道:“你是皇上的玩伴儿,我原先瞧着还好,纵干点出格的事儿,也不过少年心性,也懒待管,想着只要皇帝高兴就行了,可是听说你最近竟迷上了一个**,这也太出格了吧?”拿眼看着三哥,我差点晕倒,我们家最忌就是这种事,秦楼楚馆是禁足之地,三哥怎么会犯了这最重的一条家规?“你别急,”永璘在我耳边道:“先听听你三哥怎么说。”三哥道:“回禀太皇太后,臣虽有时不拘小节,有荒诞不经之处,但臣母家教甚严,臣并不敢违反家规去青楼妓馆等处。太皇太后所说**名叫青灵,是个卖艺不卖身的歌女,上次鄱阳王的二世子纳偏妃,请了许多京都名流喝酒,臣也被邀去听戏。青灵便是在那里遇上的,那时因世子酒是山西杏花村的正宗汾酒,酒味极佳,臣便多饮了几杯,微醺之下,为青灵赋了一首小令。那次过后,臣并没有再见过她。这事臣早已禀告过皇上的。”永璘点头:“子风是告诉过朕,还将那回所填小令写了给朕看,朕当时问他为何失态,他说因青灵弹得一手好琵琶,有惊天泣鬼之音,子风素爱音律,加之多喝了几杯,才做出此等之事,朕事后也叫了鄱阳王二世子来问过,证实子风所言非虚。孙皇申斥了他几句,因他事后确未有过份之举,朕也就没有禀告太皇太后了。”他二人一向一唱一和,就算三哥是撒谎,以永璘素日宠他的情形看,替他圆谎也不是不可能。但我素知三哥眼高于顶,公主名媛尚且不放在眼中,何况区区一个红楼歌女?加上历来的家教,倒也有八九分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太皇太后道:“原来如此,我说呢,你还不致于弃森严家规于不顾,公然包养**,看来是我冤枉你了。”三哥道:“臣确有荒诞不经之处,所以才授人话柄,太皇太后训诫也是为了臣的名声体面,并无冤枉可说。是臣素日太过疏狂方有今日之事,臣日后一定严定自省,收敛行止,勤修德行,以报太皇太后关爱之恩。”太皇太后微然一笑,道:“要你收敛行止,怕是不容易吧?你要是真的收敛得了,只怕皇帝又要失一知己了。”见到她的笑,我才放下心来,背上的衣早被汗湿透了。太皇太后道:“不过你既陪伴皇上读书,也确乎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被人指摘,皇帝的脸上也不好看。”“是。”三哥应,太皇太后道:“我听皇帝说当初为了德妃娘娘治病,赏了你四品腰牌,可以随意进出口宫廷,是吗?”“是。”三哥应,我便知要糟,还未及解释,太皇太后已道:“如今德妃大安了,你虽受皇帝宠爱,却并无半点官职,带了四品腰牌并不妥当,还是先缴回吧。”“是。”三哥应。永璘张了张口,却没发出声音,低下头,看着地上青砖。“就这样吧。”太皇太后道:“你再陪皇帝德妃坐坐,我先回宫了。”“恭送太皇太后!”我们齐道。送她出房。
我正要安慰三哥几句,太皇太后宫中的首领太监方正德一闪身进来,口中称:“萧子风接懿旨!”三哥跪下,道:“臣接旨。”方正德打开黄绢,念道:“今查萧氏第三子子风玉华天德,生性聪慧,出身世族,事母纯孝,伴读皇上期间,事君惟忠,谨言慎行,甚得皇帝喜爱。惟其不愿入朝为官,遂致其才难展,然匹夫之志,不可或夺,今因哀家年老体衰,终日昧昧,神思昏昏,皇帝事上甚孝,荐萧子风为哀家视疾,哀家深感皇帝孝心,着即封赐萧子风为‘玉真散人’,赐慈宁宫腰牌一枚,可奉懿旨入宫为哀家看脉。钦此,谢恩!”三哥道:“臣叩谢太皇太后慈恩。”我一路胆颤心惊地听完,至此方彻底放下心来,哼了一声,再也支持不住,倒在永璘怀中。“稚奴!”永璘忙扶住我。三哥走过来,照料我躺下,我道:“太皇太后恩典,三哥莫要相忘。”他点点头,对永璘道:“看来朝中有人要参我了,皇上珍重,若他日有缘,在下再来侍候皇上。”一揖而出。
永璘失神地站着看他离开,我拉拉永璘的衣服,他回头过来坐下,我挣扎起身,道:“太皇太后英明,替臣妾保全了三哥一命,皇上,要预备着朝中之事。”他道:“朕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看来有人已迫不及待要替朕清君侧了,哼!”我又急又气又担心,道:“皇上正生着病,这不是趁人之危么?”永璘冷笑:“你以为他们会对朕客气么?实话告诉你,一个月前,有人想在淮阳推你大哥落崖,以意外报丁缺,亏得朕早已有备,被安排在你哥身边的家丁护卫识破,这才救了他一命,你三哥前次出游便是为了这个去的。”好歹毒!看来他们是要灭我萧氏一门了。我问:“那二哥……”“你二哥在军营,又是四弟的手下,军队现在朕手里掌着,一时还没人敢把他怎么样。”他咬着牙道:“这是欺到朕的头上来了!”我道:“这此皇上为什么不早告诉臣妾?”他瞥了一眼我的肚子,道:“朕怕你经不得这些事,便一直压着没说,皇祖母今日的话已经很明白了,有人已经先下手了,连屈屈歌女一事都拿出来说事,朕看他们也是黔驴技穷了。”我缓缓道:“皇上要做什么只管去做,千万勿以臣妾为念。臣妾既已身属皇上,生死都是皇上的人。但求皇上能圣令顺畅,乾纲独断,方为天下之福。”他点点头,道:“你放心,朕早已有备。你在上元宫只管清静保胎,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管就是。”我应:“是。臣妾定为皇上保住龙胤。”他展开一个笑,紧紧握住了我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