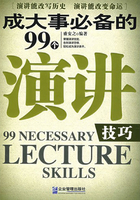“嗯……是我。”夏小北怔怔的回着,站在他身后的方向。
叶绍谦一下子意识到声音的来源,尴尬的转过身来,对着她的方向又笑了笑:“怎么过来了?就快烧好了。”
她却一点都笑不出来,只睁大了眼睛,死死的盯着他黝黑却茫然的黑眸,问道:“你的眼睛……怎么了?”
他整个人一僵,手里的铲子锵一声落在了地上。
他脸上的表情也是僵硬的,似乎还停留在刚刚微笑的弧度。
为什么……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像以前一样告诉她,没事的,只是一时不小心?哦,不,这不是真的,一定不是真的……他有一双最招桃花的漂亮眼睛,眨一眨都能电死多少小姑娘,怎么会有问题,怎么会出事?
想着,她自己也扯开嘴角,想要笑一笑,却发现那么难。正要说些什么安慰他,忽然问道一股焦糊的味道,叶绍谦最先醒过来,低呼了一声回手就要去关火。却不知为什么,那手朝着烧得滚烫的锅子就贴了上去,被灼伤的那一刻,他本能的一挥,就连锅子一起摔了下来。
他趔趄了几步,后仰着摔在地上,“绍谦……”等夏小北反应过来,第一个就冲上去把火关了,抓着他的手问,“你怎么样?让我看看烧到哪了?”
乍一看到那烫得焦黄,往外冒着血水的水泡时,夏小北整颗心都揪了起来,抓着他的手也一直抖个不停:“怎么……这么不小心,那么大一只锅子……”说到这,蓦然想起他刚才倒料酒时也是,对着锅子外面连倒了两次……
她倏地抬起头来,盯着他的脸,带着几分骇然问:“你的眼睛……是不是……看不到了?”
春雷响似鼓,到了夜间,就一阵接着一阵,仿佛来自遥远的天边,又从耳际滚过。不多时,雨点就扑簌簌打在窗玻璃上。那声音直震得夏小北心惊肉跳。
她刚说过自己这辈子都不想再进医院了,可是上午才离开,下午又回了来。也许绍谦说的对,她最近是悖运气,该驱驱邪气了,可是要倒霉也该是她,为何会报在绍谦身上呢?
病房里没有开灯,偶尔一闪而过的白光可以照见他苍白的脸。搁在被子外面的手被白纱缠了一道又一道,她方能忘记刚进来时,那晶莹红肿的血泡。他闭着眼睛,眉毛微微皱着,连入梦时都被疼痛侵扰着。其实开不开灯都一样,他不会再看见她。
戴维说:“以往他也会暂时性失去视觉。但这一次的发作,比任何一次都要来势汹涌,如果醒来时还是看不到,恐怕……”
他说不出口的,夏小北也不愿听到,他的话简直像投下了一枚炸弹,将她的思绪炸得七零八落,她都不知道眼泪怎么就不受控制的流下来了,她用最短的时间把支离破碎的片段拼凑起来,最后,终于问出一句:“他到底生了什么病?”
戴维的神色讳莫如深,一瞬不瞬的盯着她,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雨点噼呖啪啦地打在窗台上,清脆有声。
钟表的秒针稳稳跳动,一格一格慢慢走过,时间在静静流失,整间病房已经完全黑下来,她坐在床边,像个木偶人一样,脸色苍白,一动不动的握着他的手。
目光停留在他的眼角太阳穴上,戴维说,那一次在上海他车祸摔断腿的时候,顺便做了个全身检查,结果查出来有个肿瘤,长在脑袋里。这种病并不一定会致命,要看发现的时机和治疗手段。绍谦的母亲,当年就是死于这种病,那时是因为她消极治疗的缘故。
戴维还说:绍谦现在的情况还不算恶化,及早进行手术的话,完全有可能恢复健康。肿瘤生长阶段时常会压到视神经,所以会出现短暂性失明的状态,偶尔发作时头痛欲裂,绍谦一直是靠镇痛剂来渡过的。
她觉得害怕极了,她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一直怕得发抖。
戴维明明说不一定会致命的,可她就是莫名的恐惧。恐惧像黑暗里伸出来的一只手,拉着她一直下坠下坠。
她问出来的时候唇齿因为打颤都碰到了一块:“如果立刻手术的话,成功率有多少?”
戴维敛眉,想了很久。连他这样开朗的性格,此刻的神情都是如此沉重。最后,他比了个数:“之前,可能还有百分之六十。现在这个状况,恐怕只有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这个数字要放到平常或许并不算小了,毕竟这世上有很多几率不到百分之零点几的奇迹都发生过了。可是一旦套用到人的生命上,尤其是至亲之人,这个数字又显得多么的渺小!
连一半都不到!
如果进行手术,他会有一大半的可能远离这个世界,永远的离开她!
“不行,不行……别说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八十的可能都不能冒险……”她终于忍不住落泪,眼泪扑簌簌砸到他手背上:“我求求你,你是那么好的医生,你一定有别的办法的,对不对?你一定可以救绍谦的,他绝对不能有事!”
戴维只是任她抓着,一动不动,那样放任她哭闹耍赖,更像是对她的一种怜悯。
她不要什么怜悯啊!她只要绍谦好好的,好好的活下来!
这样在他床头守了一夜,他还是睡得那么安静,丝毫没有醒来的迹象。窗外天空渐渐泛起一抹死气沉沉的灰,当黑暗终于退散,她却越发的害怕起来。她紧紧握着他的手,因为一直吊着点滴,他的手很冷,她用两只手捧着,用自己掌心的体温暖着。
他似乎做了很长的梦,梦里都不曾舒展眉心。她用手指小心翼翼的抚过他额角,未能捋皮他的皱纹,自己反倒颤抖起来。
临近天亮的时候,走廊那头一下子呼啦啦涌进了许多人。她起身开门,看到走在最前面的中年美妇,她披在肩头的黑色狐毛披肩因为步伐太快,而一颤一颤的张开着,仿佛黑鸽子张开的羽翼。她后面跟着几位穿白大褂的外科手术专家,还有一整排步履统一的警卫。一瞬间在医院走廊上列队排开,气势甚为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