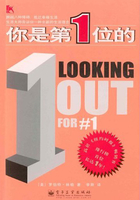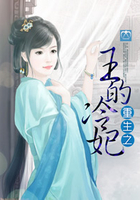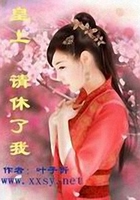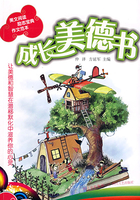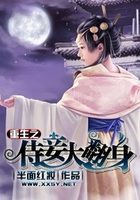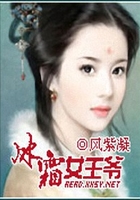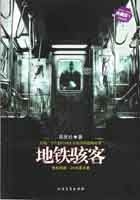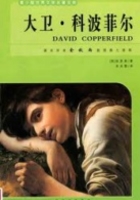放弃习惯的时候,一切都打乱了
保持一个习惯并不需要很多的自我约束能力,但是如果要养成习惯需要付出的就比较多,因为人们极容易在这个时候退回到原来的习惯去。
历史上的很多名人都是这样,他们都有固定的习惯。比如他们会规定自己白天7点到9点写作,晚上8点到10点画画,这样会增加他们的创造能力,只要是到了时间他们就会心无旁骛地进行创作,而不会被其他的事情所干扰。
在这一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康德。据说,康德的生活极有规律,几点散步,几点返回,几点做学问,几点用餐,都有准时候,而且十分的精准。后来邻居们发现只要有康德在,几乎都不需要看表就知道时间了,因为他们有“康德钟”。可见,康德是可以多么精准地按照时间来安排生活。
康德还有一个本事,可以准确地预知天气,只要他拿伞出门,那天就一定有雨。于是,邻居们只要是看到康德带了伞,他们也会带伞;如果康德没有带伞,邻居也可以放心地空手出门,不用担心下雨。难怪有人会赞叹说,康德的一生就像是一个最规律的动词。
保持一个习惯并不需要很多的自我约束能力,但是如果要养成习惯需要付出的就比较多,因为人们极容易在这个时候退回到原来的习惯去。打个比方,按照自己的习惯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然后再换个方向,感觉会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有点怪怪的呢?总是觉得换个方向不太对劲,总是想回到以前的交叉模式,这就是所谓的人们养成的习惯,是习惯造就了人。
但是,改变习惯却是困难的。无论是学习新方法,还是建立新习惯,打破一种旧的习惯要远远比人们想象中的难很多,甚至很多人的尝试都是以失败告终。
沙哈尔老师在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在壁球队打球非常的不顺利,沙哈尔老师非常希望能快点到3月1号,这样的话就可以结束打球,专心投入到学习中,因为练习壁球很浪费时间。
当球赛结束之后,沙哈尔老师停止了打球,但是学习成绩并没有得到提高。这是为什么呢?沙哈尔老师通过反思,找到了原因所在:因为在壁球赛结束之后沙哈尔老师不再打球,放弃了自己养成的习惯。在以前打球的时候习惯了在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情,什么时候该打球,什么时候该学习,一定安排得井井有条,做事也会很有效率很积极。但是当放弃习惯的时候,一切东西都被打乱了。
由此可见习惯的重要性,养成新习惯是永久改变的唯一方式。
认知重建带来的改变
看到了吧,一对双胞胎,他们从小在相同的基因和成长环境中长起来的,但是后来生活的质量确实天差地别。
悲观主义者对待世界的态度通常情况下都很消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会感到很悲观,甚至会不断地强化悲观的程序。而乐观主意者则恰恰相反,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他们的看法都很积极,这是因为两者拥有不同的神经元通道,而正如前文所述,不同的神经元通道是由不同的认知态度造成的。
有一个非常著名、非常经典的实验说明,基因只占变量因素的50%,改变是由后天的认知带来的:
有一对双胞胎,他们在同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父亲酗酒吸毒,经常实施家庭暴力——实在是一个很糟糕的成长环境。长大之后他们弟兄两个纷纷逃离了家庭,开始寻找自己的生活,在他们30岁的那年,有一个心理学家为了研究基因与成长环境的关系去采访了他们。
这对双胞胎中的其中一个人长大之后简直和他们的父亲一模一样,酗酒吸毒暴力这样的恶性行为一个不少。心理学家问他:“你知道这些是不好的吗?”
那个人回答:“我知道,但是我改不了了。”
心理学家问:“为什么会这样?”
那个人回答:“我知道我的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从小就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所以只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完全没有其他的可能了。”
心理学家知道成长环境的重要性,当听到这个人的一番话,也不禁叹了一口气,感到既同情又无能为力。接下来,他又去拜访了双胞胎中的另外一个。
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另外的一个人事业有成,并且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在一起生活得和乐融融。起初心理学家还在怀疑他是在作秀,后来又去观察了一次。心理学家在赞叹之余,问他:“你从小生长的环境那么不好,但是却不像你父亲那样,真了不起。”
这个人回答说:“您也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伤害我们这么深,这种伤痛会伴随我的一生。但是我不能再去伤害我的孩子了,我不能把父辈那些不好的习惯再延续下去。我要给他们幸福快乐的生活,我要努力做个好爸爸。”
看到了吧,一对双胞胎,他们从小在相同的基因和成长环境中长起来的,但是后来生活的质量确实天差地别。其中的一个是悲观的受害者,选择将地狱式的传统延续下去,而另一个却积极地创造了天堂一般的环境。这种截然相反的状况,归根究底是因为他们两个对事物的看法完全相反。快乐和幸福感并不取决于外部环境和过去的经历,更多的是在于一个人的精神状态。
还曾经有研究人员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研究人员将实验者分为两组,其中一组被告知注射了肾上腺素,而实际上是注射的维生素C,另一组被告知没有注射任何药品。
接下来,研究人员分别让两组的人员填同样一份试卷,上面问的都是比较极端尖锐的问题,比如问你妈妈在嫁给你父亲之前睡过几个男人之类。面对同样的问题,两组人员所表现出来的状况就很不一样,那组被告知注射了肾上腺素的实验者情绪明显很激烈。
所以说,对身体状况的看法决定了人的感受,进而决定了情绪。
在斯坦福大学,曾经进行过这样的一组实验:将参加实验的学生随机分为两组,其中一组被认为是争强好胜的,另外一组被认为是平和大方的。在这两组实验者中都要进行游戏互动的活动,第一组的游戏名称叫做“社区游戏”,第二组的游戏内容是一样的,不过名字叫做“华尔街游戏”。在游戏的过程中专家发现,第一组的成员更倾向于合作,而第二组更倾向于竞争。看来,“社区”还是“华尔街”,只不过是名称上的变化,还会带来巨大的差别。
曾经有一个同学问过沙哈尔老师:怎样才能提高哈佛学生或者其他人的志愿服务意识?沙哈尔老师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答案,那就是:改变学校和社会对志愿服务的看法,不再看做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优势。事实上,志愿服务本来就是一种优势。如果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到志愿服务的优势,那将有越来越多的人乐于参与到志愿服务中。
最后,还有一个心理学家做了一项研究,参加实验的人是酒店里的清洁女工。心理学家将她们分为两组,测试她们的一些身体指标,比如血压、体重、血脂含量、心理指标等等。但是这位心理学家只会给第二组人员讲,你们干的工作其实就是在锻炼。过了八周之后,这位心理学家回来重新检查了女工们的身体指标,发现第二组人员的血压明显降低了,血脂也明显降低了,体重有所减轻,自尊有所增强。其实这两组人员都在做同样的工作,只是由于观念不同,当她们将日常琐事认为成是一种对身体的有益锻炼的时候,不论是对心理还是对生理都会带来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