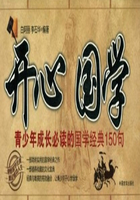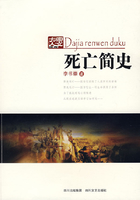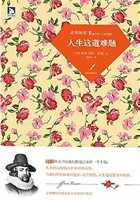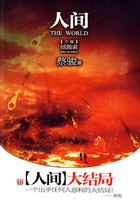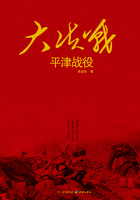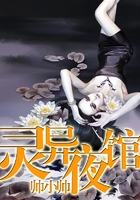(一)程朱理学
1.学派简述
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创立。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二程的思想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完成,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理学。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六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代中期,戴震批判朱熹理学“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适应了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需要,他们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使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适应了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深得统治者的欢心,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故如对宋明理学的概念不做特别规定的话,在通常的意义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
2.朱熹及其主要思想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逆翁,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朱熹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4岁时,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翚等人,随母迁居建阳崇安县。十九岁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31岁时,朱熹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及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庆元三年,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朱熹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被视为儒家正统,支配中国思想界达六百年之久。他的思想体系庞大,对多个学科都有所建树。朱熹在探究和阐释中国传统哲学时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如天理人欲、道心人心、形而上形而下、动静、道器、性情等等,都是围绕着“理”来展开的。他的思想缜密严谨,“理”的本体性贯穿一切。朱熹在追求“天理”的同时,把“人欲”看成是求“天理”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于是,朱熹提出“灭人欲”的思想主张,并把它看作“成圣”的必要途径。
(1)天理论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理本论思想,以“理”为其最高范畴,通过对“理”与“气”关系的研究和展开,建立起自身庞大而成熟的哲学体系。他的天理论,则是这一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石。
他首先说明理与天下万物的关系,提出了理在事上、理在事中的观点。他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认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皆为形而下之器。同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在他看来,理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并且理具有“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的超意志特征,和“无所适而不在”(《朱子语类·卷七十》)的超时空特征;普遍之理又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天下没有理外之物,如他举例说,阶砖有阶砖之理,竹椅有竹椅之理。形而上的理,何以在事物之上之先?朱熹从理为本体角度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这即是说,在世界本原的理那里,其本然状态便内含了物之理,它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先,而万物则是理之后由理所派生形成。他进而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朱子语类·卷一》)他强调在万物生成之前,理已存在,而且不依具体事物的转化灭亡为转移,理具有永恒独立的普遍性质。
朱熹从他的理气关系理论出发,提出“理”决定“气”,理气结合构成天下万物。何谓理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先,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这就是说,理与气两大因素,是道器对置关系,任何器物都离不开二者。“理”是产生万物的本质根据,气是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观念性本体的理与物质材料的气彼此结合,便形成了天地万物。这里,朱熹把张载视作世界本原的“气”,作为第二性的亚层次,与二程视作宇宙总则的“理”,联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理气统一体内,“理”是第一性的,是道是本;“气”是第二性的,是器是用。他以此克服张载重气轻理、二程重理轻气的各执一偏的片面性,形成自己的理气说。
朱熹天理论,是天人合一于“理”的学说。“理”,既指万物的所以然规律,又指孝亲事兄所当然的道德原则。他说:“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大学或问·卷一》)他认为,宇宙规律与社会道德,二者由天理所赋予,存在所当然的现实指令和所以然的本质规律。如讲孝亲事兄是当然之则,究其孝与事的原因,则是属所以然的规律。朱熹无意构造自然哲学的纯理论,他所主张的是以天理的所以然规律,论证说明其所当然的道德律令。他说:“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而不容己,所谓理也。又说:“理则为仁义礼智。”(《大学或问》)可见,朱熹的“理”本体是直接投射和服务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是为维护基本的封建制度,为在封建秩序下处理人世五伦关系而规定的现实道德指令。
(2)人欲论
朱熹认为:“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答黄道夫》)也就是说,人的本性从“理”来,人的形体从“气”来,这是承接了张载的学说进而扩充了自己的关于“人性的理论”,他认为:“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人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须有气,然后此物有以聚而成质;而气之为物,有清明昏浊之不同,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则为圣;禀其清明而无纯全,则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则为贤;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则为愚,为不肖。是皆气禀物欲之所为,而性之善未尝不同也。”(《玉山讲义》)
由此可以看出,朱熹认为人所禀受的气有清浊之分,“天命之性”的气是禀清的,因而是善的,所以他认为“天命之性”就是“天理”,是无有不善的;而“气质之性”的气有清有浊,因而是善恶相混的,所以他认为“气质之性”是受到外界的物欲的诱惑和牵累,是产生“欲”的根源,是有善有恶的。《尚书·大禹谟》云:“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意思是:“人心”是人对声色名利的欲望追求而产生贪嗔痴爱的不良念头,使人人自危而贪图安逸;“道心”是正大之心天地自然之心,儒家称之为良知、良能、止于至善之心。“唯精唯一”就是要集中精神,以审慎细致的思维,回归先天道心之一性,才能“允执厥中”,使言行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所以,朱熹把“天命之性”看成是“道心”,把“气质之性”看成是“人心”,朱熹要使“人心”回归“道心”,克服不善的思想和行为,就要克服“气质之性”所带来的物欲,所以“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子语类·卷十三》)“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卷十三》)有人问朱熹:“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他回答说: “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在朱熹看来,人们对美味的需求也是“人欲”的表现,因而要抛弃。可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正是建立在人们欲望的不断呈现和满足的基础上的。没有“人欲”,也就很难有社会的进步。无论如何,“人欲”的消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的争夺厮杀以及相互欺诈,都往往和“人欲”的膨胀息息相关。
在程朱理学发展的同时,还兴起一个强调“以利和义”,反对义利对立的儒家学派,称为事功学派,不过没有成为主流。事功学派源于王安石“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实用思想,包括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与理学相抗衡并在乾道、淳熙间形成鼎盛之势。他们认为理学家空谈“性与天命”,对其“静坐”、“存养”功夫尤为不满。倡言功利,赞许“三舍法”,主张习百家之学、考订历代典章名物,以培养对社会有实际作为的人才。其学说开启了明末清初颜元、黄宗羲、王夫之等的启蒙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