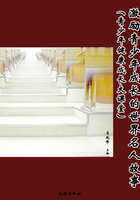记得高二时,咱每天下午大课间都去学校溜达一圈,聊天扯淡,吃冰棍。
再后来,你找了媳妇,咱仨一块儿溜达,最后我请你俩吃冰棍,关键时刻我还得回避。
哎,还记得吗,那次,“小少爷”。
在这里不细说啦,给你丫留点儿面子。
追忆似水年华,很多再也追不上了。
我们都长大了。
那会我和干爷有一事儿特牛逼奔放。美术课,咱俩不听课聊天,后来我建议,这么吵,咱功放音乐得了。
干爷说是啊!以前没这么干过,值得一试。打开手机,略略筛选,功放陈冠希的《还记得我吗》。
结果,老师示意大家停止讨论,而我们根本没在意,偌大教室忽然安静许多。
“我叫陈冠希,跟我念一遍!”
手机的功放在室内还是强大的。
还有一回放学,咱俩去吃火锅。席间你爹来电话问你怎么没回家吃饭,他从外地回来了。
结果干爷“哐”地放下酒杯:“你怎么回来了!”
我笑的差点儿把火弄灭。
咱当年。
这叫不懂事。
但更多的。
这叫无所畏惧。
唉,警察学院开学早啊。
时间滚滚,我们都会改变。
但,过去抑或将来,回忆不变。
再见面时。
容颜依旧。
(三)
我觉得是时候该说说这个家伙了。
丁与是我初二时认识的一个哥们儿。那会儿我在一班,年级里学习最厉害的班;他在二班,年级里除了学习最厉害的班。
当年还算不上哥们儿。我跟他认识是因为他跟锁越关系特别好,而锁越是我的小学同学。
两年后上了高中,跟丁与在一个班了。之后越来越聊得来,那是真聊得来。记得当年跟他没什么共同话题,但就是特爱在一块儿聊天。
什么是好兄弟?没话说,却爱聊。
再然后,就是现在,上了大学。我在北京电影学院,他在北京工业大学。
高三时,我就清楚,再过一些时日,就与所有好哥们儿分别了。
多少朋友因为大学离别,多少情侣因为大学分手。
没办法,每个人为了将来,都认了。
世间多少离别,都是为了自己。
但每个人都没有错,每个人都要实践自己,每个人都要践行命运。
我坐地铁到他那边二十多站,后来打过一次出租,没堵车,八十多块,再后来便打不起了。
每周他来电影学院找我一次,每周我去工业大学找他一次。
这就是兄弟。
脱下相同校服分别,穿上不同校服拥抱。
这就是兄弟。
各自的环境变了,日后还会再见,主动再见。
这就是兄弟。
千万别认为我话多,你知道吗,多少同窗,多少人,去了不同学校,穿上不同的校服,就是永别。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
丁与,你有没有?也有吧。
曾经,不在一班,相隔不远。
大老爷们,也别总煽情,想想过往。
那会儿初中,丁与他们几个在校门外单元楼小区抽烟,常在“二门”。后来他们中有人问咱干嘛老在二门抽烟啊,某人回答因为咱是二班啊。
“那一门呢?是不是一班的人?”
“小权儿一门抽雪茄呢。”丁与回答。
当然是玩笑,但从那天起,这变成了特大一乐事儿。
之后,二班的人一见到我就是:“权儿哥,一门呢?”然后就大笑。我被蒙在鼓里多年,直到高二才得知事情真相。
在今天,回忆回忆曾经违反校规的事,尽是噙着泪水的笑。
后来接触得多了,好多好多的乐事儿,我得告诉你,有些我还真是故意的。
丁与特能喝酒,能喝仨我。
每次我醉得跟逼似的,孙子丫总是微醺地点起一支烟。
之前中学喝的次数少,上了大学每周大酒小酒总得来点儿。
丁与,我特爱跟你喝酒,喝不过,我也爱跟你喝。
每次我挥手“再来一瓶”之时,他总劝我:“行了侄子行了,差不多行了啊侄子。”
侄子。这可是一大堆话。
高三上学期,那会儿还在小学那边补课。
一帮闲人靠在墙上瞎编辈分儿,什么爸爸儿子爷爷孙子的。其间我路过,一家伙冲丁与说:“看,你权叔。”
我是想逗逗他们,冲丁与来了一句:“叔!”
哎呦我操,给这帮孙子们笑的啊!一个个就差你妈的打滚。
这帮家伙原来没觉得我开玩笑,以为我真错了。
后来,我就成了丁与的侄子。
再后来,每个课间,一堆人围着我,轮番着问:“权儿,丁与是你什么人?你是丁与什么人?你管丁与叫什么?丁与管你叫什么?”诸如此类,总是问到我晕头转向地说错才大笑着散去。
这帮可爱的狗犊子。
我跟丁与单独也有好多好多事儿。
说也说不完,而且,都说出来也没意思了。
多少事,在不想说的心底。
但丁与求我一定要说点儿啥,那咱说一个。
有次,我跟丁与去吃火锅,吃多了,上厕所。我害怕手机钱包掉厕所里,就把贵重细软交给他,正欲脱裤子,想起大事儿,对他说:“假如我妈来电话帮我接一下。”他点头同意。
但是直到我出来我妈都没来电话。我俩并肩走。我拉肚子,有点儿虚,正在擦汗,此时此刻我妈来电话。我直接说:“哎快帮我接电话。”
丁与愣:“啊?”
我晕着来了一句:“我还没拉完呢。”
丁与笑得跟抽水马桶似的。
哎呦,我这猪脑子。
丁与,你这家伙。这事儿就差伊拉克不知道了。
这么多年,这么多事。
当年那堆侄子叔叔。
儿时,我们哭着哭着就笑了。今日,我们笑着笑着就哭了。
今天,假若还能把这帮家伙同时齐聚,我宁可当笑柄。
丁与,啥也不说了,啥都明白,好兄弟。
不在一班。
相隔不远。
(四)
To Jimmy.
Jimmy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本来想用他的外号,但碍于道德风化。
从初中认识,到现在一直没断,关系一直不错。
前天他去了加拿大上大学,说过再见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再见。在这里,记录我俩之间的一些事。
初中,我俩同班。我经常问他问题,他忙于为我解答以至难以在学校写完大部分作业回家打游戏。有一次,他郑重而生气地大声说:“我他妈的是不是欠你的。”
雪地里,我俩打雪仗,他摔倒,我假装扶他,而后把他按到满是雪的树丛里。
每天为了早打饭跑步去食堂。一次我眼镜跑掉,他帮我捡回,我感激得差点涕零。
初三时,我给他讲了一道物理力学滑轮大题,我就给他讲过这一次题。
二模上午,我去他家打了一个小时《反恐精英1.6》,半个小时《铁拳5》,复习二模考试十分钟。他告诉我的“还原剂被氧化,氧化剂被还原”被我受用到高考结束。
初二我劝他玩《铁拳》,他第一次玩,我玩俩月。我们玩了一个小时,我全输。
初三一次联欢会上,偷偷打铁拳,我第一次战胜他。
我们一次去金源购物中心吃饭、打铁拳,打了三个小时。
中考结束,我英语和他一个分,104分,我很开心,他很悲哀。
高中,我仍留在育英学校,他去了十一学校。
虽然平日不见,但仍隔三差五打电话,有空仍约出来游逛。
出来一般吃火锅,然后比谁率先开锅。
他的《铁拳》暂停,而我已经从《铁拳5》玩到《铁拳6》。
自从学会防守他的“赖皮招数”之后,我屡战屡胜。他一蹶不振,此后扬言:“铁拳没劲,老子再也不玩了。”不过每次都去街机厅打上一会儿。
有次出去,我把他的背包抢走,周旋半小时,乃还。
此后,高考结束,我们有空就出来看电影。通过陪他看《小时代1》,使我感到某女星还是蛮好看的。
他即将去加拿大,提前一天,上午,我们又去看了各自都看过的《小时代2》,因为其他电影也都看过,而此片中某女星还是蛮好看的。其间我抢他的爆米花,而后我请他吃了火锅。
他走的那一天,凌晨登机前让我给他打电话,我说能不能提前些打,忒困。他说不行,要走时想说的才多。
大约就是这样。
你不是问过我高考作文多少字吗,差不多就这么些字。只是不能分这么多段,也不能这么写。这么写,是明显的跑题、文体不清、主题不明以及缺少中心思想。
明年再见,姬绍飞。
它们真正变成了波澜不惊的记忆,安静地摆放在心底。
每当我想起它们,只是记得有那样一些事情。
我们都变了昨天出门很早。天空好似青蓝色的泼墨式水彩。
在路过一所学校时,无意间在学校门口看到了一片片白蓝色耸动的人群。
不觉猛然间意识到自己已经脱离这个单纯的群体很久了,顿觉有些失落。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失落些什么。我从容平稳地穿过了最迷茫的青春期,脱离了愈发困难且变数庞杂的高考的痛苦,而且在这一切中获胜,进入了许多人以及我梦寐以求的大学。
现在,作为一名大一的学生,因自己无法继续穿校服而失落。
至于为何我站在教室外听到“病毒是不是生物”此问题时会调动一年前的思绪;为何我在过去操场上站得比任何时候都直;为何我仍然留恋过去;为何我仍然不舍曾经。我不想做过多的阐释,因为许多是我心底的东西,有些秘密是不能说的,就当它消失了吧。
那天,看《小时代》时我忽然想起,在我高三岁月的末尾,在高考结束之后,因为事先不知而外出旅游,我没有参加毕业典礼,没有参加全班聚会,这是令我伤痛一生的事,也是我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
写到这里,我忽然打了个哈欠,而后便流泪了。没有矫揉造作,这是真的。或许是内心告诉我,过了这么久,哭哭就好了,别太伤心了。
当然,日后也不是没有聚会,但这都是徒劳的,是完全不同的。我深知,我会与某些人越来越近,也会与某些人越来越远。但相比于当年的旧时光,我们都变了。
或许有一天,我不会再矫情,我会远离这些岁月。
它们真正变成了波澜不惊的记忆,安静地摆放在心底。每当我想起它们,只是记得有那样一些事情。
但见君主临天下,尤知玄宗不早朝。
但惊天子龙颜怒,却闻媚笑向春闺。
皆知圣贤东游去,孰清是否卧青阁。
古来芸芸朝夕往,天下谁人不贪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