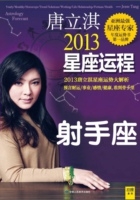但我想说,定庵以一人之勇和整个中国作对,以一介之躯与五千年作对,以一人来否定传统,这样的横站,称得起大哉斯人!定庵把握了虚无,最后被虚无吞噬,他不见容于黑暗,他即使想燃烧,但谁要你的烛照呢?道光十九年己亥年,龚自珍辞官南返,行程九千作诗三百,两年后暴死在丹徒。龚自珍己亥四月辞官南归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钱穆就说:“定庵以暴疾终,其己亥出都,以一车自载,一车载文集百卷,不携眷属仆从,仓皇可疑。”或曰为儿女之事,因为他和奕绘贝勒的侧室、着名女词人顾太清之间的私情,东窗事发,仓皇出都;或曰为政见“仵其长官”得罪宗室,或曰为经济困窘,不一而足。不管怎样,龚自珍以一人之勇而走出了那个藏污纳垢之地,成为一个为自己负责的独行于世的人。我们应该庆幸中国诗歌史上出现了这本《己亥杂诗》,也许这里面艳词的坦荡引起很多人的不快,那些在儒家文化中自宫的人是不会有这样的词语的,一切神圣和高贵都在这里崩塌。他们认为最卑鄙和最肮脏的,却是龚自珍用以灌溉生命的血液,龚自珍的庐木已拱,我也不知定庵葬在何处。他坟前的青草,绿了又黄,但我想把伏尔泰墓碑上刻着的一句名言送定庵是最合适的,“这里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是啊,在不惑之年,我不能说读懂定庵,但在我知道定庵特异的病后,开始有点接近他了。定庵有一首特别的诗《冬日小病寄家书作》:
“黄日半窗暖,人声四面希。饧箫咽穷巷,沈沈止复吹。小时闻此声,心神则为痴;慈母知我病,手以棉覆之;夜梦犹呻寒,投于母中怀。行年迨壮盛,此病恒相随;饮我慈母恩,虽壮同儿时。今年远离别,独坐天之涯。神理日不足,禅悦讵可期?沈沈复悄悄,拥衾思投谁?(予每闻斜日中箫声则病。莫知其故,附记于此)”这是怎样的怪异啊?听箫则病,这不是懦弱,也非撒娇。在定庵的诗词中,总是剑箫并举,以“剑”喻抱负,以“箫”喻诗魂。如“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他的诗作本来也就兼有“剑气”、“箫心”两种面目——激越和柔婉,郁怒和清深。这是一种命定,还是前身?从幼时的箫音,到定公48岁辞官途中遇到一个叫“箫”的女子。一个是旷代的不世出的孤独者,一个是妓女灵箫,在目光相接的一瞬,他感到了命定的相会。
箫音使龚自珍如醉如痴,如病如魔,而在定庵的晚年,上苍又让他回到童年,这一次是病,也是命,这病要了定庵的命。
风云材略已消磨,甘隶妆台伺眼波。
为恐刘郎英气尽,卷帘梳洗望黄河。
壮志难酬,如今定庵是甘心做个下人(隶)在妆台边侍候女人了。
然而灵箫呢?就算你沦落到像刘备一般在大街上卖草鞋,也要留着皇叔的一口傲气;让我们卷起帘子来,就算你只看我的眼波,我眼波里还有一条黄河呢。
这样的奇女子,《己亥杂诗》十分之一的主题都与灵箫有关,后来,两人分别,灵箫回苏州隐居,定公于两年后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有传闻说为灵箫毒杀,传说也只是传说。但我以为,与其死在腐坏的官场病床,莫如死在爱人之手。我想到《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17-28节:希律王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先知约翰在民众中抨击了他们,希律王愤然把他逮起,希罗底的女儿莎乐美在希律王的生日宴会上为他跳舞,国王高兴之余向她起誓说答应她所有的要求。莎乐美受了母亲的挑唆,向希律王要求杀了先知约翰的头。希律王万般无奈,杀掉了约翰,满足她的要求。在圣经故事中,对莎乐美的描写并不是很充分,她的出现只是个花瓶般的人物,为了杀死约翰而被母亲利用的无知少女而已。而在王尔德的戏剧中,我们却看到这样的一幕:当约翰的头颅被砍下,莎乐美举起他血淋淋的头在他的唇上深情一吻:“啊,你不让我吻你的嘴,乔卡南(约翰的名)。嘿!我现在要吻你的嘴了……我对你的美如饥似渴;我对你肉体想咬想啃;美酒也好,鲜果也好,都不足以解决我的饥渴。”“啊!我吻到了你的嘴唇,乔卡南,我吻到了你的嘴唇。你的嘴唇上有一种苦味。那是血的滋味吗?……不,说不定是爱情的滋味……据说爱情有一种苦味……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我已经吻到了你的嘴唇,乔卡南,我已经吻到了你的嘴唇。”
爱可以死生肉骨,爱也可以砭骨伐髓。爱情为物,担得起,那是决绝,是金刚怒目;担不起,也是如寻常落英,人之常情,就像病,可以使人脱胎换骨,也可以使人如山倾颓。
四
在回平原深处的老家时,知道启蒙的黄老师病了,家里人瞒住他,没有多少日子了,是绝症。
黄老师的家,在我小学的时候是常去的,他是村里唯一一个文革前高中毕业的人,他有很多书,我从他那里读《唐诗三百首》,黄昏跟着他到河边念“唧唧复唧唧”,在水车转动声中,他开始吹笛子,总是呜咽。
我知道,他在村里孤高而腼腆,有次家里没有吃的,媳妇让他到生产队的玉米地掰几个棒子为孩子煮食,度过断粮的日子。黄老师去了,谁知看庄稼的人随意的一吆喝,“看见你了——”,其实根本就是胡乱的吆喝,老师慌忙把口袋和棒子丢在地里,而口袋上写着他的名字。
以名字找人,黄老师被罚,于是传为乡村笑话。我在大学毕业后,问过此事,他说:“作贼,也要像杀人的武松,留下姓名,这样才好。”
黄老师做了一辈子民办教师,有事就窝在心里,笛子也不吹了,发黄的笛子,覆满灰尘。
师母说,老师好生闷气,该转正的时候,因为腼腆丢掉了名额,回到家就独自喝酒,就在家里关上门骂娘,就踢自己的狗和羊,说奶奶的。我记得伏尔泰有过类似的举止,这是马克思记述的,伏尔泰当年有四个敌手,他就在家中喂养了四只猴子,分别取名为那四个敌手的姓氏。马克思说,伏尔泰没有一天不亲手喂养它们,不赏它们一顿拳脚,不拧它们的耳朵,不用针刺它们的鼻子;没有一天不踩它们的尾巴,不给它们戴神甫的高筒帽子;也没有一天不用最难以想象的卑劣方式对待它们的。
是啊,黄老师的羊像伏尔泰的猴子,但黄老师最终还是没能排遣自己的郁结。黄老师为平原深处的小村子培养出了数百名大学生,而自己却竭蹶乡里,最后仍是一名民办教师,他在离校的时候,儿子到学校去接他,是傍晚学校的最后一课,他还在那里讲得起劲,暮年白发飘萧,像都德《最后一课》的韩麦尔先生,黄老师说:“下课了,孩子们。”
而孩子们却仍是不动。
命运,休论公道,我看黄老师的时候,他的食道癌,已是最后的时日,家里人还说是喉咙的一般症状,喝点鸡蛋水打打火,就会好的。黄老师无疑是一乡间的纯儒,虽然他读夫子的书很少,但他做事的底线是有些儒生不知权变的一面。为给黄老师解闷,我把香港《凤凰卫视》
上李敖讲的解闷趣事说出:新儒家的领军,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熊十力先生,年轻时为民国奔走,后来看到民国的成果为蒋介石所篡,恨得早上看报纸,只要有蒋介石的照片熊先生就一边骂一边拿上有蒋介石照片的报纸揉成一团在自己的生殖器下面擦来擦去,至情至性,如此。
黄老师对世事做不到如此,生活使他放弃了笛子,也放弃了喜爱的古文,他开始喜欢喝劣质的酒,喜欢吃辣椒大蒜。
我们没有谈张载喜欢驴叫,乡村里还有广阔的驴叫在夜深时蓦地传来。虽然张载不知道有一个乡村小学的老师,不知道“民办”这个名词背后的沉重,不知道食道癌。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我们虽然不再张贴在书院的西墙,但我们已读了千年,即使在普通的平原乡村也弦歌不辍。
我握别了黄老师,一个月后,他就悄然弃世,他挣扎着送我,握着我的手,开始老泪纵横:“常来啊!”
斯人也而有斯疾,黄老师弃世了,我理解了他乡间常常的勃然怒气,他对一些事的愤恨,使我感到了温暖,我知道黄老师是一个为生活的种种丑陋,为平原而生气的乡间的纯然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