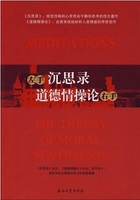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颇重历史传承的。故谈到余秋雨的创作,也不可不知他的故乡浙江余姚。余姚在日本人眼里被奉为神土,是福地,中国历史教科书前面稍翻几页,就有余姚河姆渡,一个整整七千年的文化遗址,那里已有木构建筑,已经摘食杨梅,已经种植稻谷,已经烧制炊具……余姚,是斜风细雨富春江上披蓑着笠的严子陵的旧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到了明代这里大放异彩,王阳明出现了,黄宗羲出现了,朱舜水出现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
中论及余姚时说:
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阳明千古大师,无论矣;朱舜水以孤忠羁客,开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而黄氏自忠端以风节厉世,梨洲、晦木、主一兄弟父子,为明清学术承先启后之重心;邵氏自鲁公、念鲁公以迄二云,世间崛起,绵绵不绝。……生斯邦者,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
地灵人杰,生于斯地,确实幸运,“闻其风,汲其流”,这种“风”与“流”实是一种神秘的人格传递,而这种传递是一种潜移默化,它融入了斯邦的山水大地、风土人情,是人的举首投足,是人的声咳笑貌,无形而悠长:严子陵的耽于山水;王阳明的匡时济世、治学讲学,奔波九州,最后病死江西南安的船上;黄宗羲十九岁进京为报家仇国恨,手持铁锥,见魏忠贤余孽就刺,后来江山易代,又召义军,结寨为营,失败后即投身学术,以历史学泰斗和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巍然挺立……这些无疑参与塑造了余秋雨的文化人格,又为他观察审视自然风物人情物理提供了独到的视点。
在余秋雨的作品里,总是贯穿着一种严肃的理性精神与深刻的文化批判的意念,他是以《文化苦旅》进入散文史的散文大家,是改变散文写作范式的人。余秋雨的散文作品的成功绝非偶然,从功夫上论,在散文之前,他有一种涉及东西文化、打通东西的修养和功夫,他的先在的基础是既有历史审视眼光,又有灵心体悟发现的《戏剧理论史稿》,还有《戏剧审美心理学》与《艺术创造工程》,与他戏剧科班的出身有关,也与他的才气有关,原本枯涩的理论,一到他的笔下就有了诗意的体现。
而余秋雨的名字与《文化苦旅》的成功似乎也有某种神秘的勾联,中国的古代典籍如《易》、《老子》、《内经》对中国文化的构成起了重要作用。“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情;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至今,其名不去……”这是老子对“道”的描绘形容;而作为布满人生玄机的《周易》,试图把人生、自然、历史归纳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宇宙模型的构想,时至今日,仍对当今世界上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和艺术家有着深刻的启示。
东方的文化传统是主“静”的,沉实的,但是就其存在的方式而言,却必须是无始无终地“动”的。《易经》之“易”就是指的变迁运动。
“生生不息之谓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讲一种生生不息、永远运动,而作为人生,也应以体现天道为原则,保持生命的律动,这就像一个神秘主义的链条。
《易》讲的是一种人类特具的心灵感应能力,中心枢纽为咸第三十一,《彖》曰:“咸,感也……天地感而万物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系辞》曰:“《易》无畏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通过心灵感应,《易》也就开始同人类精神发生对话,艺术既为心灵感应功能的体现,所以同《易》的精神本质存在着深刻而内在的一致。
如睽第三十八,全部爻辞是描绘一个旅人在旅途上的见闻,这是《周易》中一个讲行旅的专卦,描绘旅途上的三见三遇,这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十分相像,更奇的是睽卦之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苒。往,遇雨则吉”,睽是乖离,不顺遂,可说是行旅之苦,然而,遇雨则吉,《文化苦旅》与秋雨之间仿佛就是天然的联系。《周易》并不是一部已死的木简古书。《易》运行在我们生活的天地宇宙之间,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闪烁着神光。只是我们被世俗遮蔽得太深,没有留意罢了。
世间的学者分两种,一种如王阳明、黄宗羲,身处忧患,伤古悲今,关心国计民生;一种如周作人、林语堂,以学问自娱,青灯黄卷,闭户读书以到终老。一为担当拯救,一为浮世逍遥,无疑余秋雨属于第一类。
日本大作家川端康成曾谓:“入佛界易,进魔界难。”川端是在东方精神沐浴下长成的,所以这话头就说得特别耐人寻味。余秋雨曾在书斋中在世事炼成金刚不坏之身,就像佛家所说雪中芭蕉进入了神秘冷峻的世外仙境,然而他抛却了自我娱情,回归到象征感情生命之美丽的凡界火焰山,立成文化大德。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智与良知使他拿起反思与批判的武器,对民族及历史进行评说。所谓“苦旅”之苦,当不只指旅途的劳顿艰辛,何其臭的袜子,也有内在的忧郁与震颤在吧,艾青说:“为什么我双眼里满噙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可谓知之甚深的“苦”的另一释义。
文人秋雨挚爱着传统的文化,他常年跋涉于祖国的山山水水,面对着或绮丽或雄浑或幽静或奢华的景地,他的理性之光穿过浮泛而达到内里,不只感叹天之悠悠,且往往有一种凄凉难抑的悲怆胸怀。
《道士塔》叙写感慨的是一个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缩的平民模样的王道士,然而正是他把文化瑰宝一箱一箱移交给俄国人勃奥鲁切夫、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
王道士太普通了,是在我们国家有众多数量的生物,没有王道士也会有李道士,他们的生存就是吃喝拉撒,精神离他们很远,“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刷把。”
在王道土刷把下覆盖的可是莫高窟的壁画,那些千年不枯的吟笑与娇嗔,那些有香气的衣服和图案,那些发出生命信号的伎乐天,都被白粉刷白了,该把愤怒向着王道士倾泄吧?然而,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你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如果把这笔账只记在他头上,那么这个民族应该担当的那部分就要被抽空,“苦”,确实是苦,文人秋雨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王道士太卑微太渺小,他的肩膀怎能承担这民族文化的重任?那要谁承担呢?
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你能让王道士住手么?他在整理自己的庭院呀,望着一箱箱一车车满载文物的车队,你想拦下么?拦下了,你又送到哪里去呢?比之被官员大量糟蹋,放在伦敦博物馆里不是更好么?面对着愚昧的国人和民族,一句愤激的话“宁赠外虏、不予家奴”该是多么深重,文人秋雨脑中闪现的是“我好恨”。
批判、愤激是容易的,文人秋雨为了民族未来的构建而挥起短铁直刺民族肿包的时候,他能保证不会被肿包围困吞噬么?他的愤激、批判、抗争,环顾中国又能数出几人?无疑在这里文人秋雨的心是悲凉的,这种悲凉是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他深知这一点,为此他好恨。
我想起鲁迅曾在《写在坟的后面》的几句话:“为了我背负的鬼魂,我常感到极深的悲哀,我摔不掉他们。我常感受到一股压迫着我的沉重力量。”
塑造中国文化文人性情的本源,一道,一儒,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是本源生命,它创生万物,天、地、人是它所衍生的,道要求人“见素抱朴”,“复归于朴”,排除操心、思虑、情感,不辨是非、美丑、真假,最后达到与生命自然沟通,“与道冥一”。
道家精神是超功利的,面对人的不幸、混乱、丑恶,一个人能不同流合污、随波逐流而独善其身,“拥孤襟以毕岁”,确也算是一种“超越”,然而一个舍弃广被苍生的柔情、爱意和温良,无视生灵涂炭的现实,以换得自己灵魂的逍遥自适,拈花微笑,于心是否安然,我们倒要询问了。
文人秋雨面对自然,访古、寻古、探古,放不下的恰恰是一颗拳拳操持之心,他有闲情逸致的一面,然而却有一种担当历史使命的责任感,儒家的拯世、救世的热衷也自有它合理的所在了。坐忘、无我、淡泊……毕竟都是些消极的办法,在自然中寻适意,或是像禅宗慧能所说:“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那么这个空是彻底的无滞无待,那么怎么来印证佛的本心呢?
而平常心是道的直接后果,这便导致疾病、冷漠、死亡、腐亡、欺骗的合理性,禅家把道家向前推进,把道变成无知、无识、无爱、无憎的石头,然而王阳明、黄宗羲的文化因子,最终在文人秋雨身上显示出的却是儒家情怀,审美归审美,是一味地适性得意地构筑“桃花源”和“乌托邦”,还是返观尘世“进入魔界”?文人秋雨开始以科学的理性精神,以忧患、慧悟,历史沉思,唤醒沉睡的民族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