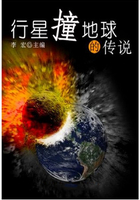我们看文人秋雨《西湖梦》,西湖“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这里有佛都胜迹、道家葛岭,有儒将楷模,有国学大师,这就像一只拼盘,它没有了宗教的庄严神圣肃穆,多的是一种世俗温情,相安无事,把各种信客都陶冶成游客,不像西方宗教那么虔敬舍身与偏执神性。
正是它的世俗性把悲剧化为嬉笑,把执着化为平常化为热闹,再也没有鲁迅笔下急急匆匆赶路的过客形象,一切化为平和,一切化为当下世俗的享受,于是文人秋雨引述川岛回忆鲁迅的话: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子才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罗纱大褂,和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于是,极大的认真伴和着极大的不认真。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凤舞的楹联。也找不到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以凭吊也可以休息的亭台。再也不去期待废墟和重建,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
修缮,修缮,再修缮。群塔入云,藤葛如臂,湖水上飘浮着千年藻苔。
西湖是中国文化的集合体和象征,是杂烩和拼盘,是消磨,是正经中透出的不检点,是中庸和消闲。而显现余秋雨批判力度的无疑是在《西湖梦》中对两个女子形象,一苏小小、二白素贞的文化透视。苏小小是南朝名妓,然而在我们这个以男人为本位的国度,却一直尊贵地长久安享景仰,这里面伏藏着什么秘密?文人秋雨开始了人生追问,苏小小原是纯情少女,遇一穷困书生,慷慨解囊,助银百两,让其上京,然而她失望了,终生有托化为泡影,世界没能给她以情感的报偿,却促使她从对情的执着踏步迈向对美的追求,成为了一代名妓。余秋雨无疑在这里费尽心思,苏小小从妓是被动还是自愿,作者宁愿她是自愿。
在女性身上,色美和情(爱)无疑常常是分割的,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琼瑶(爱)既不可得,那么苏小小就开始了对美的追求,把自己的美色呈之于市。形式并不是主要的,道在山林,道也在尿溺,妓女也只是表征,内里却是苏小小主动地对自己女性生命的烈烈扬扬的宣讲。人在世间的栖居是不完整的,苏小小的从妓意味着她不守节而守美,她比茶花女活得更潇洒。中国的女人,往往为了一个负心汉或为一个朝廷,颠颠簸簸得过于认真,而苏小小这种对生命的肯定,对人性的追求,她那种超越,才是中国文人心中秘藏的一份图腾。苏小小的价值与意义,不在于对妓女生涯的歌颂,而在于她构成的与正统人格的奇特对峙。白娘子呢?白素贞的悲剧就在于她苦苦挣扎、奋斗,想在人世做一个“人”,而尘世中都没有回应。许仙的木讷、萎顿,无法与她的情感强度相对应。
余秋雨是个文人,一介书生,在历史与自然的匆匆行旅中引他共鸣、引他感喟、促他落泪叹息的也多是文人。《柳侯祠》说谪贬在外的柳宗元“惟有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摺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而在《苏东坡突围》中我们读到“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这是善于倾轧长于妨忌的国民性的集中显示,历史的荒唐,时代的耻辱在一根捆扎过苏东坡的麻绳上显现。
在《遥远的绝响》里我们看到魏晋时代“文人的觉醒”极灿烂的人生正剧,人的觉醒是以放弃祈求生命的长度,增加生命的密度开始的,这是中华文化的另一血脉。人的自然性命是无常的、短暂的,终不免一死的,任何关于人的道德规定都无法掩盖和取消这一事实。于是,仁、义、礼、智、信,圣人的明易象、叙诗书、制礼乐、得道德教化于天下的修德济世行为的价值受到怀疑,所以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
“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于是出现了一种醉境的审美世界,魏晋人物晚唐诗,这是一个风流、风度、风神、风姿……的时代,然而这也是一个血腥的乱世,何晏被杀了,张华被杀了,潘岳被杀了,谢灵运被杀了,陆机被杀了,范晔被杀了,嵇康也被杀了。山涛曾形容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这个柳下锻铁的汉子,这个目送归鸿,手挥五弦,铁锻得好,诗写得好,琴弹得好的汉子,最后被处死了。
那时他三十七岁,临死前他让人把琴取来,说:“请让我弹一遍《广陵散》,过去袁孝民他们多次要学,都被我拒绝,《广陵散》于今绝矣!”
文人秋雨在这里能说什么呢?魏晋人物徜徉于山水之际,放荡于形骸之外,纵赤情而蔑礼俗,任己性而随意行,这种对“真”的追求与奠基,没走几步就覆亡了,他们在隐逸中没有得到解脱。这种审美的心境也正是余秋雨所具有的,既愤激又疏淡,既充满激情又富于柔情、温而丽,既有一颗放不下的心肠,又有飘逸旷达、澄明无滞的气质,这种恻然若忧的仁心,忧不失乐;超然而至乐,而乐不忘忧,澄明与忧心,共系一体,就是文人秋雨的人品文格,也即所谓的逸兴与沉哀。
当下的时代,是后现代主义走俏,游戏、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终止一切诗意唤神的本性,放逐一切具有深度的精神价值,走向精神的荒诞和不确定的平面。这种风潮在现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真正的文人,我以为是像余秋雨这样的直面人生苦难、体验着深渊并敢于进入深渊冒险的人。他在现代人情感萎缩中唤醒人对存在状况的思考,投一束光亮照彻幽昧的暗夜,重新寻找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
“在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这一问题将永远地回旋在我们每个诗人的心中,而所谓的艺术对现实的精神超越,也并非高举远翔不知所终,而是体现在“诗意地栖居”上,它意味着去注意、去歌吟、去追寻远去的诸神。
荷尔德林说:
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
栖居在这片大地之上。
我也可以说是这样:
人的纯粹远远超过,
缀满繁星夜空的幔帐。
……
人的存在和超越并非要进入一个虚幻渺茫之域,而是立足这生养死葬的大地,使生活成为有意义的生活、使诗意的栖居成为人之为人的本体根基。然而,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使人们的主体性的定位产生迷惘,人“活着”本身便成了目的,企图改变生活、诗化生活的人,都成了白痴。这个时候,我们看文人秋雨是多么的悲壮,在中国当灵魂的追问者都丧失了灵魂,都失去了追问的兴趣,那么,我们活着也许就不为什么,活着就是活着,但是苟活与死又有何区别?
余秋雨出生在余姚的农村。窗外是茅舍、田野,再远点是绵绵群山,童年的岁月便是对着无穷无尽的山遐想。在《夜雨诗意》里他对人类越来越远离诗意感到担忧,荒山夜雨可怖,但此间的诗意却是无与伦比的充沛。现代的贫乏,世界之夜已到夜半,社会因追名逐利而动荡,为贪娱求乐所蛊惑,一切的原始的诗意被破坏,我们怎样追求诗意、追求神性?这个时候,我们不禁想起余秋雨的《文明的碎片》题序中记载的一个故事:有一天上海街上一辆公共汽车突然熄火,驾驶员请求乘客们下车推一把并帮助发动,请来请去,下去推车的只是一群春游的小学生,小学生憋着吃奶的劲竟然推动了这辆挤满大人的车,而当他们上车一看,车上的座位已被大人们抢走。
这无疑是一个现代寓言,人追求诗意生活,在于本身他能趋向神性,仰望神意之光,用神性来度量自身,正是这种度量使人们的生存本身显出诗意。这公共汽车就是生活,无疑孩子们的举动是一种诗意的显现。人之为人的天命,在本质上是诗意的,但是人们往往背离神性,而追求诗意,在现代就是只有倾听,倾听自己的内心,倾听天地的神秘声音。从这个方面来说,余秋雨是一个倾听神性召唤的人,他向人们转达自然山水人世风物中神性即将到来的消息和问候,指引人们返归故乡的路径,所以,文人秋雨歌唱大地山河,歌唱月亮与日光,歌唱一切善美,这就是种诗性的显明。
人们奔忙于营造,强调这种对诗意的倾听无疑是必要的,追求外在愈多,人变得越发轻佻,越发没有虔敬感,越发没有蕴实的内在,无视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以为那是可有可无,从而人们和整个世界便会变得浮薄与轻狂。唯有当人在内心中蕴有神圣的东西,蕴有必须小心蒙护的东西,蕴有不愿意神道的东西,人生才有依挂,灵魂才不至于空虚,历史社会的人才能与自己的自然相互为友,相互恩爱,这样人们就会诗意地栖居大地,我想这也许是文人秋雨一生中所追求的东西吧。
文人秋雨好浸淫于山水清音之中,好在书简中卧游,“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庄子》)。在生命体验中,人与世界,小我与大我,瞬间与永恒融合为真正的艺术,是一种诗意的凝聚、一种精神的贯注、一种充盈了生命气息的律动,然而我想到余秋雨《龙华小记》的结尾:
孤标独立的龙华塔只想舐风蘸雨,在悠悠蓝天上默然划过,而不想在《高僧传》上记下一笔,且把现代的繁盛看成可以对之拈花一笑的大法会吧,承受过历史之神诏喻的文化灵魂,最终还要归于冷清和沉潜。
秋雨先生有一双历尽沧桑又不忘情的慧目,历史的轮回悲剧又怎能躲得过他这灵眼一觑?想来现在他在上海戏剧学院的排排书架下,慢慢地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