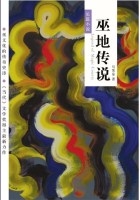季工作组晚上于大队部的土炕上睡,有根盈一班青年伺候,烧炕打水,总算捱得过去。季工作组乃一介武夫,在外多年,也习惯了这种孤旅生活。一日下午,外面下起小雪。季工作组独自坐在窑里歪着个脑袋发呆。正在这时,突然听到窑外头有异常响动。回头一看,只见是一位白净面皮的妇女探头探脑。
季工作组立刻惊觉,质问道:“来人谁氏?”那女人怯生生走了进来,屁股挂着炕沿坐了。季工作组歪着头,去瞧了她一眼。嗨,这一眼只没喝彩出声来:
好一个水亮的婆娘啊!这里有诗说她:
羼羼娜娜身儿,白白嫩嫩手儿;
慢说杨柳不禁风,由你放长丝儿。
干干净净袄儿,妖妖郁郁神儿;
任由须眉有英男,勾魂摄魄种儿。
看到这里,季工作组缓和口气,问她:“你是谁家的,我咋没见过你?”
那女人莞尔一笑,说:“我屋在村西,男人姓张,叫富堂。大前天晚饭时节,我看着你和一拨人从门前头说说话话走了过去。这前日,我回我羊甫河,与我姨家的女婿说话。说来说去,原来你是我姨家的外甥。”季工作组问:“你姨家在哪里?”富堂女人说:“在齐家河。说起来咱还是表亲关系。那女婿娃将你的好处说了一拉拉子。说你做碎娃时,就显出与众不同的地方。说你带着一班碎娃,在庙前头如何弹弦如何言说,说你生来就有为官之相。”
季工作组脑子搜索了片刻,回过脸,望着窑顶。又低头,见她一只白嫩的手指,抠着炕头的席篦子,其相甚悄闲无聊。想起叶支书汇报工作时说的,这村里有几个屋里人(婆娘),从没有说是正正规规下地干活。看她的面情模样,似乎就这类人。遂诈她道:“听群众反映,说你一年四季很少参加集体劳动。”女人一听这话,扬起头来,登时眼睛红了,愤然说道:“人都胡传,他们咋就晓得我一年四季不参加劳动?要不是这鬼病缠着我,我不愿意参加劳动拿工分,是嫌工分咬手咋哩?”季工作组平静问她:“啥病?”女人背过脸,看着墙上的主席像说:“类风湿病。请了一拉拉的医生,中药吃了几笸箩,就没有个见好的趋势。”季工作组说:“毛主席关于病这东西,有非常精确的论述,他说,病这东西,全在乎个心劲。心劲散了,即就是吃的人参,也不见得能有什么起色。毛主席开出了一个方子,是要靠运动。一运动,血脉一活通,病自然就消除了。”女人点头,说:“这话在理。而我不也是的,这半年来,我从没说是好好歇过,田头扔下锄把,灶头拿起勺把,从天明忙到天黑。”季工作组说:“你来啥事?”女人这方说道:“昨黑里我娃他大说起你,说你如何的精明如何的本事如何的口才。我说你还是自家屋的亲戚。娃他大起初不信,说咱祖宗坟头上就没这风水,还能有这么大的官做亲戚?我给他细细一说,他才信了,但还不确实。我说你试看,人来便知。娃他大说,即是自家屋的亲戚,那就连同自家人一样。你忙拾掇一下,叫到咱屋里来,吃顿饭,也是咱的一片心意。我说,人家季工作组是国家干部,不知会不会嫌弃咱屋这穷堂灶舍的。娃他大说,这你放心,季工作组最体贴疾苦不过。我说,我明个去请。这不,今日个,请你来了,只盼你甭嫌弃。”季工作组说:“嫌弃倒不嫌弃,只要是贫下中农家庭,都可以去,没有说厚此薄彼的。但党的政策在那里放着,一再要求要六亲不认。不过,像你说的这情况,吃顿饭,拉拉家常,自是人之常情。”富堂女人抬脸一笑,说:“那好,今黑我收拾彻业(齐备),到时候叫娃他大再来请你过去。”这季工作组竟不多想,点头应允下来,一双眼睛盯着那婆娘,看着她立起,走了出门,又抬高嗓门补充一句道:“我不送了。”女人外头回话:“不送不送。”季工作组心想,这真是:贫居闹市无人问,富住深山有远亲。
果然,天黑时,一位提着烟锅的老汉走进大队部院子。负责治安保卫的民兵拦住盘问,说是请季工作组去吃饭。季工作组正与叶支书一班人开会,听到民兵汇报,便对叶支书说:“今黑甭派饭了,我有地方吃了。今天早上才晓得,你村西头住的富堂,是我的表姐夫。人家一再相请,难为不过,今黑就到他家里吃饭。”
叶支书一听大惊,忙道:“原是这相,快把老汉请进来。”民兵到门外呼喊。老汉一进门,叶支书一班人急忙下炕迎上,口口声声富堂哥,搀着老汉上炕坐好。老富堂几辈辈没受过这等抬爱,一时间手忙脚乱,点不着烟锅。最后还是根盈拿了油灯,给对上了。
季工作组带了县上刚发的红宝书来到富堂家吃饭,热炕上一坐,让富堂家的一个男娃一个女娃好生稀奇,争着抢着看那红宝书。季工作组慷慨地递给他俩,说:“甭弄坏了。”任由两个娃争抢。富堂也伸手试脚,凑上去看,诧异地问:“这是啥?”季工作组郑重地说:“是毛主席语录。日后我们无论做啥事,都得靠它了。上面写得周全,天上地下无不包揽,啥都说到了。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富堂若有所悟,说男娃:“扁扁丢手,给你叔放下,那也不是你碎娃的耍货,弄脏了该咋?”富堂婆娘在那边正冒着热气的灶火下面,听说此言,也忙走过来,看着扁扁在油灯下手拿的语录,说:“啊呀,值贵得很,扁扁甭占住,叫姜姜念念写的啥。”那叫姜姜的女娃如何抢得到手里,临了还是季工作组要了回去,并当场打了开来,大声读道:“你们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念罢指点给富堂说:“你看,毛主席说的话多么在理,只没说把咱这人间社会,男男女女的鸡毛蒜皮的所有道理,都一律摸得通通透透。你看伟大不伟大?”富堂虽然懵懵懂懂,却连连点头。
正说话,富堂婆娘端上一只四方食盘,里头四样小菜,一碟辣子一碟盐一碟萝卜缨子一碟腌白菜,有红有白,收拾得甚是清爽。季工作组朝后挪了屁股,闪开一片亮处,帮着放下食盘。紧接着面条端上来,他和富堂对面坐好,拿起筷子,转身说富堂婆娘:“你也上来吃啊。”只听那婆娘在灶头说道:
“你自顾吃你的,我和娃在灶台吃。”
这一顿饭吃得滋润啊!正如叶支书所说,富堂婆娘虽是体弱多病不事辛劳,却擀得又细又长的好面。季工作组尖嘴伸着,吱溜吱溜,没过多大会儿,竟是两大老碗面条下了肚。吃完饭,擦了汗。富堂婆娘说:“再给你舀些。”
季工作组忙说:“不了不了,吃得舒坦啊!”说完长出气。富堂搁下碗说:
“吃好。”季工作组说:“吃好了,吃好了,到咱屋不说做假。”富堂婆娘说:“说得是。没说你到这儿就到了自家屋。自家人啥都方便。日后干脆就到咱家里吃饭算了。吃派饭虽然便当,但总是不会恁可口不是?”季工作组说:
“那是那是。”季工作组说着,忽然间发现灯光下那婆娘愈发是显得唇红齿白,招人怜惜。再看富堂,显老不说,一脸榆木皱纹,憨实得像瓦门墩,极不般配。一边看一边掏出包纸烟,抽一根给富堂。富堂扬起烟锅说:“我不逗纸烟。”季工作组坚持说:“你吃上一根看。”富堂手颤着接了。两个人就着灯火点燃,吃了起来。季工作组看来不甚吃烟,吃一口吐一口。一根烟吃完,这才论起亲戚之间的事由来。季工作组说道:“我做碎娃时就参军走了,所以乡党是谁,亲戚是谁,我都不认得了!”
拉呱一阵,季工作组抹起袖子看表,说:“快十点了,我得走了,不晓根盈烧炕没。”富堂婆娘说:“就睡咱屋,东边窑炕热着,暖暖和和,比大队部强出十倍。”季工作组说:“那不成,明早还有许多工作须当面安排。”说完下炕,由富堂和婆娘陪着,出了窑门。
到了院子,只听富堂婆娘说:“你到咱东边窑试看一下,觉着行,啥时搬来都成。”季工作组答应,随女人到东窑,富堂忙点上油灯。季工作组一看,果然是好去处,白晃晃一面展炕,烧得暖和不说,四围都糊着报纸。炕台桌面,收拾得整齐洁净。炕上一床拉开的花红被子,像是早就给他预当好了似的。季工作组不禁赞道:“不错不错,我但要来,明日就给你个话。”因见富堂婆娘喜笑颜开,便问:“这窑日常没人住?”富堂女人撇嘴一笑,说:“我嫌娃娃们泼烦,日常一人在这里睡哩。你但来,便由你来睡。到了咱这儿,冷热总有个照应不是。”季工作组也不多言,出了窑门。门楼底下,与富堂少不得又是一番话别。
告辞之后,季工作组抬头看了看星星,大声咳嗽了几下,然后撂开腿子,一颠一跛地朝大队部走去。夜到这时,分外安静。马路两边树木和猪圈,都变化出许多稀奇古怪的黑影。季工作组虽是当兵出身,但在这荒僻野村,心里头总有些胆怯。现在阶级斗争形势复杂,说不清什么地方藏着坏人,随时会扑出来,向你报复。走了百八十步,突然听得隐隐约约有人语传来。这声音小得像是自己臆想中的鬼怪。季工作组立住,扎起耳朵仔细辨析,似有人在小声呜咽。季工作组提高警惕,克服自身障碍,轻手轻脚地闪身过去,果然,一家门洞里,圪蹴着一个黑影,自顾哭泣。季工作组大声喝道:“你是谁氏?”那黑影咕哝着。季工作组说:“大声点,我没听清。”黑影大声说:“有柱。”季工作组想起人常提说的村里那个二尾子,点头说:“我听出来了。这乍晚了不睡觉,号得咋?”有柱说:“我娃把门闩住,不准我进门。”季工作组说:
“看你说的,你一条七尺大汉,叫屁大的娃娃管住了?”有柱说:“我那贼娃瞎(坏)着哩,你不晓得。”季工作组帮忙敲了几下门,又去推,嘎吱一声,门自开了。季工作组说:“熊囊子卖豆腐——人软货瘫!门开着,你自家蹲着不进去,怪谁?”有柱忙立起,扑死拉活地蹿身进去,像是怕娃再闩了门进不了似的。季工作组暗自一笑,心想,农村就是农村,各式各样的怪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