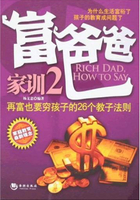动手抓杨文彰是一日凌晨。学生娃娃从家里出来,但见灰乎乎的马路两边,贴着许多标语。上操时感觉也不同往日,首先是那黑脸校长没有出来督阵。体育老师也不说正经喊操,偶尔叫一声,也似从石头缝里憋出来的,生狰冷倔,任由着学生绕圈。跑了几圈,下来说是拉开架势做广播体操,此时只见学生们轰声乱了。回头一看,原来是民兵连长吕青山带着几个如狼似虎的壮汉,手持钢枪,冲进校门。说起来也不知是哪年哪月哪个朝代,谁狗日的兴下的规矩,遇事便拿读书人开刀。杨文彰老师起初还在那里装模作样地扭腰摆胯,活动筋骨。人群大乱之时,他还伸着脖子去看热闹。正觉好奇,只见吕青山指他一下。他以为咋的,仰面一笑。几个壮汉走了上来,啪啪几个巴掌,打得他口鼻喷血,跌倒在地,几番想硬撑着站起来,都被民兵压下去。真是所谓的英雄气短。只可怜他一个风流才子,没来得及表演读书人的风骨,便被人家连推带搡,押出了校门。经这一闹,学生们一时三刻竟不能安生。这时候,黑脸校长黑着脸子从校长室里探出头来,将学生又拢在一起,宣布了县上停课闹革命的指示。
接下来便不能不说是一段阳光明媚的日子。学生们再不用像乌龟一般将头搁在桌沿上,无论你愿是不愿,都得睁着两眼去听那些狗屁课程。他们可以去打鸟,可以去河里抓螃蟹,可以去偷豌豆角,可以不上课。没人敢说哪里比学校更有意思。这里头好玩的名堂多了,不能一一尽述。总之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了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季工作组亲自发动了鄢崮村的“文化大革命”,给娃娃们带来的好处。那些天里,每逢风和日丽之时,就可以看见季工作组提溜着一条腿子,在一班民兵的搀扶之下簇拥之中,像是浮在水面的王八,无论他使力不使力都不会沉陷下去。竟可谓是人人称道的鱼水之情。季工作组多年之后,想起这段时光,也不无感慨地默默承认,说他那时曾是十二分体面地走遍村子的角角落落,倾听贫下中农的呼声,视察运动进展的情况。人们尽管日子一天苦似一天,但总还是觉着,以后时代的许多新鲜风尚,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抓杨文彰的那天早上,鄢崮村又生一件奇事。即早该进屠宰场让屠户法堂一刀子捅了的老花马,居然经过最后挣扎,生下一只小马驹来。村里人喜之又喜,伸着鼻子跑到饲养室,来看这血科拉碴的东西,是怎样从那胎衣里挣脱出来,跑到这个给它准备了许多笼套,却没有准备许多青草的世界上。接下来,黑女大(爸)忙得脚掂在肩膀上,和他的婆娘女子,又是熬米汤又是磨豆粉,像自己得了儿女一般。
晚上开社员大会。会议太重要了,所以黑女大也得参加。老东西熬了一夜,太乏了,靠住墙睡着了,鼾声大得影响到会议的正常进展。季工作组感到非常吃惊,立起来透过灯光,将老汉看了又看,心想,世界上竟有这等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不当事的。于是抬手向大队文书根盈示意,文件缓念,叫醒黑女大,说道:“老汉同志,你立起。”黑女大立起来,摇摇晃晃不知何事。季工作组说:“你立正。”黑女大还是晃荡,不知如何立正。季工作组突然高腔喊道:“立正——”这完全是部队的正规号令,弄得老汉更是没了主意,一屁股坐下去。
季工作组指着黑女大,转脸问叶支书:“这老汉是咋搞的?”叶支书说:
“老汉除了喂头牯,是啥不晓得。”季工作组说:“是吗?这样下去怎么能成?把老汉拉到主席台上,接受教育!我这次到你们这里,主要就是解决这个是啥都不晓得的问题!”民兵得令,刚说揪住老汉袖子,黑女大两脚蹬地,撒魔连天地喊叫起来:“我自碎娃时候要饭,揪我咋哩!我自碎娃时候要饭,揪我咋哩!连要饭的也揪,乃也太可怕了——”
会议气氛刹那间变得热闹起来。黑女大尽管拼死挣扎,但哪能经得住一班民兵小伙子的摆置?三槌两梆子,就给抬到主席台上。季工作组批评他道:
“你老老实实站好,听会议文件。像你这样的贫下中农,我们并不是要批斗你,只是要你耳朵扎起好好听,接受教育,知道了吗?谁说是批斗你了?看把你吓的!”
黑女大一听这话,稳住了些。这时候只听根盈一旁说道:“文件念完了。”季工作组说:“你胡扯,可没咋的,就念完了?”叶书记抬头说:“真念完了。也看再咋?”季工作组说:“按会议安排正常进行!”
说话之间,只见叶支书一起身,门外随后格踢嘹嚓一阵乱响,几个民兵将一个头发蓬乱的人物架了进来。台底下社员纷纷立起看是谁氏。此时的杨文彰,眼镜没了,一脸黑灰,人只比平日矮了几寸,相况看上去极是龌龊凌乱,即所谓斯文扫地是也。根盈慌忙带领大家呼起口号。场下稀稀落落只是几声,就说毕了。季工作组一看,急了,指责根盈道:“你弄下个毬嘛弄下个啥嘛!”说罢舞扎着手,指挥社员们坐下。
社员们刚坐下,黑女大便立不住了,欲要退下。季工作组及时喊住他道:“你老汉先缓下去,今天,先由你来揭发。你认得立在你眼前的这个人是谁吗?”黑女大说:“这谁不晓得,是杨师。”季工作组说:“看,我说你老汉缺乏学习,你还犟哩,像他这种人,咋还能给他叫杨师呢!他是反党分子,你是贫下中农,你的阶级立场跑到哪里去了?”黑女大只不敢言喘。季工作组说:“现在由你先说,说得好,你便下去。”黑女大说:“我不晓该说啥。”
季工作组说:“你细想一下,过去你见他干过什么坏事没有?”黑女大低头沉吟了下,道:“没见,就一次,我在埝盘地里割草,他在柿树底下,跟在我尻子后头,拉开嗓子地念书,把人聒得没法子。我还心想,杨师这人,这是咋了,专一扰我哩。”季工作组连忙追问:“读的是什么东西,你听清了没?”
黑女大说:“听清了,说是暴风雨就要来了,暴风雨就要来了,当时我就稀奇了,日头红哈哈的,咋说暴风雨就要来了呢?再有的就记不清了。”
杨文彰回过头,枯喇着嗓子说:“那是高尔基说的。”季工作组立即打断他,道:“放老实点,明明是你立在老汉后头喊哩,怎赖得着人家高二斤!高二斤是哪个村的?”黑女大说:“不晓得。说这话的人是他,不是高二斤!我老老几十岁的人了,还能哄人?”季工作组说:“你反映的问题很好,这件事根盈且记录在案,你先下去,念你最近忙于管理牲口,不再追究你今黑的表现了,日后要抓紧学习。”黑女大这方走了下去。
根盈立刻喊刘社宝。刘社宝是学校五年级的班长,长了个人见人爱的圆蛋蛋模样。昔日曾见天随在杨文彰屁股后头,深得宠爱。杨文彰曾无限欢喜地摩挲着他的头,对其他学生说,刘社宝总有一日会成为鄢崮村的人尖尖,不定能成个作家哩。刘社宝当即觉得他已经是了似的,让同学一旁羡慕得不成。刘社宝走到主席台前,拿出早就写好的一份稿子,用非常好听的普通话,念了起来。稿子写得太好了,用了许多词汇,非一般人能来得。底下社员一边听一边啧啧称赞。社宝他妈,大概已早知晓她娃今黑里要出尽风头,特意坐在灯火亮处,挺着面子,眼光四射,将宝贝儿子的所有举动尽行收看。
下来发言是猪娃,猪娃情形和刘社宝比起来显见差远了。自己吓得抖抖不说,声音小得像蚊子,只有他自己听见。稿子亦不怎熟读,一路吭哧吭哧,逗得人群哄笑。季工作组脸上挂不住了。幸亏吕连长带着一班人马,风风火火走了进来。主席台上坐好,对着季工作组的耳朵,说:“问题查清楚了,等会散了,给你和叶支书详细汇报。”说完又立起,走到台前,将见了他便索索发抖的杨文彰顺手务治了几下,促他低头站好。据说杨文彰已被他单独“修理”过几次,眼看是“修理”服帖了。会议继续进行。接下来是人称贺大谝的贺根斗发言。
这家伙的确是名不虚传。只见他也不用稿子,立在主席台上,腰系麻绳,袖着双手,落落大方地先念了四句诗文:“社会主义实在好,劳动人民能吃饱;社会主义道路宽,人民力量大无边;社会主义灯儿亮,贫农子女上学堂;社会主义要发展,斗争杨师不能缓。”叶支书插言:“不能再叫杨师,是杨文彰。”贺根斗连忙改口道:“对,对,是杨文彰。”然后一扬手换了口气,道:“今日个,我在这里,要揭发批判杨文彰勒索贫下中农子女的学费问题。
我儿孬蛋,说来也是去年的秋天,开学没有三天,一日里哭着回来。我问娃咋,娃说,他杨师叫他回来取钱,没钱就甭上学。看娃哭得可怜,当时我便跟着流了眼泪。心想着,这叫咋?旧社会地主老财逼迫咱贫下中农,现在是新社会了,地主老财打倒了,还有人逼迫咱贫下中农。试问,这是把他家的是咋了?杨文彰啊杨文彰,你比地主老财还厉害。地主老财偶尔还允人宽限几日,而你是喝住着要哩,把我儿孬蛋可怜的,硬是从学校里被撵了出来。娃哭得呜呜呜,脸憋得像灯笼。杨文彰你说你,你的手段是不是太狠毒了?”说着说着,贺大谝居然流下了痛心的泪水。
根盈连忙又带领群众喊起口号。斗争会出现了高潮,杨文彰的头这时低得愈发厉害。季工作组脸上终于有了喜色。等口号声落下,季工作组站起来,咳嗽几声,说起来:“广大贫下中农社员同志们,贫农社员贺根斗的发言,说得何等好啊!请大家认真地思考和领会他的发言。他的这个发言,是在给大家讲着一个道理:地主阶级虽然被我们打倒了,但现在又有一批人,在干地主阶级所不能干的事,继续欺压我们贫下中农。我们大家眼前立的这个反动分子杨文彰,就是这号货色……”
如此等等,这一通发言,如金玉掷地,铿锵有声。季工作组本人自然也在鄢崮村人的心目中变得更加高大,更加顺眼了。甚至连同他那张窄脸和跛脚,也被人们羡慕起来,似乎这更使他不同凡俗,气势铮然。
话赶这里,却问这季工作组何许人也?季工作组,大名季世虎,小名虎娃,邻近的葛家庄人。幼时放羊于西沟峁上。一日晌午,见一位背捎马(马褡子)的汉子,从沟底缓慢上来,到附近崖下,一个踉跄,随即卧下。此时季工作组尚是手脚灵便的儿童,跑了下去,立在一旁观看。但见此人眼窝实合,喘气不匀。一看便知他是因为饥饿,才倒毙在此。
也许是季工作组命里该有神人救助,他竟是奇之又奇地取出自己的半块玉米馍,给那汉子塞到手里。汉子一见吃的,立刻一把抓住,三口两口咽了下去。又递给自个儿带的水葫芦。那人接过,掀开盖子抿了几口,还给他。片刻工夫,汉子缓过精神,将他是上上下下打量一遍,问他生辰八字,他一一禀复。那人抻出指头一掐一算,有板有眼地说了起来:“好娃哩,你天门上有颗魁星,地坎上有条祸沟。这辈子你是因祸得福,又因福跌祸。但福不能无缘而赐,祸不会无故而降。按你眼下的年龄推算,再过一十八年,你祸沟溢满,魁星隐蔽,当有灭顶之灾。今日遇我,合该你娃有福。我予你将祸沟疏通,天门摆正;成年之后,官至七品,应受当朝百石俸禄。今生即有大难,也不至于殃及性命了。”说着,唤他就地平展展躺好,在他身上脸上,指手画脚地抚弄了一番。完毕,那汉子哈哈一笑,道:“好娃,你我今日也是缘分,数年之后,你我还会有一遇。”说罢头也不回,朝着东边一条土路,飘然去了。
这汉子说得果然有些神通。一十八年之后,季工作组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一架美国飞机扔了炸弹下来,同战壕的三个战友,都一命归西,而他除伤残一只腿外,其他竟都完好。回来后先是当农机站的副站长,后来在鄢崮村搞了一年的运动。到县上不几天,便被当选为县革委会主任。你说这不是官至七品又是什么?半个玉米馍馍,换了个七品县官,谁说不是天大的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