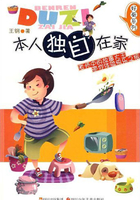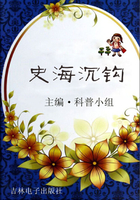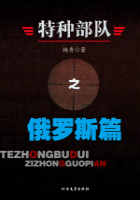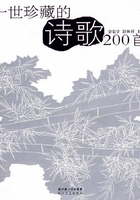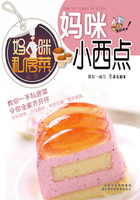天地从太极到八卦的生成变化之道
古人很早就研究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规律,试图把握它们,从而为自己服务。最开始的时候他们采用了宗教神话的方式,通过拟人化的想象把自然天地想象成和自己一样的人,而试图通过祭祀来博得它们的欢心,以给他们带来福祉,在面对未知的时候,他们多采取神秘的方式,如通过扶乩、占卜等方式来解决。慢慢地,人们通过长期观察,对自然有了进一步了解,掌握了一些自然规律,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哲学,人们开始通过哲学的方式来把握天地的变化,并且由此而描绘出了一幅世界图式。《易经》就是在这个转变当中的产物,它虽然是一本占卜的书,但是却在其中包含了古人对于自然生成变化的某种看法,这种看法通过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表达出来,其实质就是用阴阳两种元素的对立统一来描述天地万物的变化。
《易经》的体例是以阴阳爻为基本单位,进而以三个爻为一组排列组合而成的八种自然存在为基本符号两两相叠而成的。阴阳爻分别象征着阴和阳这两种对立的力量,三爻一组所形成的八种排列则成为了天、地、雷、火、水、风、山、泽这八种自然存在,也就是八卦,八卦的两两相重而成六十四卦,每一卦之后都有卦辞,每一卦的每一爻都有爻辞,对之进行解释。六十四卦的排列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隐隐透露出某种规律。
《易传》就已经完全是一部哲学著作了,几乎已经完全摆脱了《易经》的模糊和神秘色彩,它通过卦名的含义来解释卦辞和爻辞,成为以后周易流派中的义理派的先驱。
《易传·系辞》提出了太极的概念,用以描绘宇宙最原始的阴阳未分的混沌状态,是形成天地万物(宇宙)的本源。《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既是对使用蓍草进行占卜的过程的描述,也是对天地形成过程的描述,因为在古人的观念中,人无非是缩小版的天,是对天的模仿,所谓“推天道以明人事”,所以决吉凶,断是非的占卜过程也必须是对天道的模拟。
就占卜而言,这是成卦的过程,未分的蓍草象征太极,分开后就形成了阴阳二爻,也就是两仪;阴阳爻两两组合有四种可能,就是四象,四象再与两仪分别结合,就形成了八卦。就宇宙生成而言,太极代表混沌未开之时,太极分而为两仪,就是开天辟地,两仪就是天地,天地有四方,是为四象,四方再细分而有八方,是为八卦。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诸子百家都讲“道”,但是大家讲的“道”却不是同样的内容,各自强调各自的道,所以才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当然,这其中谈论“道”最著名的当属以“道”冠名的道家,道家的创始人就是老子。老子到底何许人也,一直到今天还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但是五千字的《道德经》却是人尽皆知的道家经典。
老子在《道德经》中向人们描述了一种从道到变化生成万物的图景,这就是他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首先,道是化生万物的源泉和基础,是所有一切的根本。“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是说,有这么一种东西,比天地万物都要更早更先地存在着,它完全独立,不依赖任何东西,静静无声地永恒运动着。老子认为,这个东西是天地万物的母亲,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叫做什么,所以勉强自己给它起个名字,叫做“道”,或者叫做“大”。
这个“一”再按照道的规律运动变化,就生出“二”,二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阴、阳。这是古代中国人对所有事物属性的一个最基本的区分,万事万物不是阴性的就是阳性的,阴阳构成了一切东西。
“二生三”,就是阴阳的互动、变化,生成了所谓“冲气”,阴、阳和冲气,这就是三。也有人说,这个三是指天地人三才。总之,阴阳互动及其所形成的冲气就共同形成了天地万物,这就是“三生万物”。
万物为道所生,就应该遵循道,而道则自本自根,按自己的本然状态运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要向大地学习,大地虽然默默无声,却承载着万事万物,也为人类的繁衍生息提供着一切所需,这就是大地的美德。大地要效法天,因为天时决定着地的变化,而天还不是最高的,天要服从道的规律,因为天也是从道中产生出来的。
“道法自然”,所谓“自然”,不是我们今天的自然界的意思,而是“自己”的意思。“自然”也就是自己之所是、自身的本然状态。那“道法自然”就是说道是最高级了,没有在它前面的东西了,它完全按照自己的内在规律运动变化。
这些都显示出独特的来自老子道家的智慧。
小九州与大九州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总括先秦诸子为六家,邹衍就属于其中的阴阳家。
“阴阳”两字语出《周易》,阴阳家是活跃于战国时期,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社会人事的一个学派。他们将先秦流行的阴阳观念和五行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宇宙观。邹衍就是阴阳家中的代表人物,他是齐国人,曾就学于稷下学宫,后仕齐、燕等国。邹衍的学说最著名的除了“五德始终说”就要数“大小九州说”了。
中国古人认为大地是方形的,而天像一个半圆形的盖子倒扣在地上,并认为自己处在大地的中央,周代有所谓“九服之制”,实际上就是以周的都城为中心,以距离都城的远近来划分天下的一种世界图式。九服之内又有九州,九州之外称作“四海”,指的是“夷”、“狄”、“戎”、“蛮”,而不是后世说的东西南北四海,而所谓的八荒则是指距离都城极远,已经超出九服范围的地方。这样一个对于世界的描述载于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尚书·禹贡》当中。
邹衍本来也是儒者,然而在战国乱世,儒者宣扬的以仁义治天下的主张,与攻伐夺取的时代背景是不相符的,因此根本得不到重视,作为儒者的邹衍也得不到重用。于是邹衍就创立新说,用奇异宏大的理论来迷惑君主,从而博取功名。在这种转变中,邹衍刻意地要破除儒者的权威,以迎合战国诸侯君主希望在理论上对抗儒家理论的要求,大九州之说也就由此而生了。
邹衍说,儒者们所说的中国,不过是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叫做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有九州——就是《禹贡》中提到的九州,这其实是不能叫做州的。赤县神州之外又有像赤县神州一样的州同赤县神州一起,一共九个,这是小九州。小九州之外有海环绕着它,而在小九州之外又有和小九州一样的“岛”共九个,这是大九州。大九州之外又有海环绕着它们,再往外就是世界的尽头,天和地连接的地方了。这就是邹衍的大小九州说。
邹衍的大小九州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山海经》和《淮南子》都受到其影响。《山海经·海外经》所述地理区域全在邹子外八州之中,而《淮南子·地形》篇更是前者的缩写。我们现在常说的“四荒八极”也源于邹子之说。大小九州说的产生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水平和眼界提高的结果,标志着人类对于世界的了解大大增加了。邹衍九州之说把海洋纳入了它的世界图式之中,对于世界的广大做了合理的揣测,虽然同实际的情况并不相符合,大部分出于想象和杜撰,也有政治目的在其中,但却大大地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原来世界如此之大,中国不过是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而已。
万法皆空
佛陀释迦牟尼圆寂前留下一段偈语,告诫众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就是在说“空”的智慧。佛教认为,“诸法缘起性空”,法,就是现象的意思。这也就是说,人世间的一切现象和遭遇,都是因为某些条件巧合,拼凑而成的,都没有自身的真正本质,都是一场大梦而已,像泡影一样易碎,像朝露闪电一样易逝。大千世界,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奔波劳作,生老病死,就这样延续了成千上万个年头,并且势必一直持续下去。当然,一个人一旦领悟了这个“空”的道理,也就可以解脱了。
生活就是由很多因为我们随意或偶然的一个念头、一个选择所偶然发生的事情组成的。你下班以后可以选择乘地铁也可以选择乘公交,可能你随意选择了其中一个,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与你选择另一个完全不同,看见的人,看见的事,看见的物,都会不一样。同样,你看见的那些人,他们也同样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只要那千万人中有一个人一转念选择了别的路线,你所见的又会不一样,所以,你看见的场景,就是千万人随意选择而偶然发生的一个现象,这一幕场景很容易因为其中一个人的一个念头的改变而改变,佛教因此把这个叫做“空”,一种因为缘分(缘分的意思就是偶然的临时的条件)而拼凑形成的现象,这种现象因为太容易变化,没有固定的本质,所以其实是“空”的。
接下来,“心”与外界环境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才算是好的呢?《金刚经》说:“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
若心有住,则为非住。”还说:“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真正道出了佛教的本意用心。不管怎么讲,人总是要“住”的,关键是看怎么“住”。“住”是佛教专用语,类似指常住不变,意指执著、念想于某事某物,简单说就是停留,滞留,执著。有心去“住”,或者有“住”的心愿,就会执著于“住”或者所住之物;只有“无所住”,才能真正得到心的解脱,而人又做不到“无所住”,那最好就是什么都住,什么都住也就是什么都不住。所以,“住”不是关键,关键是有心去住,还是无心而住,客观上怎么住、有没有住都不重要,主观上有没有“住”的“心”才最要紧。可以看出,这种“无所住”其实应该是什么都可以住,而关键在于“生其心”,应该是一种不为一切外物所累所动的淡然心态,这与马祖道一的“平常心”如出一辙。
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宇宙不过是在我心中,我的心便是整个宇宙。这与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它的提出却要比贝克莱早四百多年,它是十二世纪中国心学哲学家陆九渊的名言,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才不过十三岁。
他为自己论证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这个论证因为作者尚年轻,看起来似乎文不对题。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事实,中国的哲学并不同于西方,无论是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旨归,还是问题的论证,都迥然相异,中国式的智慧,有时更多是一种顿悟、一种姿态、一种执念。对这句话的解说,我们不妨从一个小故事说起,故事的主人公是陆九渊的后学王阳明:
一日,王阳明与朋友同游南镇,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道:
“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王阳明的说明非常优美,透着几分中国式的机智。同贝克莱一样,这种看法,也同样有着“唯我论”色彩,但是无论是陆九渊还是王阳明,却都是要做圣贤的,这句话的意思也只不过是说,圣贤也是在你心中的,只要你想,就有可能。所以,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圣贤,并不难,如果你能反求于自身,就不难发现,每个人心中善根已驻,无须外求。
陆九渊不像朱熹那样遍求名师,博采众家之长,而是直接师古——直承孟子的心性论;师心——发明自己的本心,这心就是孟子说的“人皆有不忍之心”。皆有美丑、善恶、是非等基本的内在良知。这个此心就是知敬知爱的仁义之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人的这种本心失去了、迷失了,所以,人之为人,不过是“求其放心”而已,通过内心返察的功夫,发现迷失的本心——圣贤心。至于如何发现和发扬自己的本心,他说要先“立乎其大者”,就是要相信自己的本心是善的,相信“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一切都是自足于心的,“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他说,道不外求,而在自己本身。心学的特点就是“扩充法”:找着善根良心,然后让它极限发挥,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像所有宗教都有个“根本转变”的法门一样,心学是明心见性式的,顿见本体,彻悟心源,便能“大作一个人”了。
万物的本原是水
自亚里士多德的记载以后,泰勒斯被认为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人,因为他提出了世界的本原问题,从此开创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研究。亚氏在《形而上学》中说,“这一派哲学的创始人泰勒斯认为水是本原。”这种解答,可能会使初学者感到泄气,因为这似乎是过于简单的说法,但我们必须结合泰勒斯提出这个命题的背景和这个命题的内涵来理解,否则就会误解命题的意义。
我们知道,在古希腊哲学产生之前,希腊世界就广泛流传着有关世界创生的完整神话传说,宇宙最先是混沌,从混沌中分化出天空和大地,天空和大地也就是父亲和母亲,他们所生的孩子是最高的神,然后又繁衍了诸神及其后代等。这些神话传说几乎是所有文明在开端时期都会有的现象,也是人类思维在原始时期的特性。但泰勒斯提出了“万物的本原是水”则标志着人类思维开始从神话向抽象思维过渡。希腊哲学始祖泰勒斯的贡献就在于他首次打破神话的形式,用自然的原因去解释自然界的统一性,从而在哲学上提出本原的思想。
泰勒斯说“万物的本原是水”,这里的“水”,绝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水,它的内涵应该比这丰富得多。同时,泰勒斯的“水”这个概念还不具有质料与形式的明确分别的意义。此“水”所具有的这种思辨性,却并不是如同黑格尔所说的,作为一种客观性质“提高为自身反映自身的概念”以及“思辨的普遍性必然扬弃掉感觉性而使它自己成为概念”,而是上面详述的希腊神话中水神创生世界的思想赋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