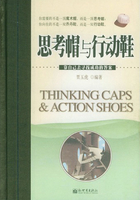黎叔是开电器行的,很多老街坊电器坏了,不想买新的或者根本没钱买,他就免费上门去帮人修。不仅上了年岁的人,年轻人对这个老街区也很有归属感,因为他们跟通宵打游戏机的小店老板混得很熟,不想因为搬走而离开他。
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故事让读者了解到,人对一片老街区会有多么浓厚的感情。当政府人员告知他们街区要被拆掉时,周绮薇站出来发声,一开始众人非常怀疑她:“你是什么人,干吗出来跟我们说这事?”直到她表明身份:“各位街坊,我就是后面那间车房老板的女儿,平时坐在门口跟大家聊天的是我爷爷,我在这里长大。”这时大家纷纷说道:“哎哟!原来是你呀,没想到你长这么大了。”突然间变得对她无比信任。从此,她成了这个反拆迁运动中,老街坊们最信任的“我们街的小女儿”。她和街坊们展开了一场“推土机前种花”的运动,抗议政府的行为。
周绮薇温柔、多情、坚定而善于倾听。她说:“还没有和街坊走在一起前,我是个没有耐性的人,区内的居民多是中年人和老人家,说话有他们的方式,共同点是开场白很长,还会把整个说话内容重复三四遍。后来我心急起来,觉得疲累,常常抱怨为什么你们不能说快一点,简洁一点。但是转念一想,政府不就是因为不愿付出时间,或先假设了街坊们什么也不懂,而拒绝找方法跟他们沟通吗?如果我也嫌弃他们,又怎样证明给政府看,推行由下而上、由居民主导的重建方案是可行的呢?”
她开始细心倾听每一个街坊的故事,并跟一些义工用图画的方法和最简单的语言,把政府那些充满术语的重建方案再次呈现出来。她收集街坊四邻的意见,向政府提出其实老百姓也想重建社区,只不过他们不想把这个地方卖给开发商,而想在盖新房的同时,继续老社区包容多元的文化。
可是,这些想法如何让政府明白呢?周绮薇想了各种办法诉诸公众,她要让全香港市民知道这个地方有些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故事。他们不要当受害者,不要当苦主,他们要快乐而骄傲地告诉大家,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比如,他们把这条街上的一家家商店用最童稚、最简洁的线条画出来,店面的样子、店里的人、平时的工作流程都画得很详细。后来他们干脆在街上摆了一个展览,用一幅幅图画向路人解释:“你看,我们不是大超市,这些都是我们一家一户自己做的小玩意儿。我们这些生计是讲技术含量,讲传承的。”其中一个人老老实实做了几十年酱油生意,不知道自己的酱油其实颇有名气。直到有一天日本的电视台专门跑来拍摄,他才晓得原来家里几十年传承下来的酱油在国际上这么有名。
到了晚上,一群老街坊在街上玩皮影戏,用民间艺术的形式告诉大家这个社区一直以来的文化故事。他们希望重建的负责人--规划局林局长--能够了解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区究竟是什么模样的,和政府规划中的社区又有何不同。周绮薇还在她爸爸的车房里摆宴席,为林局长专设了一个座位,每天八点准时等他,希望他来跟大伙吃饭,听老百姓诉说意见。几十天后,局长终于来了,可他开口的话是:“这个项目已经开始,是不能够回头的,你们必须要走。我最多只能保证,不会让以后其他重建的居民再经历你们经历过的痛苦,我会回去想办法安置你们将来的生活。”无论如何,这条让街坊们无限留恋的老街区终究要被拆掉。
这个街区还有位很有特色的老人家叫黄乃忠,他是香港硕果仅存的花牌师傅。花牌是一种典型的岭南文化,有酒楼开张这种喜庆日子,大家会摆一个很大的花牌作为庆贺。黄老爷子就在街区里做这种生意,如果要拆迁,他的独门手艺就很可能失传。他代表街区和政府打官司,最终也没有结果。终于,政府来拆迁了,当他家里那些有价值、有感情的老物件被人抬走时,突然有只蟑螂跑出来。
他竟对着大家说:“不要踩它,不要这样对这些小生命,再小都是一条生命,明天开始它就没有家了,没有家是很可怜的。”这位平时一边做买卖一边照顾街上流浪猫的老人,终于也要面临没有家的结局。
书的结尾,这片有生命力的老街区变成一片被推掉的平整土地,那些热闹繁华的景象永远留存在图画里。梁老婆婆常常回到这片空地上,想看看熟悉的老街坊,却没有一个人在。有些老伯伯、老太太在失去了心灵归属的社区后,一两年里就相继过世了。
(主讲梁文道)
《为当下怀旧》
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
叶荫聪,1970年生于澳门,于香港中文大学修习新闻学和社会学,获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博士学位。现任职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独立媒体(香港)(InMediaHK)创办人之一。
对殖民地最重要的不是祖国或家乡,而是那个被剥夺的创伤。所有被殖民者身份认同的第一个基础是被创伤过。
这几年香港非常流行一个词--“文化保育”,保的并不只是一般的古建筑,有历史价值的街道、地标,甚至整个社区都在保存之列。这场运动发生的背景如何?为香港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和思考?《为当下怀旧--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这本书给出了详细的介绍。
作者叶荫聪是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学系讲师。身为一个文化研究者,他会去质疑一切现成的文化价值,比如身份认同,不光种族与国族的身份要被质疑,本土身份也要被拆解。
什么意思呢?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老说自己是“炎黄子孙”,这几年还每年去祭黄帝。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所谓“炎黄子孙”这个说法只有一百多年历史而已。这是一个被发明的传统,是现代中国人返回来追认自己的源头。从这个角度看,任何我们以为坚固的、牢不可破的、天然而成的,包括我们是炎黄子孙这一说法都是后天发明的。
但这能不能叫虚构呢?很难说。不过,作为近年来参与香港各种各样“文化保育”运动的局内人,叶荫聪又不得不倾向于承认某种历史和文化价值。比如之前闹得很厉害的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3],你说它有价值,那个价值是什么?你要保留下来的又是什么?你不承认这个价值,怎么能够付出?又怎么能够去发起一场运动呢?
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叶荫聪引用了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4]的说法。他说,一个固定的、历史传承下来的传统并不一定构成我们的身份基础,我可以现在宣誓一个未来的身份,然后通过某种运动、某种努力、某种建构,把我变成我愿意成为的那种人。
香港的身份认同是殖民地,对殖民地最重要的不是祖国或家乡,而是那个被剥夺的创伤。换句话说,殖民体制是一个创伤的体制,所有被殖民者身份认同的第一个基础是一群被创伤过的人。
近年来香港一连串“文化保育”运动声势浩大,很多外行人或者一些被我称为“伪评论家”常常说,你们只不过是在回忆英国殖民年代,什么天星码头、皇后码头都是殖民象征,保留它,表示你们这帮年轻人不认同祖国,而要认同一个英国殖民年代的象征建筑物。叶荫聪在这本书里提出,当年那个码头是香港民间反抗运动发生的场所,参加保育运动的年轻人并不是要追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而是要追认被社会主流压抑了的、挤到边角去的反抗者身份;码头的空间记忆由殖民种族的历史转移到一个公共空间,成为香港平民百姓的本土印记;他们关心的不是所谓的皇室故事,而是老百姓的故事;他们重新为这个地方发明了一种意义,并认同这种意义,然后自己建构出一套身份,也就是被压迫过、伤害过的被殖民者的记忆。
当年这场运动闹得很大,连“发哥”都去支持了,最后还是失败了,被政府铲掉了。香港很多老街区这几年都出现过这种运动,最后也都失败了。失败的理由之一是香港这些老区的重建其实跟内地的拆迁差不多,也许文明一点,但也不算文明太多。这里面的利益当然是“卖地”,政府收回老区就有了土地,有了土地就能拿去卖。卖了之后干吗呢?增加收入。谁能赚着钱呢?当然是周边的裙带关系,比如说地产商,是不是?
(主讲梁文道)
《屋不是家·混声合唱》
徒留寂寞
适然,原名骆适然,香港作家。中学毕业后就与文友集资创办《大拇指》周报,同时担任《香港影画》及《南国电影》记者。1976年夏随家人移民美国,一直做到跨国银行副总裁。1990年返港,任记者、编辑、翻译、妇女团体总干事、公益组织义工等。出版有散文小说合集《声音》。
所谓的家并不是那间屋,每一个人都在这样的城市里,享受着必然的寂寥、空洞,尽管光线明亮。
香港有不少优秀作家,往往一停笔就是很多年,又或者产量奇低,一写就是近十年,以至于有时候市面上出现某些新作品,读者还以为是冒出新人来,没想到已经是写作数十载的老前辈了。比如这本《屋不是家·混声合唱》的作者适然。适然这部短篇小说集写法很特别,会把很多离奇的情节写淡,又把一些很淡的事情大大书写一番。比如开头这篇《花好月圆》,主人公和女朋友闹分手,辞职来到一个新发展的市镇打算重新开始生活。在日复一日、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他发现了一个新亮点--住在对面大楼的女子。他几乎像个窥视狂一样天天跟踪这个女的,看着她,想着她,甚至跟着她去买她喜欢的花,然后把花带回自己家。
但他最终还是难逃从前的情感纠葛,和原来分了手的女朋友复合,结婚生子。他回想起那段逃离经历,那段若有似无的感情,想起某天捡到女孩的钱包,把钱包放回她家门口的邮箱上--两人最亲密的接触也不过如此。他心里始终藏着这个凄凉的秘密,而人间草木,一切已不再一样。他说:“我无情地学习忘记,我们在这个城市众生喧哗中卸下了一面国旗。”那年,正好是一九九七。
他时常想到那个女子,觉得她皎洁如月,然后也学着她,开始在家里插花。当他和妻儿一起走在中秋节回家的路上,他想:“再没有其他事情发生,再没有。半生已经过去,灯好月圆,花常开。我紧紧搂着的小小身体,这是我的骨肉,我们的。而你有一个花季,在某年,朝向小耳朵呵着气问,你好吗?心神晃晃悠悠漂游到老远,不知道诘问的是谁。女儿咕咕笑,别过小面孔,向母亲叨叨诉说幼儿班上一天里的许多事。花有时,月有时,万物有时,你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