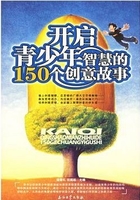还没到周五,玛莉拉就听说了那顶花环帽子的事儿,她从林德太太家回来就问安妮。
“安妮,雷切尔太太说你上个星期天去教堂的时候戴了一头可笑的玫瑰和毛茛,到底什么弄得你这么快活?你看上去一定很优雅!”
“噢,我知道粉红和黄色对我不合适。”安妮说。
“胡说八道!我指的是把花弄在帽子上,不管什么颜色,这太可笑了!你这个让人烦恼的孩子!”
“我不明白为什么把花别在帽子上就比别在衣服上更可笑些,”安妮反驳说,“很多女孩子把花别在衣服上。这有区别吗?”
玛莉拉没有被安妮从可靠的具体事例拉到模棱两可的理论道路上去,“别用这种话来回答我的问题,安妮!你这么做太傻了。下次别让我逮着你这种把戏。林德太太说她要这样戴着花进来的话,会恨不得缩到地板下面去!她没办法到你面前去叫你摘下来,人们都在议论这件可怕的事情呢。他们肯定会说我除了让你就这样出去,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对不起,”安妮的眼泪在眼里打转,“我不知道您会介意的,毛茛和玫瑰那么漂亮,我以为戴在帽子上很好看呢。许多小姑娘的帽子上都是假花,我怕这件事对您来说是个可怕的折磨呢。或许,您还是把我送回孤儿院吧。这样我会受不了的,太可怕了,或者我会得肺病,我很瘦,您也知道的,但是这也比折磨您强多了呀。”
“胡扯。”玛莉拉说,她也很焦急自己把这孩子逼哭了,“我没想把你送回孤儿院去,我保证。我只是希望你像别的小姑娘一样,甭把自己弄得可笑了。别哭了,我有事要告诉你呢。今天下午戴安娜要回家了,我看看能不能到巴里太太那儿借条裙子做样子,你要是愿意就跟我一块儿去吧,和戴安娜熟悉熟悉。”
安妮跳了起来,手像钩子一样紧紧握着,眼泪还在脸颊上闪烁,卷着边的毛巾滑到了地板上,“噢,玛莉拉,我害怕了——现在我真的怕了。要是她不喜欢我怎么办!那会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望了!”
“好啦,别激动,我可不希望你用这么长的词。小孩子讲这种话听起来太滑稽了。我想戴安娜会喜欢你的,你倒是得和她妈妈小心相处,要是她不喜欢你,戴安娜再喜欢你也没用。要是她听说你对林德太太发的脾气,还有帽子上戴着毛茛上教堂,我可真不知道她怎么想。你得礼貌点儿,行为得当些,不要发表你那些令人吃惊的言论。发发慈悲吧,这孩子不是真的在发抖吧!”
安妮的确在发抖。她的脸苍白紧张。
“噢,玛莉拉,要是您要去见一个您希望能成为知己的小姑娘,她妈妈可能会不喜欢您,您也会激动的。”安妮一边说,一边赶紧去拿帽子。
她们路过小溪,穿过小路和冷杉林到了果园坡。巴里太太听见玛莉拉的敲门声来到厨房门口,她高高的,长着一双黑眼睛,一头黑发,嘴角坚毅,外面人都说她对孩子相当严厉。
“还好吧,玛莉拉?”她真诚地说,“进来吧,这就是你领养的小姑娘了?”
“对,她就是安妮·雪莉。”玛莉拉说。
“加个尾音。”安妮气喘吁吁地说,她激动得浑身发抖,但还是决心在这么重要的问题上不能存在误解。
巴里太太没听见,或者是没有领会,只是握了握手,和气地说:“你怎么样?”
“身体很好,虽然精神有些混乱。谢谢您,姆妈。”安妮严肃地说,然后凑到玛莉拉的耳边悄悄问,“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吧,玛莉拉?”
戴安娜坐在沙发上看书,客人们进来时书从她手里掉了下来,她真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和她妈妈一样的黑眼睛、黑头发,如玫瑰花般的双颊,她喜洋洋的脸色是出自于爸爸的遗传。
“这是我的小女儿,戴安娜。”巴里太太说,“戴安娜,带安妮去花园里转转,看看花,这比让书损伤你的眼睛强多了,她看书时间太长了——”这句话是小姑娘们出去时对玛莉拉说的,“我劝不动她,她爸爸老护着她。她老是看书,我真高兴她能有个玩伴,这样她就会常常出门玩儿了。”
在花园里,柔美的落日的光芒在阴暗的杉树林中流动,直流到西面,安妮和戴安娜就站在那儿,面对着一丛绚丽的卷丹羞怯地相互打量。
巴里花园茫茫一片美丽的花儿在任何时候都注定会点亮安妮的喜悦,它被大片的老柳树、高高的杉树围成一圈,树底下生长着天性喜阴的茂盛花朵,整齐的直角小径用干净蛤壳镶上了边,如同被分成了两条潮湿的红色缎带,中间这些经年的花儿疯狂蔓延,流血一般的玫瑰,灿烂的深红牡丹,芬芳的白色水仙花,多刺却甘美的苏格兰玫瑰,粉红、蓝、白色的耧斗菜,丁香色的肥皂草,一丛丛的菁蒿,薄荷,紫色油灰根,黄水仙,大片大片的草木樨喷出如白雾般精致、芬芳的羽毛般柔软的花朵,洁净的白色麝香带着猩红的光彩喷射出一支支炽热的长矛。花园里阳光游移着、逗留着,蜜蜂嗡嗡叫着,风在花园里穿行,发出咕噜咕噜和沙沙的响声。
“戴安娜,”最后还是安妮开口了,手紧紧握着,声音低得像耳语,“你能不能喜欢我,做我的知己密友呢?”
戴安娜笑了,她开口说话之前总是笑。
“哦,我想可以吧,”她爽快地说,“我真高兴你住在绿山墙呢,有人玩儿太开心啦,这附近没有女孩子,我也没有这么大的姐妹。”
“你能发誓永远做我的朋友吗?”安妮急切地问。
戴安娜的表情像是受惊了,“发誓太可怕啦,这不道德呢。”戴安娜拒绝了。
“噢,不是那种誓言,有两种发誓呢,你知道。”
“我可只听说过一种。”戴安娜怀疑地说。
“真的有两种,噢,根本就没有不道德,只是庄严的宣誓。”
“哦,那我就不介意了,”戴安娜松了口气,同意了,“怎么做呢?”
“我们得握着手,然后,”安妮庄严地说,“应该在流水上,噢,我们只要想象这小路就是流水,我先来说誓约吧,我庄严地发誓,我将会对我的知己——戴安娜·巴里忠诚守信,我们的誓言长久如日月。现在你说一遍吧,加上我的名字。”
戴安娜笑着重复了一遍“誓约”,然后说,“你真奇怪,安妮,我以前就听说过你很怪,但我相信我会喜欢你的。”
玛莉拉和安妮回家时,戴安娜一直陪她们走到独木桥边,两个小姑娘手挽着手,在小溪边她们不断地发誓说明天下午还要在一块儿玩。
“好了,你觉得跟戴安娜志趣相投吗?”穿行在绿山墙的花园里,玛莉拉问。
“哦,是的,”安妮叹息一声,幸福得一点儿也没意识到玛莉拉的挖苦,“哦,玛莉拉,这会儿,我是爱德华王子岛上最幸福的小姑娘了。我保证今天晚上的祷告是真心真意的,明天戴安娜和我会在威廉姆·贝尔先生的白桦林边建一座游戏房。我能拿一些木棚里的碎瓷器吗?戴安娜2月份要过生日,我的生日在3月,您不觉得这太巧了吗?戴安娜要借给我书看呢,她说那书特别好看,非常激动人心。她要带我去树林里的一个地方,那儿有稻米百合。您觉得戴安娜长着双充满深情的眼睛吗?我真希望自己的眼睛也充满深情啊。戴安娜要教我唱首歌,叫《黑尔兹谷的奈莉》。她答应给我一张图片放在房间里,而且是一张非常漂亮的图片呢。她这么说的,一位漂亮的女士,穿着淡蓝色的丝绸衣服,是一个缝纫机代理商送给她的,我想给戴安娜些东西。我比戴安娜高一英寸,但她比我丰满些,她说她宁可瘦一点,因为那样优雅些,我想她只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我们哪天要到海滨去捡贝壳。我们一致决定叫独木桥下面的泉水‘森林女神泡泡’。这名字是不是够精致?我看过一个故事,那里面的泉水就叫这名字。森林女神是长大的仙女,我这么猜。”
“够了,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你别到死都讲戴安娜,”玛莉拉说,“记住把这一条列进你的计划:你不能把所有,甚至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玩儿。你有功课要做,先把功课做完再玩儿。”
安妮的杯中已经溢满了欢乐,用马修的话,是已经泛滥了。他刚刚从卡莫迪的商店回来,羞怯地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包递给安妮,同时恳切地望着玛莉拉。
“我听你说你喜欢巧克力糖,给你买了点儿。”他说。
“啊哈,”玛莉拉“嗤”了一声,“这会把她的牙和胃口都搞坏的,喏,孩子,别看上去这么凄惨了,你能吃,既然马修都已经买回来了,他应该给你买些薄荷的,那更健康些。别一次全都吃掉,把自己弄得反胃。”
“不,不会的,”安妮急切地回答说,“我今天晚上只吃一颗,玛莉拉,我能给戴安娜一半吗?要是我给她一些,那会比我自己吃还甜一倍呢,要是我能给她点什么,就真的是太开心了!”
“这孩子,”安妮回屋去时玛莉拉说,“不小气。我很高兴,小孩子的缺点里我最讨厌小气了。天哪,她才来了三个星期,我都觉得她是一直住在这儿的了,都不敢想这地方要没有她会是什么样子了。现在,马修,甭看我,我告诉你,这副样子对女人来说已经够不怎么样了,男人就更让人无法容忍了。我可愿意爽快地承认,我很高兴自己同意把这孩子留下来,我是越来越喜欢她了,但你可别老是反复提这件事来故意气我,马修·卡斯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