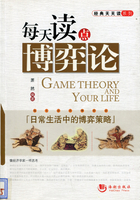“嗯,喜欢它们吗?”玛莉拉问。
安妮站在山形墙的房间里,严肃地注视着铺在床上的三件新衣裳,一件是讨厌的花格棉布料子,是玛莉拉这个夏天受了诱惑从小贩手里买到的,因为它看上去很耐穿;另一件是黑白相间的棉缎料子,冬天时她从廉价货柜台挑出来的;还有一件是难看的蓝色印花面料,僵硬死板,是她上个星期在卡莫迪的商店买的。
她是自己做的这些衣服,所以看上去都一个样子,式样简单的裙子腰身紧紧的,袖子和腰差不多朴素,裙子却和袖子差不多紧。
“我会想象自己喜欢它们的。”安妮冷静地说。
“不用你想象了,”玛莉拉不高兴了,“我知道你不喜欢!它们怎么啦?它们不是很整齐干净而且是新的吗?”
“是的。”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
“它们,不太漂亮。”安妮说。
“漂亮!”玛莉拉的鼻子吸了口气,“我可没特意为你费劲做什么漂亮衣服!我不会纵容虚荣的,安妮!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这些衣服很好,很朴素,耐用。没有华丽的饰边,这些就是你今年夏天穿的衣服了。这件棕色条纹的,还有蓝色印花的你上学时候穿。棉缎衣服上教堂和周日学校时穿。我希望你能干净整齐点,别把它们扯坏了。我觉得你穿过那些紧巴巴的棉绒衣服以后,应该对大部分东西怀着感激的心呢!”
“哦,我是感激涕零,”安妮宣称,“但要是,要是您把其中一件的袖子做宽松些,我会更感激的,现在流行灯笼袖。它会让我兴奋得颤抖呢,玛莉拉,只是穿一件袖子打褶的衣服而已。”
“得了,你省掉你的颤抖吧,我没有多余的布料浪费在灯笼袖子上,我觉得看上去太可笑了,我倒是更喜欢这种简单理性的式样。”
“但当所有人都很可笑时,我倒宁愿可笑,也不愿意就我一个人简单理性。”安妮忧伤地坚持说。
“自信一点儿吧!好了,小心地把衣服挂在衣橱里,然后坐下来学周日学校的课程。我从贝尔先生那里拿了本季刊,明天你就可以去周日学校了。”玛莉拉恼怒地消失在楼梯下。
安妮握着双手盯着衣服看。
“我真希望有件白色的衣服,灯笼袖的。”她一脸忧愁,“我做过祷告,但没指望能得到它。我不认为上帝有时间来操心一个小孤女的衣裳,我知道我只能指望玛莉拉,天哪,幸亏我能想象自己有一件雪白的薄棉布衣裳,上面缀着可爱的花边,还有三褶的袖口。”
第二天一大早,严重的头痛让玛莉拉没法陪安妮去周日学校了。
“你得下去找林德太太,安妮。”她说,“她知道你要上学了,注意要行为得当,待着听布道,然后让林德太太告诉你我们的座位在哪儿,喏,这是捐献的一分钱,不要盯着别人,也别四处乱跑。回家以后把上课的内容讲给我听。”
安妮出发了,身上穿着黑白棉缎衫,端庄得体,长度适中,不能指责它过瘦,但它人为强调了她瘦小的骨骼的每个边边角角。帽子是那种小小的扁平的帽子,闪着光泽,非常简单,这当然再次让安妮失望了,她让自己假想着它的几种式样,缎带,花边。无论如何,安妮到山路之前就已经有花儿戴了,她到半山腰时,就看见了被狂风吹乱的金色毛茛一片狼藉,还有漂亮的野玫瑰。安妮大方轻快地给她的帽子镶了一道沉重的花环,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安妮是满意了,她轻快地沿着路走下去,骄傲地在红头发上顶着粉红和金黄的装饰品。
她到林德太太家时才发现,林德太太已经走了。没什么可沮丧的,安妮一个人向教堂走去。在门廊前,她看见有一群小姑娘,或多或少都用了华丽的白色、蓝色、粉红色装饰自己,而且全部睁着好奇的眼睛注视着她们中间的这个陌生人,还有她头上这种非凡的装饰品。安维利的小姑娘们都已经听说了安妮的奇怪故事,林德太太说她的脾气很坏,绿山墙雇用的男孩杰里·布托说她像个疯子,总是在和自己,或者和花花草草说话。她们瞅着她,在书本的遮掩下低声讨论,没有人友好地接近她。过了一会儿,开始的练习结束后,安妮才发现自己上的是罗杰逊小姐的课。
罗杰逊小姐已经人到中年了,在周日学校任教也已经二十多年了。她的教学方法就是提问那些书本上已经印好的问题,苛刻地用眼角盯着那些她选中回答问题的小姑娘。她老是盯着安妮看,安妮呢,感谢玛莉拉的演练吧,回答得非常迅速,除非问的是她是否透彻理解了问题或者答案。
她不喜欢罗杰逊小姐,而且,她非常伤感,班里的每个小姑娘都穿着灯笼袖的衣裳,安妮真觉得没有灯笼袖活着都没有意思了。
“你喜欢周日学校吗?”玛莉拉见安妮回来了就问道,她的花环已经凋零了,安妮把它扔在了小径上,玛莉拉暂时不知道。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太讨厌了。”
“安妮·雪莉!”玛莉拉指责的语气。
安妮长叹一口气,坐在摇杆上,吻了吻“漂亮爱人”的叶子,向盛开的紫红色樱花挥了挥手。
“我不在时,它们一定很孤独。”她说,“现在说说周日学校吧。我按你说的,表现得很好。林德太太已经走了,我就自己去了。和很多小姑娘一起进了教堂,练习课开始我就坐在了靠窗户的角落里。贝尔先生的祷告词长得可怕,要不是坐在窗口,他还没讲完我就累死了。不过,窗口的位子正好看见阳光水湖,我就坐在那儿想象各种漂亮的东西。”
“你根本就不应该做这种事,你应该听贝尔先生的讲话。”
“他又不是和我说话,”安妮反对,“他在跟上帝讲话呢,而且他自己好像也没什么兴趣。我猜他觉得上帝太遥远了。湖边有一长排白桦树,阳光穿过白桦树洒落在湖面上,往下,再往下,渗到湖水里。玛莉拉,就像一场美梦!美得让我颤抖,我说了两到三次感谢上帝!”
“我希望你没大声叫。”玛莉拉忧心忡忡地说。
“没有,在心里说的。好吧,贝尔先生终于说完了,他们叫我跟罗杰逊小姐的班到教室里去,还有九个女孩子。她们全有灯笼袖的衣裳。我也假想自己穿着灯笼袖的衣裳,但是想不出来。为什么想不出来呢?这跟我在东山墙想象她们都穿灯笼袖衣服一样容易呀,但真在她们中间,而且她们都穿着灯笼袖衣服时就太困难了。”
“在周日学校里想灯笼袖是不应该的,你应该仔细听课,明白吗?”
“好啦,我已经回答了很多问题了,罗杰逊小姐问了这么多问题,我可不认为她问这些问题很公平。我也有很多问题想问她呢,不过我没问,我觉得她和我并不会志趣相投的。后来,其他女孩子背了一段课文,她问我明白不明白,我告诉她我不明白,但是我会背《主人坟前的狗》,她要是愿意听的话,是《第三位忠实读者》里的,并不是那种真正富有宗教意义的诗,这诗很悲伤很忧郁。她说不用了,叫我准备下节课要学的第十九节。后来我在教堂看过了,很不错,有两行还能让我颤抖呢。
“可怕的日子里,米甸被屠杀的队伍猝然倒地。
“我可不知道那一队人,也不知道米甸,但它听起来像悲剧,我可等不及到下个星期天才背,这个星期我就要背。下课后我问罗杰逊小姐,因为林德太太太远了,没办法告诉我哪儿是你们的位子。我安静地坐在那儿,课文是第三章的启示录,第二、三节,很长。要是我是牧师,我就只选那些简短爽快的,那布道也太长了。我猜牧师是想和课文相配呢,我觉得他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他的问题没有一丁点儿想象力,我没怎么听他的。我就任自己的想法跑啊跑啊,我在想着奇迹呢。”
玛莉拉无助了,她知道应该严厉地批评安妮,可安妮说的一部分是不容否认的现实,这妨碍了她的批评,特别是牧师的布道和贝尔先生的祷告词,几年来她自己也觉得冗长不堪,只是从来没说出来过罢了。她好像觉得这些隐秘讳言的批评念头变得清晰可见,只不过借着这个被人忽略的小人儿的口说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