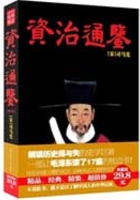这不是什么故事,却是一份真实的情感;虽然我不曾拥有过这份幸福,但我试图去吮吸,去品尝……
—题记
母亲四十五岁,生下我这个压尾崽。母亲没有奶。我很瘦,像根火柴棍。哭声比不上毛茸茸的猫叫。父亲只知道下地干活。母亲没有办法,月子里搂着我长泣短哭。
嫂子抱走了皮包骨头的我。把我同侄子放在一个摇窝里。侄子大我一个多月。嫂子的奶很肥很大。一日三餐。一个奶奶一个。我很乖。一天一个样。长得比小狗儿还欢。
我和侄子都会走路了。
暮晚时分,我和侄子便早早地吃力地抬着一方小凳,放在堂屋前的阶沿上。然后,坐在庭院前面的那棵大柳树下,静静地远望着那无垠的原野和那忙碌的人群,搜寻着嫂子的形象,企盼着嫂子归来。劳累了一天,嫂子终于回屋了。我和侄子雀跃起来,满身泥垢,摇摇晃晃扑向嫂子。
嫂子坐上小凳,一手揽一个,撩起肥大的衣襟,把我和侄子拥入她温馨、丰隆、厚实的怀抱。我们青嫩的小手轻轻按压在嫂子的奶上,就像是捧着一个晶莹透亮的琼壶,密咂密咂吮吸着甘甜的汁液。这时的嫂子,肥大的手掌轻轻拍打着我们的脊背,脸上绽出一朵醉人的山茶花。
嫂子的奶壶有吮不完的奶汁。
三岁多,嫂子给我们断了奶。我天天哭,时时闹,吵着要拱到嫂子的怀里。看到我哭,嫂子总是怔怔地望着我发呆。实在拗不过,她才卷起衣角,让我吮上几口,然后便匆匆离去……
这一切,都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后来,我长大了,长得人高马大,五壮十粗。
后来,我读大学了。
后来,我参加工作了。
后来,我回家去,嫂子看见我,便避着躲闪过去。即使我总是追到锅头灶边想跟她唠上几句,她也会低着头,红着脸,借故走开的。
后来我要结婚了。除嫂子一人以外,家人都来了。尽管在婚前,我和妻特意去请过她,尽管“大”侄子代表我劝过她,尽管老母亲动员过她,尽管……可嫂子还是没有来。我很怅然,也很愧疚,心里总像失落了什么。喝酒的时候,老母亲提议,在上席给嫂子留个位子,尽管那是圆桌……
199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