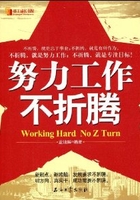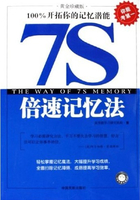父亲下决心给我做美容手术了。
在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里,我作为一位特殊病人进入该医院牙科。此前,我一直是忐忑不安的,我不敢想象,医生如何在我的嘴里动刀。也不知我来医院美容的消息是如何走漏的,一帮记者也闻讯赶来,他们似乎对我来做美容很感兴趣。
医院先引导我拍了口腔片子,之后有人带我去见主治大夫。这是一个年轻的女军医,干净整洁的白大褂下面,是一套笔挺的制式军服。她的身上有一种淡淡的香水味道,我说不清具体是什么香味,但我心下很乐意她作为我的主治大夫。
很快,治疗方案定下来了。女医生对我父亲说,我最里面的一个大牙因为咬噬骨头及硬物,已经断裂成两半了,必须拔掉,待三个月后可以镶义齿。另外,前面四颗爆出嘴唇的虎牙得打磨,或者连根拔掉,同那颗大牙一样装义齿。我想起了自己在山里时,那些坚硬的核桃,硬生生被我咬开的往事。
考虑到这样“工程量”太复杂,父亲建议先拔掉最里面的大牙。事实上这颗大牙已经困扰了我几年,如果不是重新和家人团聚,我或许还得继续忍受牙痛的痛苦。
医生决定马上给我拔牙。呵呵,这回可是狼口拔牙了。这样想着,我躺倒在长长的躺椅上,等候医生的发落。父亲在一旁焦急地等待着,女医生却说,“请家属都出去等待。”
父亲怏怏地出去,坐在楼道的长条椅上。刚点着一根烟,却被另外一名护士嚷着灭掉。我瞥了眼父亲,“真是,也不看这啥地方嘛?抽什么烟!”
重新躺下。女医生已经全副武装,她戴了手套,手持一把明晃晃的钳子在我松动的牙齿上敲打着。一股钻心的疼立即从牙根直至全身,我有些发抖。那女医生却说,“有那么痛吗?你的事迹我们都从报纸上看到了,你很棒的。这点痛算什么?!”是的,这点痛算什么吗?我心里想着。
女医生的助手给我注射麻醉药,这是一根稍弯些的针头,在我口腔接近那颗大牙的地方扎了进去,大概数秒钟的功夫,助手将针头拔了出来。
我觉得口腔内壁稍微有些疼,却马上像肿了一般,变得硬硬的,渐渐无了知觉,抬头望望手术椅上方的灯泡,正直直地照着我的脸。我的脸好像已不是我的脸了,我感觉越来越紧绷,药效好像还再持续,我的喉咙也不是我的了,有一口唾沫卡在其中,想咯出来,喉咙却不听指挥……
女医生走了过来,“张开嘴!”
我张大了嘴。她用钳子伸进去,在里面拼命摇着那颗残牙,我已不觉得疼了。
她使劲地拔,却钳不住。牙冠已经被我咬残了,只剩下短短的一截,她肯定不好下手的。看她怎么拔我的狼牙?呵呵。
没有办法,她喊来助手,令助手将一根凿子伸进去,顶到残牙上。之后,她托住我的下巴,固定住。
“可能会有点疼。”她柔柔地说。
我点点头,用眼睛的余光望着她。她的睫毛长极了,尽管口罩遮着的脸只能看到她的眼睛,但我能看出这是一双极其美丽的眼睛。这样看着,我也不觉得疼了。
她的助手一手执凿子,另一手执一小榔头,猛击凿柄。凿子像凿石头一样在我牙缝里“咣咣”得脆响着,女医生则拿镊子夹着棉纱给我止血。我旁边的小磁盘里一会就扔满了带血的纱布,我只觉得头皮一阵发木,喉咙则发痒发干。
我感觉他们不是在拔牙,反倒好像在挖一颗极其难挖的树根,我的头颅在榔头的震荡下不停地晃动着。只觉得整个脑子都在嗡嗡作响,头好像也不是我的了,任人摆布着……在这个过程中,女医生的手一直托着我的下巴,大概是手臂累了,她又换了另一只手继续托。
大约十分钟的样子吧,我听见瓷盘里梆梆两声脆响,是我的牙根被拔出来了。我松了一口气,她让我含一口水,迅速地吐出来。我觉得嗓子眼像被堵住了,吐不出来水,也咳不出痰来。她迅速地叠好一块止血纱布,让我咬住,并交待半小时之内不能松开,也不能吐唾沫。
医生又叫我父亲进来,大概交待了一下,让再过一个礼拜过来处理另外几颗龅牙。我忍痛出了诊室,等待在楼道里的几个记者又是摄像又是拍照,父亲挡着镜头说,“别拍,别拍,人不能说话……”
尽管如此,父亲还是碰见了几个他熟悉的记者,他们都是多次采访过我的,父亲实在拗不过,就地接受了他们的采访。大致说了几句,匆匆陪我下楼,坐车回家。
整个一个暑假,我几乎几天就跑一次医院。而电视和报纸上也就几乎天天播发着关于我的新闻。
“我儿子将不再是狼人了,我想让他过正常人的生活……”
看着电视里父亲说着的那番话,我有些想笑。
由于不能咀嚼,我几乎天天吃着流食,母亲让厨师蒸了蛋花,给我加强营养……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变得非常幸福,反倒不适应了。想想自己在山里时,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想办法,我担心长期这样养尊处优,我会丧失了狼人的本领,变得和平常人一样。
处理好几颗牙。我的嘴唇终于能闭合了,却没了呲牙时的凶神恶煞。接下来,父亲又考虑为我做隆鼻手术。
我在狼洞生活的十几年里,一直将头埋在地沟里,鼻子扁平,没有美感,而且里面还形成了息肉,必须手术解决。
像上次拔牙一样,也须麻醉。但这次麻醉却不注射,医生用药棉蘸上麻醉剂,塞入我的鼻腔,我的鼻子痒极了,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将药棉全震出来了。没有办法,医生又重新塞麻醉药棉。这回成功了,却有一些麻醉药流入喉咙。我只觉得喉咙肿胀,无法发声,无法咳痰,痛苦极了。
遗憾的是,这回的女医生可没上次拔牙的女医生温柔,她拿一根长长地激光枪,深入我的鼻腔,一阵点击般的电流瞬间向我袭来,我只觉得头被高压击偏,一阵抽搐。我一声大吼,女医生吓得跑了出来。我父亲忙不迭地解释,“没事,他就是那样的,你们继续,你们继续。”
这次,医生特赦我父亲可以进入手术室,扶住我的头颅,重新给我做手术。我恨极了,恨父亲非得给我做美容隆鼻手术,否则我也不会忍受这样的痛苦……
隆鼻手术很成功,加上上次口腔的美容手术,我的脸已经变成一张英俊潇洒的脸庞了。我照着镜子,望着那张熟悉而又陌生的脸庞,我想,邹怀星,你还是那个狼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