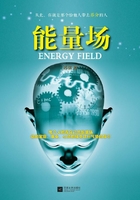然而终究没有不透风的墙,苏雪林入教的事情很快还是在她求学的中法学院和中国留学生中传开了,并同时遭到了巨大非议,甚至有的人对此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慨:有人指责她这是对“五四”精神的背叛;有人指责她是对祖国的背叛,意欲做帝国主义的帮凶;有人说她是为了骗钱—那个拉她入教的神父答应,只要她入教,每月就给她数千法郎。为此有人诅咒她,有人仇恨她,更有甚者扬言要杀了她,连平素与她交好的同学和朋友也对她多表示不解。一时间里她不但成了孤家寡人,而且几乎成了众矢之的、千夫所指。这让她倍感痛苦,并一时无法摆脱;同时,她更怕发生在这儿对她的非议传到国内,于是她决定中断学业,从这儿抽身,提前回国。
1925年6月,苏雪林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养育她长大的太平岭下村,并于8月在苏家老屋里与张宝龄举行了一个中西合璧的新式婚礼。
当苏雪林与张宝龄双双向卧病在床的母亲跪拜时,这位在大家庭里与苏雪林几乎相依为命,并在许多关键时刻给过年幼的苏雪林许多力所能及的保护的女人,竟热泪夺眶而出,她的泪水除了喜悦还有欣慰,因为她看到眼前的这个新女婿,虽然是一位洋博士,但似乎并未脱掉身上的质朴与本分。苏雪林也流下了眼泪,但她的眼泪中却有着太复杂的内容。多年后她在自己的自传体著作《荆心》中对于当时的心情有过回忆,她觉得自己此时终于满足了母亲的一个心愿,而她自己则如那走向圣坛的基督,头上的花冠竟是用荆棘编成。
然而,这应该算是一件幸事吧,毕竟,苏雪林这条人生的小船已在人世间漂泊了太远太远、太久太久了,就此似乎可驶进了一个宁静的港湾了。
四
苏州葑门12号是一座初看上去很普通的江南民居,但细一看又会发现它很不普通,因这它外形酷似一条搁浅在那儿的船。
苏雪林的婚姻,正如这条船一般,被永远搁浅在了这儿。
这座船屋是张宝龄亲自设计并建造的。他之所以设计成这样,是因为他虽说在江南船政局造船厂任工程师,但是真正坐船出游的机会却很少,他把自己的住房设计成一条船,既是对这一遗憾的一种慰藉,同时也借以表明自己一种人生的愿望。张宝龄考虑这些时并没与苏雪林商量,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因为在他看来,这是根本用不着与她商量的事情。虽然他曾留学美国多年,但是由于家庭出身和本身性格的关系,他并没有因此而学得一点西方绅士风度,甚至连男女平等、夫妻互敬等“五四”时期普遍提倡的思想在他身上也很少。他是个生性沉静而理性的人,平时待人接物总是冷冰冰的,这与苏雪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且令苏雪林难以忍受的是他处处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大男子主义,对此由于苏雪林多有思想准备,所以婚后凭着忍耐总算没与之发生太多明显冲突。
他们结婚前,张宝龄就是上海造船厂的工程师,收入自然颇丰。后来苏雪林从老家到上海后,只在张家闲居了很短的时间便应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之聘赴该校任教,每月大洋100元,同时又在东吴大学兼课,每月大洋50元,这样的收入也算不错。她结婚后不久,母亲便去世了,这让苏雪林感觉多有愧疚,因此她自然而然想通过多给弟妹们一些经济上的接济来求得心中的安慰。但是没想到这却令张宝龄不能接受,为此常常发生争执。不仅如此,他还要求苏雪林将自己的收入都交他管理。可这又是为苏雪林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在她想来道理很简单:当时女人多数一旦嫁人,多有丈夫养活,我不但不要你养活,而且还能自己挣钱,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你凭什么管我!
就是为类似这样的家庭琐事,苏雪林的新婚生活并不愉快。她曾天真地想过:或许这都是因为两人相处时间少、沟通少所造成的;或许若能像多数夫妻一样朝夕相守,就会有所改观的吧?
正好有一个机会,东吴大学需要一个工程方面的教师,张宝龄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学的正是工程,她与校方一说,校方欣然表示愿意聘他。张宝龄倒也爽快地接受了东大的聘书,不久即辞了造船厂工程师而来苏州就东大教职。
来到苏州工作后,他们住在由学校代租的一座房子里,此时的张宝龄并没想到要自己盖房,倒是他一年后辞了东大教职回到上海后,反而想起来要在苏州盖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那是他回到上海后突然病了初愈之后,或许是他因病而有所感悟到要好好享受生活,或许是正好父亲分给他一笔财产手中有钱得找个用处,总之他病中就托东大的原同事帮着买了一块地皮—葑门12号。那本是一家酒厂,因为酒厂拆迁,便将地皮与厂房一起出售。张宝龄便买了下来,将原来厂房拆了,盖起了一座船屋。
尽管张宝龄在做这一切时,始终都没与苏雪林商量过,但是眼看着这么一座别致的船屋出现在面前时,她还是为此感到十分欣慰。一是她本也是个生性浪漫的人,这样别致的设计无意中倒很是中了她的下怀;再则,她很希望这条“船”能从此成为他们夫妻躲避人生风雨的诺亚方舟。
谁知这一切似乎都只是苏雪林的一厢情愿。
其实在船屋构建之时,对于苏雪林来说,一场注定将要来临的人生的风雨就来了。那一天,景海女师的校长不知从哪儿得知她是耶稣的信徒,兴致勃勃地邀请她一同去教堂做礼拜。而她却实话实说:“我信的是天主教,与你们信的基督教是有新旧之分的,一同做礼拜不合适吧?”没想到此言使校长的脸色一下由晴天突然转阴。他鼻子里“哼”了一声转身走了。在这所由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里,从此以后她无异于成了一名异教徒。且事情至此还远没有结束。不久,学校里便开始风传她当年从法国中断学业回国的种种谣言,以及她当年在法国加入天主教而引起的种种传闻,也不知怎么也如影随形地跟到了这里,且被添油加醋地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她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在法国时的尴尬处境中:孤立、无助、痛苦,而又无辜、无奈、无望。那一次她可以逃回国内,可这一次她往那儿逃呢?自然只能逃回家,好在不久后他们的“船屋”就可建成。
果然,海景女师下一学年不再聘她任教,说是学校经费紧张。回到船屋后的她事实上找到了庇护和安慰了吗?
她大哭着扑进丈夫的怀抱,张宝龄非但没有紧紧抱住她,反而将她推开,并冷冷地说:“这有失礼仪!”
“这是在家里呵!”
“家里也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性格。”
……
“我知道自己三次拒婚曾让你不高兴,我再次向你表示道歉,请你看在这都是另有原因的分上原谅我。”
“与那无关!其实我也求之不得……我需要的妻子不是你这样的,而是一个贤妻良母。”
她越发哭得更大声了,张宝龄很不耐烦地说:“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女人哭!”说着一甩门出去了,并且很快便扔下她,一个人去了上海。
偌大的一条大船上,只留下了她一个人在其中,它感到自己这个“水手”已无力将这条船开进那风光无限的生活海洋了。可是她又清楚地记得,当时搬进船屋时他们是那么的兴奋,她都记不清自己曾经多少次设计其中的布置和摆设,也记不清多少次在其中梦想着自己将来的美好生活,梦想着自己与张宝龄就是这条大船上的水手,他们将驾着这条属于自己的大船驶向那风光无限的生活海洋……
她万万没有想到,竟然这么快,这条大船就这样搁浅了,搁浅在了生活的荒滩上。
一只鸽子飞到了她的窗台上,它咕咕咕的叫声似乎唤醒了苏雪林作为一个女人内心全部的妻性和母性;她想将它揽入手中,抚摸它,给它以爱的抚慰,可它竟然扑扑翅膀飞走了。忽然间她倒因此而有了灵感,何不将自己的情和爱、苦和乐、伤和痛都与这小生灵说说呢?于是有了《鸽儿的通信》,有了《我们的秋天》,有了被她后来称为“美丽的谎言”的新婚日记《绿天》。当然还有《棘心》。
《绿天》和《棘心》的出版,一举奠定了苏雪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名作。然而我们读着这些优美的文字时,没有人会想到,它们竟写于一条搁浅的爱情与婚姻的空船上哩!
五
苏雪林将自己一生的爱情埋葬后离开了苏州这个伤心地。
此时毕竟丈夫与婆家都在上海,所以她自然而然地回到了上海,不久她又去了安徽大学,之后不久,去了武汉大学。在这一过程中,其实苏雪林并非没有重新获得爱情的机会,但她都自己放弃了,
1930年,苏雪林被安徽大学聘为教授,竟有三个很不错的人试图走进她生活并给她带来了三次重生爱情的机会。其一是一位“银行家”,原是张宝龄的同学;其二是一位给她写过无数情真意切的情书的医生;其三是她的同事,一位学术上小有成就的学者。苏雪林对于他们的爱意其实十分清楚,为此她还写了《小小银翅蝴蝶故事之二》,将他们分别比喻为飞蛾、虺蜴和天牛,但是,或许是因为自己已有誓言在先,或许是顾忌于自己与张宝龄的关系虽“实亡”但毕竟“名存”的缘故,她这只高傲的蝴蝶对他们一律不屑一顾。
1931年8月,苏雪林来到武汉大学,初到珞珈山她就遇到了一位教体育的同事S先生,可尽管这位帅气的S先生不但“读过《棘心》,并很有兴趣”,而且还教她学习游泳,学习骑自行车;尽管S先生教她骑自行车时,竟骑得“脸色也跟着泛上了桃花般的红艳,浑身的气血也在这汗水的漫溢间畅通了”;尽管她后来每骑自行车总常常想起那位S先生……但她终究没能让他走进自己的生活。
不知怎么回事,每当面对这样的机会,她总是想起还是在法国时父亲在一封信上说过的话:
你不必怀疑张宝龄,他比你操守还坚固呢。我听人说,他在美国躬身自好,目不斜视,同学无不许为君子。有一个美国女同学,曾示意爱他,他特将你的相片插在衣袋里带到学校,让那女同学看见,说是未婚妻……
苏雪林或许一直在潜意识中与张宝龄比着谁的“操守坚固”吧!殊不知正是在这样的比试中,她将自己的手脚和心越束越紧。为此著名女作家,也是苏雪林在安庆师范附小的同事、北京女高师的同学庐隐曾说:如果苏雪林是一位真正的解放的女性,她早就解除那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了,因为她“还不乏对她的爱慕者”。此话说得可谓是一针见血。
苏雪林本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解放的女性”。
好在没有了爱情,还有事业!
晚年的苏雪林在自己的《自传》中就自己的爱情婚姻生活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想我今日在文学和学术界薄有成就,正要感谢这不幸的婚姻。假如我婚姻美满,丈夫爱怜,又生有一窝儿女,我必安宁于家庭生活,做个贤妻良母,再也不想到社会上去奋斗,则我哪能有今日的成就……我已知自己身世是个缺陷,但这个缺陷未尝不美。
这样达观而从容地看待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固然与她此时已是人生晚境,眼里的一切都看得淡了有关,但也不能说与苏雪林固有的爱情观和事业观无关,纵观她的一生,她似乎始终将事业放在爱情之上。张宝龄走后,苏雪林很快便发表了剧本《玫瑰与春》,其中她借剧中人物之口宣布:
我以后要勇敢地向前奋斗,在我尚未灭亡之前,不但不再叹一声气,再流一滴泪,而且脸上要永远漾着温和愉快的微笑。玫瑰,你究竟太自私了,你不配作为理想的伴侣。去吧,永远地去你的吧!从此我是脱然无累,可以安心干我所要干的工作了。
回顾苏雪林一生,其事业上真正成名还是在武汉大学的十多年间。而要说起这,又不能不提到她从苏州回到上海后结识袁昌英、凌叔华和初见鲁迅。
由于结识了袁昌英和凌叔华,使她有机会于20世纪30年代三人相会于珞珈山下,曾被一时誉为“珞珈三杰”;而初识鲁迅,却使她有一天终于扯起了“反鲁”的大旗,并因此而暴得大名,就此走上了终生反鲁的道路,最终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有家难归。
1928年7月7日,这是一个让苏雪林刻骨铭心的日子。那一天,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在悦宾楼设午宴招待在他的书局出版过书籍的作者。苏雪林由于在那儿出过《绿天》等,且销路很不错,因此也在被邀之列。说实话,此时的苏雪林充其量还只是一名文学新秀,能得到这样的邀请她自感是很荣幸的,心想着能参加这样的午宴也一定是很愉快的,因为有机会见到许多名字早已如雷贯耳的文坛大家。
那天天特别的热,但是苏雪林一点也没有在意,她早早地顶着烈日去赴会了,可是没想到路上几经周折,赶到悦宾楼时,在门口迎接的李小峰的侄儿说:“客人们都到了,就等您了!”再一打听,到的客人中有达夫先生和他夫人王映霞,还有鲁迅先生……
关于这次午宴,郁达夫和鲁迅分别都在自己的日记中有所记载。郁达夫的日记中记道:“中午北新书局宴客,有杭州来钦文,川岛等及鲁迅、林语堂夫妇。席间遇绿漪女士(苏雪林。本文作者注)。新自法国来,是一本小品文的著者,文思清新,大有冰心女士的风趣。”据此我们可以肯定两点,一是那天苏雪林到得确实有点晚,二是郁达夫对苏雪林还多有褒嘉。鲁迅在日记中记道:“晴。午得小峰柬招饮于悦宾楼,同席矛尘、钦文、苏梅(苏雪林。本文作者注)、达夫、映霞、玉堂及夫人并女及侄、小峰及其夫人及侄等。”由此可知,鲁迅对于苏雪林虽无如郁达夫的褒嘉,但也并无交恶。然而苏雪林却在这次宴会上得到了相反的感受。
当苏雪林推门走进包间时,见眼前的确已坐满了客人。李小峰夫妇最先站起来迎了上去。“我担心您怕热不来了哩!来来来,认识一下。”然后将她介绍给大家,“这是苏雪林女士,我们北新出了她三本书。”
苏雪林也微笑着说:“非常抱歉,让诸位先生久等了!”
然后李小峰又一一向苏雪林介绍客人:“这是林语堂先生……”她赶忙上前致意,林语堂客气地与她握手,并说:“苏梅女士,你笔锋很厉害呵!”
“这是矛尘先生!”
“哈哈,我们认识!”
于是也热情握手。
“这是达夫先生!这是他夫人王映霞女士!”
“刚拜读过大作《绿天》,文笔非常优美,我很喜欢!”
于是也热情地握手。
……
来到了鲁迅先生面前,见鲁迅先生坐在一张沙发上似若有所思。还没等李小峰介绍,苏雪林就有些激动地说:“鲁迅先生是吧?”同时满脸微笑着将手伸了过去。可是没有想到,鲁迅只是向她微微点了一下头,并没有与她答话,也没有给她一个笑脸,更没有与她握手,她伸出的手一时不知如何收回。
见此情景,李小峰连忙大声说:“开席!上菜……”
或许鲁迅此时确另有所思,无意中有所疏忽,或许鲁迅只是想以此来表示一下对她来晚的小小抗议,然而这对于敏感的苏雪林来说,这一顿午宴竟因此而成了她一生吃过的最难以下咽的一顿饭!这一天也成了她一生中最铭心刻骨的黑暗一天。
在该见的时空中,见得了该见的人,那是一种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