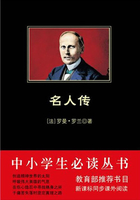而这一阶段张爱玲与她生活在一起,欲不受其影响才奇怪哩!所以,那时的张爱玲,虽然见过她的人都觉得她像个“傻不经事”的中学生,但实际上并不“傻”了,她的“傻”只是对于世俗里的琐碎不太在意或不愿在意,但对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她早已世故和精明得很了。如在文学事业上她看得比谁都透,并能一语道破:“出名要趁早”,甚至在自我经营上她也早已有了自己的生意经和小九九。那时物价飞涨,人们都挑值钱的东西买,而她竟然一下子囤积了许多白纸,于是有人跟她说,现在非常时期,谁还看书呵,你还是少出为好。她却说:“我要多出,打铁要趁热!”果然,很快别人就只能眼看着她用自己囤积的纸印出一本又一本小说并独家畅销,为她不但赚得名气,也赚得大把大把的钞票。张爱玲对“生意经”的如此精通和成功运用,我怎么看都会看到张茂渊的影子,甚至我怀疑是否直接来自于张茂渊的指点,只是张爱玲没有说过,张茂渊也没有说过,我在此不好妄下结论。
三
前文已经说到,张茂渊与张爱玲生活期间还打了两场官司,一场是与张志潜打的,一场是与张延重打的,前者是她同父异母的长兄,也就是张爱玲的大伯;后者则是她的亲哥哥,也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官司的起因是张茂渊认为张志潜主持家庭的财产分割不公。
中国人向来都信奉“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所以家里的事一般都很忌讳去见官,此所谓“自家菜篮的菜拿到别人菜篮去洗”。但是张茂渊偏不认这个理!
打官司在中国历来都是“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所以中国人多数都是“冤死了不告状”,但是张茂渊偏不信这个邪!
虽说此时是民国了,但是打官司这样的事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要写状纸,拿证据,找证人,请律师,还要疏通关节等等,作为一个弱女子,要独自面对这些,可以想象决不是容易的事,但张茂渊都独自承受了下来。更何况与自己公堂对簿的都是自己的亲人,整个过程中要经受怎样的心灵煎熬,只有她自己知道。另外还要承受舆论的压力,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多数人都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是没有资格在家里计较财产的;虽然张茂渊并未“嫁出去”,但毕竟只是张家的“女儿”。
但是张茂渊一意孤行,还是去打了这两起官司,其特立独行又一次显现无遗。
众所周知,在现代作家中,张爱玲是一个特别独立的人,且其独立性是表现在从人格的方方面面到生活事事处处和人生的自始至终,而其源头似乎也可在张茂渊的特立独行中找到。
官司的结果是张茂渊输了,输的原因在她看来完全是自己亲哥哥张延重收受了张志潜的好处而在法庭上倒戈。这样的结果将张茂渊的心彻底的冷了,也彻底冰冻了她亲情的最后一线余温,从此以后,她对亲情变得麻木了漠然了,也从此以后,无论她在生活中再遇到任何艰难困苦,也从来没有再找过他们去倾诉,更不会上他们的门去要过一分钱。直到最后张延重去世,家里打电话告诉她,她也只是在电话中冷冷地“嗯”了一声,再也没有说什么,更没有去吊唁。她没有悲伤,当然也没有兴奋,有的只是冷漠和决绝。当一些人因此而对张茂渊不无指责时,只要再设身处地想一想,这又能怪她吗?她的这一切表现,不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甚至是十分应该的吗?
所以,尽管张茂渊事实上很喜欢张爱玲这个侄女,并与她长期相依为命,但是她们一起生活从来都是“AA制”;张爱玲考取了圣约翰大学,学费迟迟没有着落,张茂渊也不肯帮着出一分,因为她觉得这“应该”是张爱玲的父亲的事;张爱玲果真“趁早”出名了,但是张茂渊并不看重,依然当她的白领,回到家里依然与张爱玲“AA制”……她因为受伤害太深,所以她不想再受伤害,更不想因为自己的过度热情而有可能使这种伤害很深;她理智得近乎冷漠地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和任何事,所以常常目光犀利而近乎挑剔,语言深刻而近乎刻薄。
张爱玲回忆说,她小时候看《孽海花》,看到有关章节中描写父母如何如何相敬如宾、琴瑟相和,不禁心向往之,没想到姑姑却说:“我想,奶奶是不愿意吧!”虽然很煞风景,但是细想想应该说得是大体不错的。这似乎让我们不由得明白,在张爱玲的笔下,为什么总喜欢将最美好的东西残酷地撕裂,从而展现其丑的事实和本质!
总之,在活得真实而不虚伪,活得理智而冷静方面,张爱玲与张茂渊的确表现得非常相似,所不相同的只不过是张爱玲却将此用在了文学中,而张茂渊将这用在了生活中;也唯因如此,张爱玲在生活中的有些方面似乎有点“傻不经事”,而张茂渊对于文学似乎总有些不屑而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张爱玲也承认,姑姑实际上是有着极高的文学才能的,她的创作实际上向姑姑学习了许多。张爱玲这样说不只是一种吹捧,因为她不但举出过许多例子,而且还在平时生活中,将姑姑说过的一些极有文学性的话语随时记录下来,以备创作之用。张爱玲一生中最奇妙的一部名著《姑姑语录》便是这样产生的。如有一次,张茂渊在洗头,发现水很黑,便不经意地说:“就跟头发掉色似的。”还有一次,从楼上公寓的窗口俯视到下面行道树下有几个日本兵,说:“他们真像是树上的青虫!”这样很奇妙很文学的比喻,如果张爱玲自己不说,读者一定会觉得典型“张爱玲式”,但是殊不知原本是“张茂渊式”,这类语言的版权原本在她那儿哩!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张茂渊也去搞文学,说不定不会输给张爱玲,更何况她原本在文学界就有着比张爱玲更多的关系哩!
张爱玲出名后作品自然总是洛阳纸贵,每一稿成,各家杂志、报馆和出版社都争相抢夺,可在她还是个文学青年时却不是这样。处女作写成了,她抱着小说稿一家一家敲杂志社的门,敲到苏青门下,这才有了苏青对她“傻不经事”的第一印象。是的,哪有这样投稿的?不碰一鼻子灰才怪哩!得先找一名家推荐,请他即使不能写个序言、评论之类,至少得写封信或写个条呵!这种情形,恐怕直到今天的文坛也是如此吧?一个文学青年,想通过自由投稿,就能发表作品以至成为作家,这实在是太难了。
从这一点来说,张爱玲初闯文坛时遇到的难题,与我们今天文学青年遇到的是一样的,当然解决的方法也与今天大同小异,大多数人对此一定都会心知肚明、心照不宣。
张茂渊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一个叫黄岳渊的人,当时是上海名流,张茂渊将张爱玲领到黄老先生面前,几声世伯叫过后,他终于答应将张爱玲引荐给当时上海最走红的文学杂志《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这才有了张爱玲的横空出世。
所以说张茂渊是张爱玲的文学伯乐似乎一点也不为过。甚至有人说,张茂渊几乎就是张爱玲的文学导师,因为在张爱玲的创作历程中可以明显看出,她在与张茂渊一起的十年中,是其一生的第一个创作高峰,也是唯一的一个创作高峰,当她离开张茂渊独自去了国外后,创作源泉便似乎就此枯竭了一般,虽然也有作品发表,但质量每况愈下。当然其中的原因并不如此简单,但是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
以斯而言,张茂渊是成就了张爱玲的文学事业的人,至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员。
四
是女人都似乎终难逃爱情一劫,聪明如张爱玲者最终也没能逃过,张茂渊注定也一样的在劫难逃,且她与张爱玲一样,在爱情上似乎也总表现得“傻不经事”。
我猜想,苏青在说张爱玲“傻不经事”时,心里一定是很复杂的,因为此时胡兰成已先与自己有一腿了,她当然不希望胡兰成再去找别的女人,且还是自己的朋友;再则她也很为张爱玲捏一把汗,因为她既已领教了并抵挡不住胡兰成这个情场老手的厉害,在她想来张爱玲无论如何更是抵挡不住的。苏青果然不幸猜中,张爱玲果然浑然不知,兴冲冲地以为捡着个天上掉下的大元宝,一头扎进了胡兰成的怀抱,一扎到底,最终扎得鼻青脸肿,以至差点身败名裂。当然这是后话。
张茂渊呢,虽然也曾对张爱玲有过“至于吗!不就是个伪政府中的小文员,你何至于如此隆重地去见”的告诫,但在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时,她还是让自己最好的朋友(当然也是张爱玲的朋友)炎樱做了伴娘,然而不久的事实是,胡兰成给炎樱也写起了长长的情书。张爱玲与张茂渊对此都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由此不能不说,虽然是胡兰成太过厉害,但也可见张茂渊与张爱玲对于男女之事是迟钝的,或者是实心眼的,不设防的,傻的。
张茂渊的感情据说最早竟发生在同性之间,对象就是张爱玲的母亲黄逸凡,再后来又爱上了自己的表哥或是表弟,再后来又与一外籍混血儿发生了办公室恋情。每一次她都一头扎进去,以牺牲自己为前提地爱着对方,每次也总是以自己的牺牲为结局。好在她能做到并不把爱情当做生活和人生的全部,更不会将自己的衣食住行都系在男人的裤腰带上,所以她之对待爱情:一旦遇到,就全心全意投入;一旦没了,也不会要死要活。无论是有爱还是没爱,她都能不慌不忙地生活,不会在失去爱时发现自己早已因投入其中而被烧煳了,成了废物。黄逸凡似乎正是这样的人——她为了爱情,长年提着一箱古董满世界追逐,到头来什么也没追着,只落得个客死他乡的悲惨结局。
张爱玲的爱情观与张茂渊似乎一脉相承,由张胡之恋不难看出,在她看来,既是爱情,那就与别的无关;既然爱了,那也不必管别的,总之应该全心全意,实心实意。张爱玲得知胡兰成另有新欢,去责问他,胡兰成说:“在汉口大半年,都是小周姑娘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我怎么能……”张爱玲先是怒不可遏地以不屑的口气说:“不过是奴仆,从前我们家有十几个围着我转哩!”这是典型的张爱玲风格,失败面前也不失傲慢,厉害!可是,傲慢过后,她的头终于又慢慢地低下了,轻轻说:“那些照顾人的事,我又不是不会做……”那一幕,让人真是要落泪—一个能写出《沉香屑》的人,原本也是会当老妈子的!多么可敬、可叹,又可怜、可悲呵!这是为什么呵?当然是为了爱。因此当胡兰成成了汉奸躲在温州乡下,张爱玲竟然还千里迢迢去寻夫,当她发现胡兰成竟然又有了别的新欢时,她并没有高傲地转身离去,而是还要让胡兰成做一道选择题:是选择自己还是别的女人?但胡兰成很快就轻松地将皮球踢回给了她:一个全国通缉的罪犯(胡自指),一个关在牢里(小周),你还让我选什么,你傻不傻呵?张爱玲无语,然后是默默离开,然后是给这个又一次骗了她的男人寄钱。唉,是的,傻不傻呵?真傻!张爱玲似乎只学到了张茂渊之于爱情的真诚和执著,并没有学到姑姑对于爱情的那种拿得起放得下,所以张爱玲最终也没有收获到真正的爱情果实,而张茂渊最终倒也算收获了,尽管这收获是那么的晚。
1987年,78岁的张茂渊终于披上了婚纱,与李开第喜结良缘。收到姑姑打来的电报,张爱玲说:“我知道姑姑总有一天会结婚的,就是八十岁也会结婚的!”说这话时虽然张爱玲泪如雨下,且已68岁,但是仍掩不住自己语气中对于爱情的渴望。此后不久,她去香港为自己做了一次美容手术。
之所以说张茂渊这颗爱情的圣果收获得有点晚,并不是只指她结婚时的绝对年龄相对有点大了,更因为她与李开第相识相恋其实是发生在五十年前。五十年前他们相识相恋,一切是那么的自然而然,但是终止或者说暂停得也是那么的自然而然。既然中止了或暂停了,那也绝不勉强,这就是张茂渊的性格。十年浩劫中,李开第被迫扫厕所、刷马桶,张茂渊便默默地用自己做过女红也弹过钢琴、抽过雪茄的手帮他扫帮他刷。李开第的妻女卧病不起,她更是去替李开第为他妻子端汤递药,让他妻子在临死前留下遗言,希望她能与李开第结婚。这一切不能不让人无比敬仰,但是敬仰之余,又不能不让人想到张爱玲说过的那句话:“那些照顾人的事,我又不是不会做!”
呵!张爱玲与张茂渊,又是如此地心心相通!
是的,张爱玲太像张茂渊了,换一个角度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张茂渊,就不可能有张爱玲,无论是生活中的,还是文学中的!
然而,今天对于一般人来说,只知道张爱玲,不知道张茂渊,似乎张爱玲是天上掉下来的那个“玲妹妹”。其实即使是天才,那也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定是从生活中成长出来的。对于张茂渊来说,她当然绝没有想到,本来由自己照顾着成长起来的这个侄女,其身影竟然有一天完全遮住了自己,使得自己似乎反而是生活在她的身影里一般。
的确,张茂渊只能在张爱玲的身影里才能永生。没有张爱玲今天不会有人知道张茂渊,但没有张茂渊或许也没有张爱玲。前者是历史,后者也是历史!
她姓朱,单名一个“安”字,但是鲁迅无论是活着时还是过世后,都因为这个女人而常常不得安身和安心,因为她是他不愿伤害,也不忍抛弃,但又无法爱上的“大太太”。
朱安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都称鲁迅“大先生”,而称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则是“二先生”—她对周家兄弟俩如此“公平”的称谓,即使在周作人那儿也全没有封建大家庭中“长嫂为母”的霸气,倒恰恰意味着朱安终究只是周家一个无足轻重的弱势角色,甚至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多余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