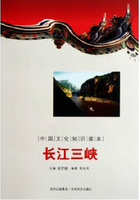两个人的叙旧变成一个人的回忆,我没想到我和单小双会话不投机到此,只能先搁一搁再说了。而单小双仿佛真是为了喝酒来的,五瓶啤酒,我面前一瓶还没见底呢,她那里已四瓶皆空了。我劝她吃点菜,她也不怎么吃,径自又叫服务员送啤酒。酒一瓶瓶送来,又被她一瓶瓶喝光,眼看着她面前已站了十几个空荡荡的瓶子了,觉得无论如何得阻止她一下了,就从她手里要过来酒瓶子说,你看我们光顾喝酒了,还没怎么说说话呢。
单小双也不跟我争,只是起开了另一瓶噌噌冒着泡沫的啤酒,分外疲惫沧桑地说,又有什么好说的。
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和老车殊途同归,居然一前一后进了城。我在聊城东郊读书,他在聊城北郊改造,我们还是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我还是无法忽视他的存在。他压根也不想叫我忽视他,早在县城看守所羁押期间,他就把我当成救命的稻草,几次发明信片给我,托我给他疏通关系,帮他打官司什么的。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也从内心里不愿意管,只是一想到他的事多少与我有关,况且又对他死去的表哥怀有歉意,毕竟心虚,就从牙缝里挤出点钱来,硬着头皮给他找了个律师。律师是我大学同学的爸爸,说老车这案子,数罪并罚至少要判15年有期徒刑的,他上下游说,没少在法庭内外做工作,终于在11年上生成判决。因为是批捕在逃,又是主犯,案子速战速决,老车很快就转到我就读的这个地区所在市服刑,与我咫尺之遥。这样一来,他更是不停地写信或干脆托人捎话来,让我给他送吃的用的,甚至烟茶,仿佛我上辈子欠了他一样。我先前对他入狱而滋生的那点愧意,至此又被他亲手破坏掉了。
难为你送这送那的,老车这样辩解说,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可这里离家四五百里路,让老家来人,总不如你更近便些。等我出去了,再十倍百倍地还情。
我并不指望老车还情,但我不明白我怎么会如此摆脱不掉他的纠缠,总算考学进城了,他也如影随形地跟了来,叫我一天都不得清净。因为去看他就得顺便也给二壶、老一捎带点东西,都是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伙伴,哪能厚此薄彼。比起他来,我倒更愿意多看看二壶、老一。我的日子就此捉襟见肘,好容易争取来的一点奖学金和从牙缝里省下的几个钱,大多都花在了他们几个混混身上,以至于大一上学期结束,我连一张回家过年的车票都买不起,连跟白梦娣团聚一下都办不到了。
但这仍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
真相是,我骨子里活跃着既不安分又靠不住的因子,丰富而多元的大学生活使我几乎忘了乡下还有一个未婚的妻子。那么多闻所未闻的新思想,那么多刺激又充满挑战性的文体活动,叫我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眼花缭乱,忘乎所以,随波逐流中,也跟着懵里懵懂地参与到喧哗与骚动中去,一天天地忙于空谈,结社,参加这样那样的演讲朗诵辩论比赛。动辄指点江山,随处激扬文字,多是些形式大于内容的行为艺术。到暑假,我们几个不同系别的同学勤工俭学,联袂开了几个少儿书法绘画作文音乐辅导班,天天脚步匆匆,这个班出,那个班进,跟明星赶场似的,煞有介事。好容易到了第二年寒假,我仍然没及时回家,我跟师院的一帮同学登长城游孔府爬泰山去了,甚至还险些谈了一场恋爱。那天黄昏,我们在泰山滑雪,我和另一个女生在乐不思蜀中掉队了,先后滑出了规定的区域。仗着雪橇,我们虽然没少产生飞翔的快感,没少尖叫大笑逗趣,但也不同程度地摔伤了胳臂腿儿。她跟我既不同系,也不同级,低我一届,数学专业,原本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也不相往来,旅途中却走到了一起。她发现自己离群后就蹲在雪地上哭了,一眨眼由一个快乐天使变成了一个落难美人。我最见不得女孩子哭,跟著名的花痴宝哥儿有一拼,不光心里怜香惜玉,还动手把她拉起来,告诉她不用怕,只要跟我走,一定能走出这深山老林去。还现场发挥,在她耳边胡诌着行吟出一首诗来——
没有比在路上的人,
更需要结伴;
也没有比结伴同行的人,
更能决定我们走多远
女孩很快破涕为笑了,雀跃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又挽上我的手说,是挺蒙人的,不过我喜欢。可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怪毛病的?我只知道自己有毛病,不知道她也有,正有点摸不着头脑,她又附上我的耳际说,你相信吗,我最喜欢跟一个人走了,从小就喜欢,哪怕那个人是个骗子,把我领到一条越走越黑的道上。我明白我也是,但我没有跟她说,因为我的怪毛病比她多去了,一时半会儿根本罗列不完。当下两个人互相搀扶着,走一会停一会,既找不到队伍,也辨不清方向,而天色果然就眼看着黑了下来。天愈黑,我们靠得愈紧密,脸贴在脸上,手握在手里,互相安慰鼓气中,恋爱的错觉突如其来。商量好就这样手足相抵一夜,肝胆相照一夜,走累了就找个背风处歇一歇,彼此温暖呵护到天明,到天明了,正好最早看日出。直到那个女生喃喃起悄悄话,说她在中学时期就憧憬跟一个人浪迹天涯,结果跟一个勇气不足的地理老师私奔未遂,又问我过去都有什么情感故事,我才恍然梦醒,恨不得即刻落荒而逃,我陷入的哪是什么荒山野岭,而是典型意义上的泥淖沼泽。我怀疑,我很可能是看见她落单,自己也才故意落单的。那时我还不知道上帝已在冥冥中安排好了每一桩缘分,不知道这个女孩最终将成为我的妻子,只是无比汗颜地放开她说,对不起,我在老家已找好了媳妇。那女生慢慢地圆睁了杏目,又慢慢地倒竖了柳眉,却一点也不慢地裹挟了风声,劈手甩过来一巴掌说,你这个混蛋,你刚才还吻了我呀。如此羔羊迷途,等待我的,也该是一份切肤的痛吧。
我是大年三十那个傍晚才回到家的。回到家才得知,在我进城读书的这一年半时光里,白梦娣的神色越来越呆,目光越来越直,一天到晚地躲在屋子里,怕光,更怕见人,常常一个人哭,一个人笑,一个人自言自语,她再不是那个冰雪聪明的可人儿了。为找回白梦娣的魂,两家的老人已没少给她寻偏方,请巫婆,不止一次灌她喝过这样那样的汤药,以及掺杂了香烛灰纸箔灰的水。庸医害人,只会往伤口上撒盐,把花朵摧毁。那时她形容憔悴,形销骨立,看见我就像根本没有看见我,目光涣散得就像没有目光。我没有任何资格抱怨任何人,只有抱着她默默地流泪。她反应不过来还好,一反应过来,就躲,就嚷,就往下出溜,比那年在农中时我一拉她的手她就抱头鼠窜的情形还要更强烈。等她好容易安静下来,我比比画画地说,我要带她到市里的医院看看病,要不会越来越严重的。她好像听懂了,但一叫她出门,她竟丢下我,自顾自把几件破衣服抻开来叠上,叠上再抻开,反反复复地说,你总得叫我收拾一下啊,你总得叫我收拾一下啊。我隐约觉得这话有点耳熟,一愣怔,就见她又两手抱住头说,你叫我想想,你叫我想想。
我双手掩耳蹲到了地上。
从来都没有旧好可以重修,就像那个广为流传的拔钉子的故事,钉子可以从木桩上拔下来,但木桩上已是伤痕累累,千疮百孔。老人们告诉我,收拾衣服和抱头,几乎是小六妮的两个习惯动作。别说外人,就是爹娘让她去干点事情,比如叫她去提桶水或磨袋面什么的,她稍微觉得不对劲了,也会很突兀地重复起这两个动作。之所以一直没告诉我,一是怕影响我功课,二是想把她看好了再说,谁知就看不好了呢?那一刻我悔到心碎,悔青了肠子,想把老车杀死,然后自杀,我们合伙把一个美丽的姑娘给毁了。我记得我和白梦娣热恋的时候,她偶尔也会出出神,发发呆,我只要拉住她的手,附上她的耳际,轻轻说一句跟我说爱我,无论她说还是不说,都会从远处收回来目光,连害羞带撒娇地偎到我怀里,就跟这句话是打开她心灵的密码或钥匙一样。我想重新唤起她的回忆和感知,把她揽到怀里,喃喃出声说,跟我说爱我。此一时彼一时,我不知这句话已不灵验了,她比正常人还正常地推开我说,我爱你什么?
我的大学生涯很庸常,少有往事可圈可点,不知是高中阶段把所有的力气使完了,还是高中那几年的事太多,把脑汁子给绞尽了。我比别的同学更不如的是,乡间还有一个未婚妻,并且患有精神病,我那股意气风发的劲儿,从大二下学期就分崩离析。来自亲密爱人的一句“我爱你什么”叫我自惭形秽,多少天后仍深感无地自容。我先前还有个学业完毕再报考研究生的想法,也只是想想,人一懈怠下来,再想振作就难了。
在聊城读书期间,我带白梦娣来看过几次病。医生说看得太晚了,延误了病情,一时也没啥好法,慢慢调理吧。有一次是我姐姐陪她来的,见她药一退去又说胡话,就问我以后怎么打算的,难道真要叫她拖累一辈子。我的心很疼,不是没想过变心,不是对别的同学没一点好感,但谁酿的苦酒谁喝,白梦娣这个包袱我不背谁背。我姐姐也好一阵叹气,又问我分配的事有着落了没,有没有希望留校或留城。我在大三下学期开始出任学院文学社刊的执行主编,并在全国一些不错的期刊上发表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在同学之间,算是小有成绩的,争取一下,也不是一点可能都没有。但想想白梦娣需要我照顾,老车他们也还有好几年的刑期,不如快点离开的好,眼不见心不烦哩。所以当同学们开始为就业或明或暗地活动时,我听天由命,很自然地被发落回原籍,成为单小双的同事。单小双看见我略略一惊,苦笑了一下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我差不多算赶上了国家大中专毕业生分配政策的末班车,还能回墨水镇农中教书。但与此同时,也赶上了墨水镇农中解体。在石悄悄的领导下,农中境况一年不如一年,先是拖欠教师工资,三五个月下发不了一次,接下来故技重演,又玩起当初苟延残喘的招数,改头换面为墨水镇中心初中,还真是误人子弟上瘾了。石悄悄对墨水镇教育事业的最大贡献,就是在她手上结束了高级中学的历史,把大雪球滚成小雪球。只是这几年农中农中地叫惯了,大家一时改不了口,每说起它,都还说它是农中。学校里本来就人浮于事,这下更显出僧多粥少的局促相来,开始实行买断制轮岗制。石悄悄一向与单小双不睦,至此有了弃之不用的理由,因为学校取消了农技课,她便把她无限期地晾了起来。一个人小肚鸡肠如她,也同样记恨我,当初毕竟是因为我的转学直接离散了人心,走掉老车几个混混也罢了,连白梦娣一个好学生都没留住,此番落到她手上,难怪要看我不顺眼。我一个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就算不放心我生手担主课,不让我教语文,也该安排给我历史政治地理一类的科目吧,她却非要我教两个初三班的化学,还不说用人所短,还非说要把我锻炼培养成一个多面手不可。我的化学基础很差,教学生得从头学起,如此现发现卖的,岂不也成了误人子弟!我有好几次要求调换,她就好几次跟我说,我也知道委屈你这高材生了,可我这儿庙小,没法给你提供用武之地哟。仿佛学校成了她家的一样。
有道是祸不单行。白梦娣那儿丝毫没见好转,我父亲又积劳成疾,就在我毕业那年的深秋十月,一场大病夺去了他刚过半百的生命。我说过,我父亲内心深处是指望过我学而优则仕的,如今只回来当了一个小教师,月薪不过百把块钱,且不能及时拿到,不光没叫他歇一口气,还不得不重新给我操心娶亲成家一类事。那时他已从村委会要来了一块宅基地,又自制模具,亲手烧好了一窑红砖,一窑红瓦,不能自力更生的水泥沙子石灰,以及门窗玻璃檩条,他攒点钱就去购买一地排车来,再攒点钱又去购买一地排车来,蚂蚁搬家似的,陆陆续续地备下了盖新房的大部分材料。他是要给我们盖一座明三间暗五间的大房子的,准备让我和白梦娣在那个春节完婚。当时村里富裕些的人家,时兴盖那种房子,我们家不富裕,但父亲不想叫别人小瞧了我们。新宅基地在村子南头,边上有一个两三个人深的大坑,就是那个大坑要了他的命。为了填平它,他计划赶在秋收以后和秋种之前的这个当口,从我们家责任田里一层一层地起土,再一地排车一地排车地运来。他运得起早贪黑,在一个天还没亮的黎明,他把一车土靠着助跑动作猛地掀到坑里的时候,没能收住脚,自己也猛地一下扑到了坑里。
数年如一日的超负荷运转毁掉了我的父亲,他一倒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到了镇卫生院一检查,父亲身上所有的零件几乎都用坏了,胃肺心脾没有一样完好的,并查出了贲门癌,已到不可救治的晚期。父亲绝对不能算一个恶人,但任劳任怨一生,到头来还是患上了噎食这一报应恶人的顽症,吃不下饭,咽不下水,叫我深感报应一说太虚妄了,怎么说都说不通。父亲拒绝治疗,自责没置下一点儿家业,不能再往他身上白白花钱了。镇上也不敢动手术,县里虽然没说不敢,但强调了没那个必要。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要一意孤行地违背父亲的意愿,在他毫无反抗能力的垂危时刻,又辗转到聊城,找同学,托老师,好歹是答应动手术了,结果也只是白挨了一刀,医生打开一看实在没法动,又按原样匆匆缝上了。我深深记得父亲身上的那条长长的刀痕,它从父亲的左胸口划至父亲的腰部,到死都没有愈合。此后许多年里,这条斜穿父亲身体的刀痕一直划在我心上,叫我在懊悔、自责、默哀中,独自承受子欲养而亲不在的缺憾和痛惜。一个凉意袭人的雨夜,他在气若游丝的弥留之际弥留了很长时间,几次把我叫到跟前,几次才把一句话断断续续地说完——
要孝顺你娘,他说,还要学会节俭,承受,担当和与人为善。
知子莫若父,父亲了然洞悉我的一切。我上面有姐姐,下面有弟弟妹妹,他却独独放心不下我,在我身上曾经发生和必将发生的一切,都囊括在他最后一句努力了半天才拼凑完整的临终遗言里面了。我应该好好想想父亲这句沉甸甸的话,即使受到不公正待遇,好人也得了恶疾,仍然矢志不渝,到死都强调与人为善。这是他辛苦操劳一生的思想智慧和行为准则,是他留给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宝贵的遗产,舔犊情深。但我让父亲不放心是他从内心深处就看准了的,结果就像他担心的一样,在后来的人生旅程中,我会离他这话的核心坐标越来越远,直到踏上一条不归路。彼时,父亲说完便撒手而去,任我和姊妹们哭哑了喉咙,再也唤不醒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