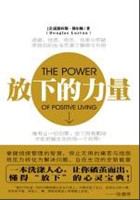俗话说:有山靠山,有水依水。白井子依靠甚?所处的地理位置是:西接宁夏,北邻内蒙,南靠延安府,东有绥德、米脂、榆林。甘肃的华池、环县也只有一山之隔。因地处要道,有人把这里比喻成“旱码头”、“西口”,其意无非是要从这达走,就得过“西口”。
这里也有土地,也种五谷杂粮,但更重要的是每年的三月三,六月六、九月九的物资交流会,少则一月,多则四十天,尤其是九月会,更是红火的不得了。秋收刚过,脚夫们赶着牲灵,或是从弯弯曲曲的山野小道,或是宽宽展展的黄土小路,还是茫茫一片的沙海之中,以及涛涛有声的黄河岸边,驮上自己的红枣、绿豆、烟叶等土特产,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换回自己所需的皮毛、食盐、甘草、五谷杂粮,通过交流寻找财路。
每当此时,远远的沙土路上,一队队赶牲灵的脚夫队伍便向这里集中,把驮队装扮得十分耀眼,这似乎已形成了规矩,谁的驮队更威风,就显示出掌柜的更有派头。走在前头的那口骡子是百里挑一的好脚,浑身光亮,无一根杂毛,脑门心上抖动着五彩缨子,脖子上套一大串铜铃铛,随着牲灵们神气十足的“哒哒哒”的踏地声,铜铃悠扬的“丁当”声敲击着沙漠的平静。二三十头牲口串在一起,踏着铜铃的响音,迈着有劲的步子向目的地进发。赶牲灵的后生们心口也热热的,嗓子也痒痒的,止不住还吼上几句: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哟三盏盏的那个灯,
哎哟戴上了那个铃子哟哇哇的那个声。
白脖子的那个哈巴哟朝南的那个咬,
哎哟赶牲灵的那个人儿哟噢过呀来了。
从蒙地来的驼队也不示弱,每峰骆驼的脖子下挂着一个大铜铃,脑门心上顶着红粉带,一串几十峰,“咣当”的响声带着大草原的气息,和着“沙漠之舟”的脚步,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驼峰在沙梁梁上时隐时现,与沙海搅和在一起,悠荡地成为一片“舟在海里行”,只有那“咣当”响的驼铃声,才使人分辨清,是驼队过来了。
一来二去,久来久往,脚夫们和本地的女子婆姨们混熟了,少不了也弄个相好的换换口味。平日里难得见上一面,好不容易见面了,互诉衷肠,你送我块花花布,或是一瓶瓶雪花膏,抹头的杏核油;我给你做一件毛坎肩,或是一双手打的毛袜子,礼物不重情意深,相会才是真格的。遇上无风无雨,阳光和煦,无遮无挡,沙湾里,树下阴,都是相见的好地方,坐在绵格楚楚的沙沙上,互送礼品后,少不了进入互补精神空虚的状态,恩恩爱爱的哥呀、妹呀的亲热起来。如家中无人,悄悄把人带回盛(住)上一夜也是常有之事,有这么一首歌:
清水水那个玻璃隔着窗窗照,
满口口白牙牙对着哥哥笑。
双扇扇门来单扇扇开。
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
这里距边城不足六十华里,却太平了许多,不像边城那样,今天共产党来了,解放了;明天马鸿奎又打回来了,又占领了。三天两头,兵荒马乱,人心不宁。虽有队伍也从此经过,但很少进城堡,就是土匪也骚扰甚少。有人说这里有洋教堂,也有人说掌柜的刘义首人品好,反正和外边就是不一样。
刘义首,也有人称其为“留一手”,人沉稳而老道。三年前,土匪“沙里蜂”就曾来过一回,城堡里的人确实也惊慌了一阵子。看城门的王老二壮着胆子给掌柜刘义首提醒:“实在不行,给二少爷通个气,带队伍回来抵挡抵挡。”
这是刘义首最不愿意听到的,因为在他的心里二小子刘得财已经不存在了,原因很简单,他不学好,让他念书不好好念,让他经商也不干,成天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抽,一身的臭毛病,后来干脆到城里给马鸿奎的一个团长当了参谋。这让刘义首更为恼火,祖宗八辈子也没出过这种事。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真是家门不幸,一气之下,断了父子情义。王老二提到让他带队伍来抵挡“沙里蜂”,不真成了哪壶不开提哪壶,刘义首心里能痛快得了?
“咋?让我依势压势?不干!”刘义首白了王老二一眼:“我偏不信狼是麻的,他沙里蜂不是娘养的,不食人间香火,不吃五谷茶饭。给堡里人说,不要怕,该干甚的干甚,让沙里蜂冲着我来。你到时该开城门就把城门打开,其余的事不用管。”
“沙里蜂”真的来了。
城门真的开的展展的。
人们该干甚的干甚,只是心里在惴惴不安地“扑腾”着。
刘义首却稳如泰山,坐在大厅里,不慌不忙抽着水烟,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似的。
“沙里蜂”领着十多名土匪,骑着高头大马,腰里别着盒子炮,绕着城堡转了一圈,发现无甚情况,直冲刘义首而去。
刘义首抬了抬眼皮,问:“是否手头紧了?”
“刘掌柜的真是明白人”。“沙里蜂”并未下马,只是抱拳相告:“今日里正好从此地经过,打扰打扰!”
“好说!”刘义首站了起来,吹灭了正燃着的火香头,吩咐伙计:“抬出来!”
两伙计应声从后厅抬出一大筐白花花的响洋,放在了院子中间。
土匪们愣住了,大眼瞪小眼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还是把目光停在了“沙里蜂”的身上。
“沙里蜂”把两道砍刀眉锁了一锁,翻身下马,凶光直视着刘义首。
刘义首把嘴对着香火“呼”地又一吹,香又着了,转身坐在了太师椅上,“呼噜,呼噜”悠闲的有滋有味的品着水烟,喷出的烟雾在脸前缓缓缭绕着。
“沙里蜂”款款走到大筐前,把手伸进了筐里,顺势抓起了一把响洋,又缓慢的让响洋顺着手心一块一块地滑向筐里,响洋“丁当”的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哈哈哈!”“沙里蜂”仰天一阵狂笑:“没想到刘掌柜是如此畅快,我沙里蜂也是重义之人,这响洋就算是兄弟我暂借了,以后只要是刘掌柜的货。沙窝里照样通天,有难为的地方言传(说话)。忙,兄弟帮定了。”
土匪们一声呼哨,离开了城堡,转眼就无踪无影了,只看见沙窝里荡起的一阵阵尘埃。
“沙里蜂”就是“沙里蜂”,从此后再也没有来过城堡,就是其他土匪听说白井子三个字,也直竖拇指,来往的脚夫,只要报上白井子赶会有刘掌柜的货,土匪们立马让道。
刘义首虽然“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但他内心的苦却只能独自往肚里咽。几年来一直死丧不断,最看重的大儿子刘得贵前年突然爆病死了。半年后,大媳妇哭坏了身子,也死了。最让他受不了的是自己的老婆思儿心切,卧床不起,去年也撒手人间,离他而去。两年抬出三口棺材,受得了吗?二小子刘得财又是那么个“流逛锤”(不成器),他只能把唯一的希望全寄托在孙子刘英子的身上了。
刘英子也算听话懂事,对爷爷百依百顺,爷爷不让他上学校念洋文,说他二大就是念洋文学坏的。平日跟陈老侃念念“三字经”,八股文,识文学字,长进还真不小。刚满十六岁,爷爷就给他成了亲,无非是盼望着早日见上重孙子。有钱的人有有钱的烦恼,无钱的人有无钱的苦闷,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该过的光景还得一天天的过,一年年的熬。走过的路知道了,后边的路黑麻鼓冬,谁也说不清。人的命,天注定,该当官的当官,该发财的发财,是个要饭命的走走停停都离不了那根讨吃棍。刘掌柜平日最信奉的就是命。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又是古历的九月了。今年的会比往年起得早,八月刚尽就起了会。堡里堡外,好不热闹,有唱大戏的,有耍杂技的,卖小吃的和卖杂货搭的帐篷一个挨一个。俊男俏女们肩挨着肩,手拖着手,这个货摊上看看,那个帐篷里瞧瞧,碰上相中的衣裳在身上比划比划,合适了,付钱。
开饭馆的更是扯着嗓子在叫喊:“牛肉臊子拉面煮好啦!碗大舀得稠,浮起漂着辣子油。”
另一家也不示弱,声音扯的更长:“羊杂碎哟,圪堆冒尖了,不香不要钱哟!”
喝酒的、划拳的、叫卖的、唱戏的,合成一片红火的繁荣场景。
堡子外,一片平展的沙滩,骡、马、驴、牛,头顶红缨,拴在木桩上,一看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天然的牲口交易市场。买主和卖主手搭着筒筒,讨价还价的在底下用手捏着码码。有的男人为了炫耀自己,鼻梁上还架一副圆坨子茶色二饼子眼镜,以示自己的身价及富有。
夜戏散了,人却未尽,仍然有熙熙攘攘的人流从堡子里外出出进进,划拳的叫喊声和醉汉们的吵嚷声时隐时现。夜深了,才有稍许的安宁。
也是天公作美,这几天的天气却特别好。一大早,太阳红格彤彤地露出笑脸。
“又是一个好天气啊!”
掌柜刘义首这几天气色明显好多了,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忘记看看大门外墙根底他亲手栽的那棵枸杞树,这里人也叫“狗条刺”。在别人的眼里,种个花呀草呀的是为个清静好看,唯刘掌柜地对“狗条刺”却情有独钟。施肥、浇水,都是他亲手干,从不让人插手。望着刺头上掛着的红格澄澄的枸杞蛋蛋,刘掌柜舒心的拈下一颗含在嘴里细品着甜津津的滋味。这几年虽然家门不幸,但财路却未断。尤其是今年,一个客栈,一个货栈,人、货满沿沿的,对刘掌柜也算是个宽心了。用他的话讲,这叫东方不亮西方亮,丢了那样有这样,人不能光背霉,有样总比没样强。他哼起了昨晚大戏里“铡美案”包公的唱段来:
身穿黑,头戴黑
浑身上下一锭墨?
而内心深处仍是一种酸楚楚的感觉,这就叫“黄连树下弹三弦,苦中作乐”,他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得儿驾!”随着一声吆喝,姜骡子手持皮鞭,骑着一匹紫红骡子,吆着二十多匹牲口从客栈忽拥而出。他,十六七岁的样子,光溜溜的脑顶上留着一撮帽盖子(一撮头发),上身穿一件半旧不新的不吊面的老羊皮袄,敞着怀,肚脐眼露在外面。下身着一件宽松的大档棉裤,系一条红市布裤带,活扣两头长出半尺多的红绺绺,一抖一抖的。只是脚上的那双遍纳绑子鞋已露出了“大舅舅”(大拇指),俨然一副“神气十足”的架势,哟赶着牲口。
“小心把人踏上!”刘掌柜连忙叮咛着。
“解(音害)下(知道)啦!”姜骡子吱应着,把牲口拢在一起,吆出堡外,身后扬起一片黄尘。
“真是个灰锤子(冒失)”刘掌柜用巴掌搧了搧从眼前飘浮的尘土,心里又盘算起人的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