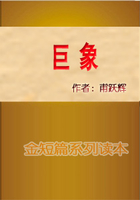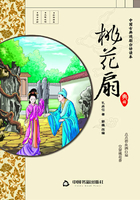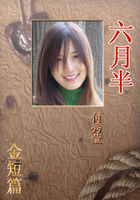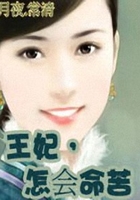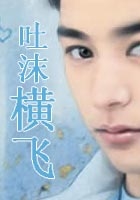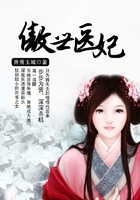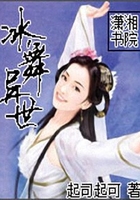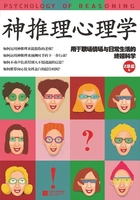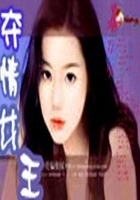早在一八七二年冬天,荷兰传教士携清廷“龙票”在这里建起了教堂。同时前来传教的还有比利时、法国的传教士。他们来了以后,勾结地方恶霸势力,在教堂周围筑墙挖壕,圈占牧场,侵占民田,挑拨教民与平民之间的关系,确实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不少麻烦事。而沙智林却不同于其他传教士,他待人随和,不依势欺人,和大家和睦共事,在人们的眼里,也不觉得这个大鼻子老沙有多么坏,相反,有事也请他帮忙。
教堂里早就空旷旷的,只有燃烧着的烛光在不停地跳跃着,使高挂在十字架的耶稣像也忽明忽暗,更显出一副痛苦不堪的神态。
在教堂的里边,有一间宽敞的暗室,几支蜡烛同时在蜡烛台上点燃着,室内明光一片,和民房相比,风声小了许多。老沙倒了两杯特别的红洋酒,顺势把一杯递给了身旁的修女。
“让我们共同享受慈祥的主赐给我们最好最美的甘醇吧!带我们到那个极乐而愉快的世界。”
修女,一位本地女子,年龄也不过十六七岁,修长的线条,细细的柳腰,像弯弓一样的眉毛,一双毛格茸茸的大花眼就如一潭清澈见底的湖水,透亮而吸引人。鼻梁子不高也不低,恰好镶在中间,给人一种无可挑剔的感觉。小嘴嘴一笑,就像三月的杏花开了一般,粉格楚楚的爱人。一口白生生、齐整整的牙齿,更增添了几分丽质。一张瓜子脸上生就的两个酒窝窝,衬托出了一个完整的美人胚子。这是老沙在靠近内蒙边上金鸡滩村传教时发现的,她的名字叫白美玉,家离白井子也不过八十里地,父母都是教民。让老沙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在异国土地,沙海茫茫的窝窝里,竟有如此美丽的“锦鸡”?说来事也凑巧,白美玉的母亲患有偏头疼,喝了多少苦药汤,老也不见效。老沙知道此事后,不辞劳苦,为其祈祷、瞧病。也真怪,几粒白药片片,竟将病去了个一干二净。在白美玉一家人眼里,老沙就是上帝的使者。侍奉老沙,就是侍奉上帝。为此,白美玉一年前就毫不犹豫来到教堂,当上了修女。这一切难道不是上帝的恩赐和安排吗?为此,老沙还给白美玉送了一个很好听的外国名字,“白得丽沙”。除此之外,又赠给她了一个只有老沙和她本人知道的雅号:“红苹果。”
美玉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即使天天如此,她也乐意,因为这是上帝的安排和旨意,不能有丝毫的违背。加之,老沙也挺会体贴人,尤其是男女方面,更能让她云来雾去。她和老沙碰着杯对饮着,一杯红洋酒下肚,只觉得浑身那股热乎劲在向外浸透着,两个脸蛋蛋泛出阵阵红晕,一种奇妙无比的麻酥酥的感觉,想要飞起来。尤其是那块神秘的男人们想要的“开阔地”,似蚂蚁在蠕动,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向敏感区靠近。啊!外国人太能行了,怎能发明出这么美妙而爽口的甘醇?让人如此陶醉。
老沙显得十分沉稳和老道,虽然红酒也在体内发挥着威力,搞得他的浑身燥热燥热的,但他深深懂得,只有此时才更要稳住,老练是成功的一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太急了是要烫嘴的。他像欣赏上帝赐给他一件珍品一般地注视着美玉的惟妙惟肖的神情变化:“啊!我可爱的红苹果,可惜上帝赐给我太迟了!”心里暗想着,一只手搂住了美玉,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玉峰”。
果然,美玉按耐不住欲火中烧,一下子扑到老沙的怀里,搂住了脖颈,老沙恰到好处地将舌尖尖款款地伸向美玉的嘴里。两张嘴津津有味的相互吸吮着,老沙只觉得搂着自己脖颈的那双手一会儿比一会儿紧。
他将美玉抱了起来,放在了还是从荷兰带来的洋床上,嘴中仍在吸吮着美玉的舌头,腾出一只手慢慢地解开了美玉的裤腰带,很熟练的就触及到那块“毛茸茸”的“开阔地”了。
“嗯!”美玉发出一声轻微的叫声,扭动了一下柳腰。老沙更觉得体内阵阵发热,那根粗而大的“东西”在缓缓的膨胀着。他再也忍不住了,脱光了自己的衣裳,又剥掉了美玉的衣裳。一双赤裸裸的肉体滚翻在床上?
外边的风仍在刮着,但似乎小了许多。
平房里,陈老侃继续侃着:“吴三桂看到连自己喜欢的女人都保不住,投靠你闯王有何用。身子一歪,倒向了清军。于是,在山海关摆下了一个战场。这边是投靠清军后的吴三桂,那边是刚从北京撤出的闯王军。也是天意所不容,也就在这个时候,天突然刮起来了狂风,那风不比咱这儿的风小多少。吴三桂完全处在上风的位置,也就是咱常说的‘上岗岗风’,而闯王呢,处于下风,就是‘顶头风’,风刮得将士们连眼也睁不开,还能打胜仗?”
陈老侃瞪着已被“羔酒”染红了的眼珠子,惋惜地甩动着脑袋上的“二道毛”:“天意不可违哟!”
“咣当!”一声,门被撞开了,随着一阵风刮了进来,麻油灯灭了。
石冲子妈,跌跌撞撞闯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冲子,你大出事了!”
“不要着急,慢慢说。”陈老侃边安慰边划着了火柴点着了麻油灯。他知道石冲子大石诚义前几天到宁夏去买树种,遇上这样的沙暴天往回返,要出事肯定是大事。
“还是王老二开得城门,牲口回来了,却没有人。”冲子妈显得十分着急,话语带着哭腔。
陈老侃紧皱了眉头,暗自想:不好,石诚义八九要出大事。但他嘴里却没说,只是叮咛大家:“赶快回去,把马灯点上,寻人!”
堡子里锣声响了,教堂的钟声也响了,只有遇上大事的时候才会这样。
风仍在刮,但小了许多。
人们集中在堡门口,各持马灯,都在听陈老侃的吩咐:
“王老二,你领上顺子、骡子,顺着风,向南找,其余人跟我向西走。记住了,在沙蒿圪堵会合。”
城堡子的两扇大门早已打开,几乎所有的人都惊动了,就连“福盛兴”掌柜的刘义首也在城堡门前焦虑等待着。
神父沙智林,修女白美玉不停地在胸前比划着十字,祈祷着上帝能够保佑受难的人平安无事。
沙窝里、沙梁上时隐时现地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亮,那是提在人们手里的马灯。
风不知什么时候竟断断续续地停了。东方已经泛出了白光,天就要明了。
根据陈老侃分析,果然在离沙蒿圪堵不远处找到了石诚义,但人早就僵了。眼里,鼻孔里,嘴里全灌满了沙子。
“不长眼的老天爷呀,撇下我们娘俩可咋活呀!”冲子妈号啕着,指着石诚义的尸体埋怨着:“短命鬼呀!走的时候就发着烧,让你好了再走,你偏不听,叫我以后可咋办呀?”
“大呀?”石冲子哭得更是泪人一般。
人们搀起了冲子妈和冲子,几个青年人抬起了已经被陈老侃蒙住脸的石诚义向城堡方向走去。
天已经大亮了,沙蒿蒿在微风中晃动着身躯,一伏一起,一起一伏,再伏再起,仿佛在向死者鞠躬默哀。
这里人的风俗:死在外边的人是不能再回城堡的。城外边搭一个灵棚,死人停在灵棚里,第二天下午入殓。掌柜的刘义首专门请来了一班子有名气的吹鼓手,一阵乐声,石诚义被安放在一口杨木棺材里。
冲子披麻戴孝跪在灵前,哭叫着:“大呀,我的大!”
石诚义生前不信教,一切都由陈老侃按当地风俗秉办。
沙智林和白美玉前来吊唁,不烧纸、不磕头,嘴里念叨着,在胸前比划着十字。
第三天一大早,太阳刚冒花,出殡的人早就准备好了一切。陈老侃右手持剁面刀,左手抓着守灵鸡,将剁面刀在鸡头上轻剁了两下,公鸡“嘎嘎”惊叫着。陈老侃一声高喊:“起灵!”四个小伙子,两边站立,用杠子穿过麻绳捆绞着的棺材,一齐发力,将棺材抬了起来。
石冲子眼睛用白纱布做成的“蒙眼罩”遮着,将顶在头顶上的灰盆使劲地摔在了一块早已备好的石头上,“咣当”一声,盆子被摔得粉碎,纸灰飞起一片。
吹鼓手腮帮子一鼓,凄凉婉转的一曲“秦雪梅吊孝”响了起来。于是,号啕声,哀乐声混为一体,在清晨的沙弯里格外清晰。
送殡的人们排成了一溜溜,沿着弯弯曲曲的沙漠小路向长城脚下走去。
也不知从甚时候起,长城边就成了这里人的葬身之地,据说,这里的风水好,咋个好?说不清,道不明,总之,死了一代又一代,活了一茬又一茬,无人能说清到底死了多少代,活了多少茬,死也好,活也罢,都是这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