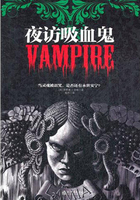白井子堡,这座明成化十三年就建起的用大青城砖砌成的坚固的城堡,东南两道城门共二里三分地,住着二十多户人家。因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因素,杂姓人多,就连外国人的天主教堂也建于此堡。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好大的一场狂沙,一刮就是三天三夜,一歇都不歇。风势好像无数双巨手轮番抓着沙子,在天空扬着、向大地掼着。刚长出绿芽的树,在大幅度地挣扎着躯干,拼命地和狂风较着劲。树枝和树梢发出阵阵“嗖嗖”的呼啸声,仿佛在呐喊、助威、叫阵。太阳早就躲藏得无踪无影了,天空由赤色变为黄色,又由黄色变为赤色,风势一点不减,“呼呼”地吼叫着,似乎要把整个大地吞噬下去。
在漫无边际的茫茫沙海中,一位中年男子,顶着狂风烈沙,吆着一头小毛驴,艰难地行进着。忽然一个踉跄,差一点摔倒在地。他挣扎着摇晃了几下身躯,但仍没有顶住烈风的劲力。从一架山梁上滚了下去?
风刮得更为猛烈了,小毛驴的身影早已被扬起的狂沙隐去?
狂沙在这里已属司空见惯,家户人早就拴好牲口圈好了羊,风刮得再凶,白天屋里点上灯,该做甚的做甚。
好赌钱的早就凑在一间烂草房里,一个碟子一个碗,再加一副骰子,随着庄家“哗啦哗啦”的一阵摇,将扣着骰子的碗、碟往桌上一放,庄家高叫着:“单卖一碗!”赌棍们有跟庄家走的,有唱反调的,叫准了赢,叫错了输。这里人把这种简单易懂的押宝赌博方式称之为“摇单双”。任凭室外风狂狂,骰碗照样“哗啦啦”。不要小看这骰碗,输了房子输了地,输光了羊子再输婆姨,输得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还照赌!
婆姨女子们也不怂,有男人弄的,就有女人弄的,你耍大的,我玩小的,仅此差别而已。几个婆姨女子坐在一起,马戏丑角扑克牌一摊,“掀花花”赌输赢。要不然弄副纸牌摸一摸,日子打发的也很快。
这样的天气,爱吃喝的自然会凑在一起,五六个人,宰只羊羔,拉起风箱,灶火里添把牛羊粪,水开肉烂,一只“宰羔子”滚瓜烂熟,外加一壶自制的“羔酒”,有酒有肉,滋味无穷。完了大家把羊肉酒钱一平摊,这就叫“打平伙”。待肉吃净了,弄块荞麦面,压几床饸饹,把羊肉汤也要喝干。已经成了规矩,在谁家“打平伙”,头蹄杂碎就归谁,主家贴点功夫并不吃亏,还挺乐意呢!
提起“羔酒”,更有来头,酒是自家酿造的纯粮食酒,不晓得是谁发明的,把死在母羊肚子里的胎羔洗剥干净,往盛满酒的坛子一泡,用黄泥封好坛盖,往地里一窖,待羊羔子在酒中化净,再启封酒坛,那个香啊,隔着院墙也能闻到。曾有这样一种说法:不怕天上狂沙起,不管炕上无芦席,硬叫尻子流脓水,也不让嘴上吃了亏。先人辈上就是这么传下来的,没甚大惊小怪。
再说那爱串门子的吧,遇上这号天气,心里别提有多美。男女生来就有七情六欲,谁还没有个相好的。平日里你送个媚眼,我递个秋波,嘴上不说,心上精明着咧!去吧,保准!或者在家里,也许柴草房,反正是两人知道的地方,早就有人等着哩!每遇此情,十有八九,家的男人不是去赌博,就是吃喝“打平伙”。有些男人知道了,也是睁一眼闭一眼,“拔了萝卜眼眼在”,又不碍大事,自己用的多,别人用的少。人生稀里糊涂就那回事,何必过多的认真呢?两个人的小天地就是美,无拘无束、光溜溜、缠绵绵,哥呀、妹呀地浪上一阵子,那个亲热劲一点也不亚于七月七牛郎会织女。早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边城有三宝,皮毛,咸盐,甜甘草;又说,草绳拴牛牛不跑,沙子打墙墙不倒,嫖客跳墙狗不咬,女子嫁汉娘不恼。风刮得越大,才越好咧!屋里尽情的“哼咿”,而外面还有“呼呼”的风声助威,正乃别具一格。
老天爷才不管人间香火呢!这不,天已经黑了,还在使着性子地猛刮。
“真是个倒糟天!”石冲子妈暗骂着老天爷,拔下头上的卡子挑了挑麻油灯的捻子,灯“忽”的亮了一下,但随着阵阵风的呼啸声,灯头却在不停地跳跃着。她显得有些焦虑地望着窗外黑糊糊地天空傻愣着。冲子大已经出门四天了,咋还不见踪影?算日子也该回来了。这两天右眼皮在一个劲地跳,跳得人心神不宁。不会出事吧?她想着,更显得有些焦躁不安。
冲子才不管事呢,饭碗子一撂,就到他大叔陈老侃家听古朝(古代故事)去了。
陈老侃,四十来岁,一撮山羊胡子加一脑二道毛和一副架在鼻梁骨上的眼镜,一看就像个知书达理之人。他孑然一身,住在堡子西边的两间一套空的土平房里,过着一个人饱了全家不饥的日子。在平日里,白天人们各忙各的,到了晚上,不用招呼,三三两两的人便聚集在他的房里,听他谝古朝。《小八义》、《大八义》、《封神演义》、《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就连“水浒传”中梁山英雄排座次,谁在第几位,绰号是甚,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讲得头头是道,别人听得是津津有味,没法子,天生就是这份好记性。他不怎么劳动,凭着自己的底子,给东家的孩子教教三字经,也混几个好钱。晚上他讲古朝是种享受,别人听古朝更是一种享受,少不了这个提点肉,那个拿点酒,有吃有喝。虽膝下无妻儿,但一点也不孤单。方圆几十里,谁不晓得他陈老侃是个能人,谁家的牲口病了,他也能够瞧瞧,谁家的羊丢了,他会拨踪。就连婆姨养娃娃难产的事,他也上过手,还救过好几个母子的命呢。加之天文地理,阴阳八卦,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一提到陈老侃,人们准会竖起拇指称赞:“好人!”因为他不贪财,不心黑,用他的话说:“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活在世,名誉第一。”
至于他为甚一辈子不娶婆姨,确实还是个谜。
“打平伙”的碗筷还没有拾掇利落,就催促他接着讲昨天的故事。石冲子、姜骡子、王顺子、刘英子几个十五六岁的光葫芦小子更是催得厉害,这个说:“陈叔,我给你拿烟锅。”那个说:“陈大大,我给你倒酒”。
石冲子更灵醒,把刚打完“平伙”吃剩下的羊羔脑从热着的后锅里端了上来:“陈叔,还热乎着呢!”
“好!咱就开讲!”
陈老侃抹拉了一下那撮并不太长的山羊胡子,咳嗽了一声,清理了一下嗓子,又对着麻油灯头点着烟袋锅,呷了口“羔酒”,用长长的指甲抠了块羊羔脑肉,塞在嘴里,然后啧啧嘴,把遮在眼前的“二道毛”向脑后一甩,开讲起来:
“昨天说到闯王李自成进了北京,当了皇帝。作为常年征战沙场,马不卸鞍,身不离剑,又坐了江山的人来说,是该歇歇身子骨了。不免还有些飘飘然然。在宴请群臣时,他问众爱卿,人在世上干甚最好?众臣们面面相觑,不知闯王此番话究竟何意?真不好应答。闯王呵呵一笑言道:我说,过年最好。他为甚要说过年好呢?米脂人,穷怕了,从小吞糠咽菜,饥一顿,饱一顿,只有过年时,才能见点腥,或许吃顿饱饭,当然是过年好啦,那就天天过年!就这句话,瞎啦,本该四十一年的江山,只坐了四十一天。因为皇帝是金口玉言。”
陈老侃又呷了口酒,往嘴里塞了块肉。望了望横七竖八躺在炕上的、坐在地上的、听得聚精会神的人们,继续说:
“闯王手下有一位身经百战的大将,姓刘名宗敏,此人铁匠出身,有万夫不挡之勇,为闯王打天下可谓赤胆忠心,屡建奇功。你说就这么个人,天底下多少好女人不能爱,偏偏爱上个陈圆圆。别小看这个女人是名妓女,她可是镇守边关总兵吴三桂的老相好?”
“当,当,当!”
风仍没有停歇,但教堂的钟声还是传了出来。
这座天主教堂就在掌柜刘义首“福盛兴”货栈的隔壁,神父是个荷兰人,高高的个子,深深的眼窝,更衬托出他那高而大的鼻子。此人也不过三十大几,外国名叫沃洛夫,取了个中国名字叫沙智林,这里的人都习惯叫他“老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