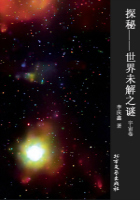其中所指虽然隐晦,但意思却很清晰,多指向秋瑾。在吕碧城眼中,秋瑾的“不让须眉”是自卑的,她对于男性近乎痴狂的模仿恰好反映出性别上的自卑。吕碧城认为,性别生来就有差异,男子的刚强是值得颂扬,女子的灵秀亦是一种美,无须争个高下。即便是今日,在男女差别这一点上,很多人依旧无法正视。而吕碧城一百年前就已明晰这个道理,实在是智慧。
虽说二人见解不一,却依旧相互尊重,算不上密友,却也维持着淡如水的君子之交。秋瑾远渡扶桑之后,吕碧城在《大公报》上刊登她的来信文章,也作《敬告中国女同胞》等文章。作为清末最有气概和风度的两位女子,吕碧城与秋瑾隔海相望,一文一武,谱奏出一曲末世女子传奇。秋瑾去日本之后便开始投身革命,回国之后发动起义,而后就义。她未能活到中华民国建立的那一日,实在是一大憾事。
吕碧城与秋瑾并未有过深入的交往,然而,她曾经在报上刊登过秋瑾的“反动”文章,这一点就足够让她下狱了。因此,秋瑾逝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吕碧城“亦为惊弓之鸟矣”。不过,对于这位女义士的胆识和气魄,吕碧城还是十分钦佩的。后来,她路过杭州西泠秋瑾墓之时,曾经有感而发,作诗悼念这位故交:
松篁交籁和鸣泉,合向仙源泛舸眠。负郭有山皆见寺,绕堤无水不生莲。残钟断鼓今何世,翠羽明珰又一天。尘劫未销惭后死,俊游愁过墓门前。
高处的孤独
秋瑾就义之后,“惊弓之鸟”吕碧城之所以能幸免于难,还多亏了袁世凯的保全。吕碧城曾经在袁世凯家中做家庭教师,深得袁世凯青睐。而“皇二子”袁克文更是对这位文采飞扬、貌若惊鸿的女子青眼有加,将她引为知己。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儿子,仪表俊逸,又颇有些才气,诗词戏曲收藏,四大皆通,也都有小成,对书法最为在行。他是与吕碧城唱和的雅士之一,文字场上一来二往,有些蓝颜红颜的意思。可是,吕碧城眼光何其老到,一早就看清他那些小才气下的贵公子做派,知他挥霍无度,风流成性。于是向友人评说,这位知己也不符合自己的择偶观,只是个在风月场里依红偎翠的主儿。
果不其然,袁克文有名分的妻妾五个,死后更有上千妓女为其送葬,其排场声势不亚于写“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柳三变了。而他先是入青帮,混了个大字辈,平日里拿着父亲的钱挥霍,挥霍完便了,虽说行事荒唐,可为人倒也磊落,平生事能写出一本流光溢彩曲折跌宕的小说了,不过这绝非是吕碧城的那杯茶。
吕碧城终身未嫁,绯闻却没少有过,先是提携她的英敛之,又是袁克文、费树蔚、李鸿章之子李经羲等人,都是名流,却无一入得她法眼。吕碧城曾扬言:“予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启超)早有妻室,汪季新(精卫)年岁较轻,汪荣宝(国会议员)尚不错,亦已有偶。”
如此口吻,也只有吕碧城敢说了。不过,这看似孤高的宣言,实际上就是吕碧城的心声。她对配偶的要求是文学水平,她曾经说:“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耳!”
吕碧城在词坛的地位很高,被推崇为“李清照后第一人”,而樊增祥对她的词作评价则是“漱玉犹当避席,断肠集勿论矣”。被词名掩盖的诗文虽然没那么有名,在当时却也佼佼。而她对白话文写作又向来持反对态度。如此自负和地位,几乎让她自绝前路。
另一方面,吕碧城向来宣言女权,对纳妾等行为十分不耻。光是这一点,恐怕她就将很多已婚男士和风流公子排除在外了。这个独身女子的爱情向来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可有趣的是,作为一位新女性,吕碧城却十分推崇包办婚姻,认为包办婚姻中父母会为子女考虑周详,可以促成踏实可靠的婚姻。
且不论少时被退婚的遭遇给吕碧城留下的阴影有多深重,只看她一生的成就就足以让很多男子退避三舍了,王熙凤的干练让贾琏找不到位置,李清照的才华令赵明诚找不到位置。在传统社会里,男尊女卑,因而女子无才便是德,吕碧城的“才”显得有些扎眼了。
对于那些与吕碧城唱和往来的才子们来说,欢场上逢场作戏不难,偶尔也要酝酿些情绪来装点文字。可待那墨迹凝涸,又有多少情意可以不退场?这世间,向来情比纸薄。
无论爱情是否曾经在他们身上上演过,吕碧城和英敛之之间一直都有着不得不说的故事。英敛之比吕碧城大十几岁,邂逅吕碧城之时,已经有了妻室。然而,二十岁的吕碧城,姿容曼妙,又气质逼人,一身才气更是令英敛之的妻子自惭形秽。那日,吕碧城走后,英氏在书桌边写字,还向英敛之提出要去北京读书。
而英敛之呢,他虽然明白自己所处的身份和境况,却也忍不住心猿意马,对这位才貌双全的女子生出爱慕之心。谁知,这种爱慕在今后的共事生涯中渐渐消磨了。倔强的吕碧城和固执的英敛之,一遇到分歧便各不让步,久而久之,也就渐行渐远。
其中最主要的分歧可能还是来源自不同的政见。英敛之是满人,一直主张君主立宪制,是革新派。他对清政府有着天真的同情和信任。而吕碧城的思想则比较尖锐,她早已看清清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因而政治主张也比较前卫。吕碧城曾经在《予之宗教观》中提及与秋瑾分歧,她解释道:“予持世界主义,同情于政体改革而无满汉之见。”对于秋瑾信奉的旧三民主义,她尚且觉得局限太大,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么,在她看来,英敛之的君主立宪之说自然更加迂旧陈腐。
此外,英敛之的见识比较守旧,反对女子着装艳丽,还在报上登文劝诫。这可直接触怒了吕碧城。她的服装打扮向来与人殊异,生活也比较奢侈。她曾经穿过孔雀装:头戴孔雀翎,衣裙类似西式,颜色渐变,到裙摆处幻化作五彩的雀屏。如此奇装,比张爱玲要早了几十年。女子本身就爱美,而吕碧城个性特立独行,又最推崇女性美,不认为穿得花哨就似妖似魔。英敛之在报上的谩骂劝诫,看似无关痛痒,却字字朝她掷来,怎能不令她盛怒?
之后,英敛之在日记中写:
“碧城因《大公报》白话,登有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段,疑为讥彼。旋有津报登有驳文,强词夺理,极为可笑。数日后,彼来信,洋洋千言分辩,予乃答书,亦千余言。此后遂不来馆。 ”
在此之前,吕碧城的二姐吕美荪因为北洋女子公学的事务来到天津,常常出现在英敛之的视野里。她的名声虽不如吕碧城那么响亮,却也十分出色了。当时有“淮南三吕,天下知名”之说,指的就是吕碧城和大姐吕惠如、二姐吕美荪。
吕美荪的到来,使得英敛之对吕碧城更加冷淡,他似乎找到一个更加温顺的对象去关怀怜爱。吕氏姐妹中,坤秀与惠如逝世较早,晚年独剩吕碧城与吕美荪还在人间。而吕碧城却与她,曾扬言“不到黄泉,勿相见也”。姊妹反目,多少有些是因为英敛之的缘故。
然而,吕美荪之后忽然嫁人,却未曾告诉过英敛之,他因此愤怒了好长一段时间。不过吕美荪终究不是吕碧城,不会一味地针锋相对,两人不久又重归于好。
除却这些私人间的恩恩怨怨,英敛之还是心平气和地欣赏吕碧城的才气,他编印《吕氏三姊妹集》,对这三姐妹都是赞扬有加。
英敛之对吕碧城有知遇之恩,是一手将她的名字推向全国乃至世界的良师兼益友。且不论他们之间是否曾经有过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情愫,英敛之都是吕碧城人生中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
素手先鞭著何处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光明的时刻,曾经在袁家担任家庭教师的吕碧城自然更不例外。一直以来,袁世凯都十分欣赏她的才干,吕碧城之所以能掌管北洋女子公学还多亏袁世凯的提拔。秋瑾死后,更是多亏了袁世凯的保全,她才能幸免于难。
因此,袁世凯要任命吕碧城为秘书的时候,她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对于满腔抱负的吕碧城来说,总统秘书这个职位就是最好的机会。
然而,担任总统秘书的三年里,吕碧城逐渐发现现实并不如预想中那么顺风顺水,袁世凯企图称帝的野心也逐渐暴露。1915年,袁世凯准备复辟,对政治心灰意冷的吕碧城辞职南下,定居上海。
这时候,她作过一首《浪淘沙》,以遣悲怀:
百二莽秦关,丽堞回旋,夕阳红处尽堪怜,素手先鞭著何处,如此山川。花月自娟娟,帘底灯边,春痕如梦梦如烟,往返人天何所住,如此华年。
吕碧城最终在青灯古佛前了结一生,是她毕生最大的谜。在一些观点中,人们往往以童年阴影、情感挫折等等来剖析她遁入空门的原因,我却不敢苟同。在大多数人眼中,无论吕碧城有多么大的成就和胆识,他们还是会以小女人的心态来揣度她的人生。
其实,我认为,在吕碧城的一生中,有一样东西要比爱情更值得揣摩,那就是她的抱负,她做事的立足点很高。如张爱玲那般,爱恨都无关他人,烽烟四起也不过是为了倾城一恋。在她那儿,一切最宏大的东西都可以变得渺小而无所谓,私人到极致,而吕碧城则全然是另一个极端,从最初《大公报》发出的那一声“问何人女权高唱”的呐喊,她的一生就不再只是为生计疲于奔命,或是在情爱场上卿卿我我,她把自己给了那些宏愿,可这时运并未给她放手一搏的机会。
那天,当她从新华宫中缓缓走出的时候,步履应该沉重如灌铅吧。因此,才会有“素手先鞭著何处”,“往返人天何所住”的无奈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