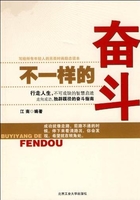文/郑晓欣
周道香医生为我做眼角膜移植,他们把我眼部的神经麻醉了,可是我神志清醒,能听到金属器具的丁当声和周医生的说话声。
我的右眼发炎红肿,三年多了,军中医官说我患的是角膜炎。最后我到台北三军总医院去求诊,那时我的右眼已经看不见东西了,而我的左眼又视力极差。
医生说:“可能你是用了脏毛巾或在游泳池里游泳感染的。”
我说:“很可能就是这么得的病。”
一年后,我听说角膜移植可以使得失明的右眼复明。我把这消息告诉妻,她听后,脸绷得紧紧的,想了好久,找出她多年来积蓄的新台币两万元的存款交给我。
“两万元不够的话,再另想办法,”她说,“你不像我,大字不识一个的睁眼的瞎子。一只眼看书写字不方便。”
周医生是台湾最早做角膜移植的医生之一。我马上去登记,等候移植。不到一个月,他打电话来说:“一位司机在车祸中受了重伤,临死前对他太太说,身体的器官能卖掉就卖掉,得点钱抚养他们六个未成年的孩子。出一万块钱可以吗?”
手术费、医药费和住院费顶多不超过八千。我答应了,医生叫我第二天就入院。
我的运气很好,许多人要等好几年才能等到个角膜。我感激妻给我的资助与鼓动。
我刚被推出手术室,女儿小蓉在我耳畔说:“很顺利。妈本想来看您,怕您……”
“去跟她讲,我不要她来。告诉她我很好,叫妈安心就行了。”
我以前住在三军总医院时,妻从未来过,而且我也不要她来。
和妻结婚那年,我刚刚十九岁,是奉父母之命结婚的。父亲和岳父是世交,二人指腹为婚。
婚前我根本就没有见过妻的面。等到把她从花轿里拖出来拜了天地,进了洞房,我才用秤杆子挑下她的红盖头,认清她的面貌。
我没法形容当时的心情。她整个脸都是坑坑洼洼的疤,鼻尖上还有一条条的肉柱,眼皮上一块块反光的疤痕,显得眼眶浮肿,眉毛稀疏。才十九岁,看起来像四十多。
我跑到母亲房里,哭了一夜。母亲劝我认命,并说丑妇有福,红颜命薄。不管母亲说什么,也解除不了我内心的痛苦。我不肯和妻同房,也不跟她说话。我在学校里寄宿,到了暑假也没回家,后来还是父亲派一位堂兄把我连劝带训地拖回去住了两天。
到家时,妻正在煮晚饭,抬起头朝我微微翘翘口角表示欢迎的意思,但我连忙别过头,直向母亲房里走去,就像没见到一样。饭后,母亲把我叫到她房里说:“孩子,你太任性了。你媳妇外表是丑了点,可是她的心并不丑。”
“美,美,美得像天仙!”我愤怒地说,“不然你会娶她做儿媳妇?”
母亲气得面色发白,说:“她实在是个好媳妇,知情达理。到我们家六个多月了,从早到晚,从锅上上到磨房,我和你爹吃的穿的都是她一个招呼。你这么样对待她,她一句怨言都没有,也没见过她掉眼泪。不过,你懂不懂,她的眼泪是往肚子里流的。”
母亲又说:“人,怎么都是一辈子。只要她把你侍候得好,能照料家务,好好抚养孩子就够了。难道能叫人家守一辈子活寡?拿人心比自心,别人对你这个样子,你是不是受得了?”
之后,我和妻子同房了,可是心里总有说不出的别扭。她老是低着头,低声下气地说话。有时我顶上几句,她都向我尴尬一笑,再低下头去。她像一团棉花一样,没自己的意见,也没有脾气。
结婚三十多年,我绝少给她过笑脸,也没跟她在大街上走过路。数不清多少次,我偷偷地咒她死。
也许正因她面貌极端丑陋,妻有一般人所缺乏的耐心和爱心。初来台湾的几年,我在军中阶级低,收入只够温饱,孩子又多病,还要应付医药费。妻一面照顾两个孩子,一面做家庭副业。住中部海边,她编织草帽草蓆;搬到东部渔港,她给渔民织网补网;住在北部的时候,她又学会在陶瓷用具上画花草鸟兽。我回家的日子也少,不论孩子的教育或家庭费用,我从未问,当然更不用操心了。
我们从没住过眷村,一方面是我怕别人见到妻,她也怕见同事长官们的眷属。我从陆军退役后,迁居在一幢偏僻而简陋的房子里。现在女儿小蓉已从大学毕业,并已教了一年书。她弟弟比她小三岁,在官校成绩很好。现在正是他考试最紧张的关头,我叮嘱小蓉不要让他晓得我要施手术,免得他分心。
小蓉为我送来了一架晶体收音机,但我住医院以后,常回想过去的事,动辄就要想到妻。我后悔拒绝她来探我,老都老了,子女都长大成人,还继续挑剔什么?
两星期后我知道快要拆线了,心里着实有说不出的高兴。我想,失去自由的人重获自由,大概就是这种心情吧。我告诉小蓉说:“等我出了院,一定要到给我眼角膜那人的坟上去祭奠一回。”
可是我也很担忧,因为我知道角膜移植的成功率不能达到百分之百。医生除去我右眼的纱布,我简直不敢睁开眼睛。
“看得见光吗?”周医生问。
我眨眨眼道:“上面很多亮。”
“那是手术灯,”医生拍拍我的肩,愉快地说,“朋友,成功了。一星期后就可以出院了。”
这一星期,一天比一天有起色,换药的时候,周医生都要检查一次。出院那天,窗户、病床,连桌上的茶杯都看到了。
小蓉来接我出院。“妈中午准备好几样您喜欢吃的菜。”
“她是好妻子,好母亲。”我说出了蕴藏在心底多年未曾说出口的一句良心话。
我和小蓉招了一辆计程车。路上,她始终闭着嘴闷不吭声。
回到别了二十一日的家,妻正端着盘菜从厨房出来。她一看见我,猛然怔住,赶忙垂下头,畏畏缩缩地说:“回来啦?”
“谢谢你赐予我光明。”我第一次向她说这样话。
她歪着头,从我身边擦过。盘子放在饭桌上,人背着我,双手扶着墙壁,嘤嘤地哭泣着。“有你这句话,也就够了,我死也够了。”
小蓉从外面跑进来,哭唧唧地叫喊:“妈,快告诉爸,让爸知道他右眼换上的是你的角膜!”小蓉摇着妻的肩,“快说呀!”
妻止住哭泣说:“这是应……应该的。”
我抓住她的双肩,仔细看她的脸,妻的左眼珠变成灰白色,跟我以前的右眼一样。
“金花!”我第一次叫出妻的名字,“为什么……为什么这样?”我狂喊,用力摇着她。
“因为……你是我的丈夫。”说罢,她扑在我的怀中。我紧抱着她,然后我在她面前跪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