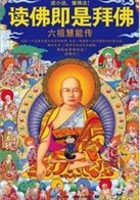弥留之际,他对妻子说:“我死之后,你一定要接替我每天去吃一碗馄饨。这是我们队12个兄弟的约定,自己的兄弟死了,他的老婆孩子,咱们不帮谁帮。”从此以后每天的早晨,在众多吃馄饨的人群中,又多了一位女人的身影。来去匆匆的人流不断,而时光变幻之间唯一不变的是不多不少的12个人。
时光飞逝,当年矿工的儿子长大成人。而他饱经苦难的母亲两鬓斑白,却依然用真诚的微笑面对着每一个前来吃馄饨的人。那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与善良。
更重要的是,前来光临馄饨摊儿的人,尽管年轻的代替了年老的,女人代替了男人,但从未少过12个人。穿透十几年岁月沧桑,依然闪亮的是12颗金灿灿的爱心。
行善不在于勉强为之,它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有时,行善因其不为人知而更加幸福。
一年轻小伙吹着口哨,从一片草地走过。他看到道旁的木椅上坐着一个女孩。阳光很好,青草如诗,而女孩的眼里却满是愁苦和忧郁。小伙随手采了一只狗尾草,微笑着送给女孩,而后吹着快乐的口哨,慢慢地走远。
一个雾蒙蒙的清晨,洒水车司机发现了一位衣衫褴褛的小男孩一直尾随其后,一条街,又一条街。司机终于忍不住好奇,停车问询。原来小男孩是个孤儿,今天是他生日,而洒水车放出的音乐,正是那首《祝你生日快乐》。司机得知原委,双眼潮热,邀请小男孩坐在驾驶室。那个清晨,整个城市便弥漫着温馨的生日歌。
大戏剧家莎士比亚说过,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像甘露一样从天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给予的人。所以,行善是一种幸福。当和尚出门化缘的时候,总是一家一家地敲门,其实这也是在提醒人们,时刻不要忘了做善事。
知人识人,更要学会去爱人
做人难得的是知人、识人,但最重要的是应该爱人。这才是重中之重!
单纯能够认准面前的人还不够,还要做到爱人,才能帮助迷途的人改正错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朝阳升起之前,庙前山门外凝满露珠的春草里跪着一个人:“师父, 请原谅我。”
他是某城风流浪子,20年前曾是庙里的小沙弥, 极得方丈宠爱。方丈将毕生所学全数教授,希望他能成为出色的佛门弟子。他却在一夜之间动了凡心,偷下山去,五光十色的城市迷住了他的眼目,他从此花柳街巷,只管放浪形骸。
夜夜都是春,却夜夜都不是春。20年后的一个深夜,他陡然惊醒,窗外月色如洗,澄明清澈地洒在他的掌心。他忽然深自忏悔,披衣而起,快马加鞭,赶往寺里。
“师父,你肯饶恕我,再收我做弟子吗?”他急切地询问。
方丈深深厌恶他的放荡,只是摇头:“不,你罪过深重,必坠阿鼻地狱, 要请佛祖饶恕,除非——”方丈信手一指供桌,“连桌子也会开花。”听方丈这么说,浪子失望地离去了。
第二天早上,方丈踏进佛堂的时候,惊呆了:一夜之间,佛桌上开满了大簇大簇的花朵,红的白的,每一朵都芳香逼人,佛堂里一丝风也没有。那些盛开的花朵却簌簌急摇,仿佛是焦灼的召唤。方丈瞬间大彻大悟。他连忙下山寻找浪子,却来不及了,心灰意冷的浪子重又坠入他原本的荒唐生活。而佛桌上开出的那些花儿,只开放了短短的一天。
是夜,方丈圆寂,临终遗言:“这世上,没有什么歧途不可以回头,没有什么错误不可以改正,一个真正向善的念头是最罕见的奇迹,好像佛桌上开出的花朵。”
而让奇迹陨落的,不是错误,是一颗冰冷的、不肯原谅的,不肯爱的心。
在“义”的前提下追求自己应得的“利”
君子重义,小人重利。
义与利是对立的统一,有一定的界限。利与害也是对立的统一,经常相互转化。专意求利,却常常得害;唯有专意遵义而行,才能免除祸害。“出利入害,人用不生。”人离开物质利益就要陷入危害境地,不能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因此,君子也不可不食人间烟火,有时也要“喻于利”。
由此,想到一个地方。义乌古称乌伤,此名的由来缘于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相传,有一个叫颜乌的孝子,虽然出身贫寒,却深知礼义,孝敬长辈。有一年,与颜乌相依为命的父亲病故了,他无钱办丧事,只得独自筑坟安葬父亲。他日里负土堆垒,晚上通宵守坟,一群乌鸦看见这般情景,深为感动,纷纷衔土相助。坟终于筑好了,可是乌鸦的嘴巴也全都啄伤了。从此,这个故事就四处传扬开去,秦始皇时定名为乌伤县,唐时改称义乌。
义乌自古多商,追求利益可以说是商人的基本特征,作为商人,总是以最高的经济效益为目标,把获得最大的利润作为自己最大的追求,义乌商人也不例外。然而,义乌商人除了重利,同样重义。在生意场上,义乌商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先让进货者赚钱,因为只有等进货人赚到了钱,他才会回过头来继续买你的货,进而让你赚更多的钱,即所谓的“利滚利”。诚信经营,逐利的同时不忘道义,才会有持久的发展。因此,“喻于利”没有错,错的只是争名夺利的手段。
义与利是密切统一的,义中含利,而利中显义,如果简单地将义与利作为君子与小人的划分标准,实际上是把义与利二者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怂恿人们去追求一种虚幻的道德满足感。
有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一生从不与人争利,包括自己应得的利益。在这个俗世中,他像野草一样活了一生,慢慢老了,最后死了。他来到了天堂,发现天堂的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所有人都你挤我拥,想早点进入天堂的大门。
他想,他不能和人争,不然会有麻烦的。于是,他一个人排到了队伍的最后面。前面不断有人插队,为此许多人混战成一团,然后妥协,队伍又恢复了平静。他不敢插队,连这样的念头也没有。还有人不断向他请求,能不能把位置让给他们,他答应了,于是又站到了队伍的最后面。他在这里有很好的名声,所有新来的人,都会让他把他的位置让给他们。他永远都排在队伍的最后面,这样过了几个世纪,他还没有进入天堂。他慢慢有些不耐烦了,但他从来不敢和人说,更别说生气了。所有人都说他的脾气好,然后像在人间一样,开始把取笑他作为一种游戏。
终于他遇上一位天使,他壮着胆子问:“天使啊,我在这里站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进入天堂?”天使把他的情况告诉了上帝。上帝说:“你说的是那个永远排在队伍最后面的人吗?让他下地狱吧!”
天使把上帝的话告诉了他,他终于愤怒了。
他去质问上帝:“上帝啊,你不是把天堂留给那些温良、仁慈、有道义的人吗?”上帝说:“是的,但是如果你连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都不愿去争取,那么地狱最适合你了!”
有时,一味放弃自己应得的“利”,处处宽忍退让,只会助长小人的贪婪。鲁迅先生曾说:“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所以说,在“义”的前提下追求自己应得的“利”是正常且正当的,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也!
成功做人,走外圆内方的路
做人要讲分寸,不能剑走偏锋。做官也和做人一样,做人不要太走极端,不能表现得过于“特立独行”。做任何事都要合乎“礼仪”、有合适的言行举止,否则会害了自己。
这样看来我们明白了,这和孔子一向主张的“中庸”思想比较一致。不过时下一些年轻人可不这样想,他们最喜欢谈的就是张扬个性。他们最喜欢引用的格言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如今的种种媒体,包括图书、杂志、电视等也都在宣扬个性的重要性。曾几何时,个性已经成为独特、怪异的代名词,过度张扬的个性在不知不觉间伤害了别人,更毁灭了自己的前途。
人活着确实该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不过如果为了个性而个性那就得不偿失了。如果你显示出自己要逆潮流而行,神气活现地炫耀你反传统的观念和怪异的行为方式,那么,人们会认为你只是想哗众取宠,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他们还会因此而轻视你。他们会找出一种办法惩罚你,因为你让他们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不如你。过分“特立独行”是危险的,不妨让自己的行为与别人差不多,你就不会受到太多的阻力。
《庄子》中有一段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只特立独行的猕猴,它非常喜欢表现自己,处处都要显得与众不同。
有一日,吴王乘船在长江中游玩,登上猕猴山。原来聚在一起戏耍的猕猴,看到吴王前呼后拥地来了,立即一哄而散,躲到森林与荆棘丛中去了。
但这只“特别”的猕猴,想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它在地上得意地旋转,旋转够了,又纵身到树上,攀缘腾荡。吴王看了不舒服,就展弓搭箭射它,它从容地拨开射来的利箭,又敏捷地把箭接住。它并不清楚,这种炫耀对掌握天下生杀大权的君王是种侮辱,吴王脸都气红了,命令左右一齐动手,箭如风卷,猕猴无可逃脱,立即被射死。
吴王回头对他的友人说,这灵猴夸耀自己的聪明,倚仗自己的敏捷傲视本王,以致丢了性命,这完全是它咎由自取。可悲的猕猴过于迷恋出头冒尖的感觉,一味张扬,表现自我,浑然不觉自己的行为是多么怪异、幼稚。它的目的达到了,它的确引起了所有人甚至一位君王的注意,可惜这种注意带来的是负面看法和评价。这只猕猴成了众人反感、厌恶的对象。
“与众不同”造成了它的命运悲剧,这不得不使我们引以为戒。
俗话说得好,“出头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以卖弄、炫耀为爱好的人必将品尝自酿的苦果。这就是孔子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现代意义。“烦恼皆由强出头”,这个“强”,一指“勉强”,也就是说自己的能力还不够,却勉强去做某些事,固然有可能获得意外的成功,但这可能性实在太低,结果不但失败了,还会招来嘲笑和白眼。“强”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指你的能力虽强,但外部环境、条件尚未成熟,“大势”不和,机会不来,此时出头,必将遭到别人的排挤和打压,仇恨的种子从此栽下,冤冤相报却又何苦来哉?你我本一般,为何独露脸?纵有千般术,难躲暗中箭……
成功做人是要“外圆内方”,而不是为了表面的“个性”,肤浅地表演自己的不随潮流,这样只会让自己吃尽苦头。为逞一时之快而不顾后果真是个危险游戏。
最难揣摩是人心
人心难测。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的心犹如海底针,很难揣测。
有人曾经以为鹤顶红、砒霜是世界上最毒的东西,但是其实不是,世界上最歹毒的莫过于人心。一个念头能使人上天堂,一个想法也能让人下地狱。最毒是人心,最善也是人心,最难把握的还是人心。有时候,你最亲近的人的心你也未必能了解。历史上的父子兄弟之间有很多反目成仇的,为了权威与地位,抑或是金钱大打出手,完全不顾及亲情与道义。从本质上来说金钱与权力并不是坏东西,而是有人因为它们上演一幕幕丑剧的时候,人们才觉得它们太坏了。
帝王在选择太子时心理是很矛盾的。太子仁弱一点吧,怕将来继位后缺乏驾驭众人的能力;太子贤明一点吧,又怕众望所归会危及自己。宋太宗见到自己的太子颇得人心,就曾酸溜溜地说:“人心都归向太子,欲置我于何地?”皇帝既有这种心态,太子委实难处。不能不得人心,也不能太得人心;不能太不及父皇,也不能太胜过父皇,这中间的尺寸确实是很难把握的。
隋炀帝的儿子杨柬就因为把握不好这个度,而与父皇产生隔阂。造成他们父子失和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为了一个美女。有一次,乐平公主告诉炀帝,有个女子十分漂亮,但不知为什么炀帝听后无所表示。过了一段时间,乐平公主以为炀帝对此人不感兴趣,就把她推荐给了太子杨柬。杨柬马上把她纳入后宫。后来炀帝忽然记起这事,就问乐平公主:“你上次说过的那个美人现在哪里?”乐平公主回答说:“已经被太子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