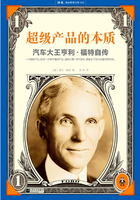◆文/赵丽宏
在黄昏的微光里,有那清晨的鸟儿来到了我的沉默的鸟巢里。
我喜欢泰戈尔的诗。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泰戈尔就把我迷住了,一本薄薄的《飞鸟集》,竟被我纤嫩的手指翻得稀烂。那些充满着光彩和幻想的诗句,曾多少次拨动我少年的心弦……
《飞鸟集》破损了,我渴望再得到一本。然而,“文化革命”一开始,这个小小的愿望,竟成了梦想。我的那本破烂的《飞鸟集》,也被人拿去投入街头烧书的熊熊烈火中,暗红色的灰烬在火光里飞舞,飘飘洒洒,纷纷扬扬。我仿佛看见老态龙钟的泰戈尔在火光里站着,烈火烧红了他的白发,烧红了他的银须,也烧红了他的朴素的白袍。他用他那冷峻而又安详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看着,看着,他的神色变了,似有几许惊恐,几许不安,也有几许愤怒,几许嘲讽……
我还是喜欢泰戈尔。在动乱的岁月里,我默默地背诵着他的诗,以求得几分心灵的安宁。“诗人的风,正出经海洋和森林,求它自己的歌声。”我陶醉在他所描绘的大自然中了——那宁静而又浮躁的海洋,那广袤而又多变的天空,那温暖而又清澈的湖泊,那葱郁而又古老的森林……
有一天,我忽然异想天开了:到旧书店去走走,看能不能找到几本好书。结果,当然叫人失望。但,我发现,有时还会有几本“罪当火烧”的书出现在书架上,或许,这是出于店员的粗心吧。于是,我抱着几分侥幸,三天两头往旧书店跑。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又走进冷冷清清的旧书店。我的目光,久久地在一排排大红的书脊中扫动,突然,我的眼睛发亮了:一条翠绿色的书脊,赫然跻身在一片红色之间,呵,竟是《飞鸟集》!
该不会有另一种《飞鸟集》吧?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一看,果真有泰戈尔的名字。随即,我又紧张了,是的,这年头,得而复失的太多了。挤压着《飞鸟集》的一片红色,又使我想起街头那一堆堆焚书的烈火,那漫天飞扬的纸灰……我赶紧向书架伸出手去。
几乎是同时,旁边也伸出一只手来,两只手,都紧紧地捏住了《飞鸟集》。这是一只瘦小白皙的手,一只小姑娘的手。我转过脸来,正迎上两道清亮的目光——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小姑娘站在我身旁,抬起脸看着我,白圆的脸上,一双清秀的眼睛眨巴眨巴地闪动着,像一潭清澈见底的泉水,微波起伏,平静中略带点惊讶。
我愣住了,手捏着书脊,不知如何是好。还是她开了口:“你也要它吗?那就给你吧。”声音,清脆得像小鸟在唱歌。
我的脑海里忽然旋起个念头:在这样的时候,她还会喜欢泰戈尔?莫非,她根本不知道这是怎样一本书?于是,我轻轻问道:“你知道,这是谁的书?”
“谁的书!”小姑娘抬起头来,颇有些惊奇地看着我,秀美的眼睛睁得滚圆,转而,开心地笑起来,一边笑,一边做了个鬼脸:“这是一个老爷爷的书,一个满脸白胡子的印度老爷爷。我喜欢他。”说罢,用手做着捋胡子的样子,又格格地笑了。如同平静的池塘里投进了一颗石子,笑声,在静静的店堂里荡漾……
啊,还真是个熟悉泰戈尔的!我多么想和她谈谈泰戈尔,谈谈我所喜欢的那些作家,谈谈几乎已被人们遗忘了的世界呵!然而,这样的年头,这样的场合,这样的谈话肯定是不合时宜的,即便年轻,我还是懂得这一点。小姑娘见我呆呆地不吭声,刷地一下把《飞鸟集》从书架上抽下来,塞到我手中:“给你吧,我家里还藏着一本呢!”没等我作出任何反应,她已经转身去了。我只看见她的背影:一件淡紫色的衬衫,上面开满了白色的小花;两根垂到腰间的长辫,随着她轻快的脚步摆动……
她走了,像一缕轻盈的风,像一阵清凉的雨,像一曲优美的歌……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旧书店里的那次邂逅,留给我的印象竟是那么强烈。真的,生活中有些偶然发生的事情,有时会深深地刻进记忆中,永远也忘记不了。我不知道那个小姑娘的名字,甚至没有看仔细她的容貌。但,她从此却常常地闯到我的记忆中来了。当我看着那些在街头吸烟,无聊,踯躅的青年,心头忧郁发闷的时候,当我读着那些大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奇文,两眼茫然迷离的时候,她,就会悄悄地站到我的面前,眨着一对明亮的眼睛,莞尔一笑,把一本《飞鸟集》塞到我手中,然后,是那唱歌一般悦耳的声音:“这是一个老爷爷的书,给你吧,我家里还藏着一本呢!”……
她使我惶乱的思想得到一丝欣慰,她使我空虚的心灵得到几分充实。她使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青年人都忘记了世界,抛弃了前人创造的文化,抛弃了那些属于全体人类的美的事物!
有时,我真想再见到这位小姑娘,可是,偌大一个城市,哪里找得到她呢?有时,我却又怕见到她,因为,在这些岁月里,有多少纯真的青年人变了,变得世故,变得粗俗,就像炎夏久旱之后的秧苗,失去了水灵灵的翠绿,萎缩了,枯黄了。我怕再见到她以后,便会永远丢失那段美好的回忆。
一次,我在街上走着,迎面过来几个时髦的姑娘,飘拂潇洒的波浪长发,色调浓艳的喇叭裤子,高跟鞋踏得笃笃作响,香脂味随着轻风飘漾。她们指手画脚大声谈笑着,毫无顾忌,似乎故意招摇过市引得路人纷纷投去惊奇的目光,目光之中,不无鄙视。对那些衣着打扮,我倒并没有多少反感,只是她们的神态……
我忽然发现,这中间有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呵,难道是她?是那个在书店遇见的姑娘!真有点像呀!我的心不禁一阵抽搐。我迎上去,想打招呼,她却根本不认识我,连看都不看一眼,勾着女伴的颈脖,嬉笑着从我身边走过去。哦,不是她,但愿不是她!我默默地安慰着自己,呆立在路边,闭上了眼睛……
是的,这决不会是她。然而,这件小事却给我心头重重一击。工作之余,我又打开泰戈尔的诗集。泰戈尔,这位异国的诗人,毕竟离我们遥远了,他怎么能回答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疑虑和苦恼呢!他的一些含着神秘色彩的诗句,竟使我增添许多莫名的忧愁和烦闷。“有些看不见的手指,如懒懒的微风似的,正在我的心上,奏着潺谖的乐声”。呵,“我知道我的忧伤,会伸展开它的红玫瑰叶子,把心开向太阳”!
冬天的小鸟啾啁着,要飞向何方?
历尽了一场肃杀的寒冷,春天来了。经过冰雪的煎熬,经过风暴的洗礼,多少年轻的心灵复苏了,他们告别了愚昧,告别了忧郁,告别了轻狂,向光明的未来迈开了脚步。就像泥土里的种子,悄悄地萌发出水灵灵的嫩芽,使劲顶出地面,在春风春雨里舒展开青翠的枝叶……
恍若梦境,我竟考上了大学。去报到之前,我清理着我的小小的书库,找几本心爱的书随身带着,第一本,就想到了《飞鸟集》。呵,她在哪里呢?那个许多年前在书店里遇见的小姑娘!此刻,即使她站到我面前,我大概也不会认识她了,可是,我多么想知道,她在哪里……
人流,长长不断的人流,浩浩荡荡涌向校门。我随着报到的人群,慢慢地向前走着,不知怎的,我仿佛有一种预感——在这重进校门的队伍中,会遇见她。于是,我频频四顾,在人群中寻找着。
一次又一次,我似乎见到了她——她背着书包走过来了,脚步,已不似当年轻盈,却稳重了,坚定了;身上,还是那一件淡紫色的衬衫,上面开满了白色的小花;两根垂到腰间的长辫,轻轻地晃动着……
这不过是幻觉而已,我找不到她。在这支源源不绝的人流里,有那么多的小伙,那么多的姑娘,哪有这样巧的事情呢。可是,我的心头还是涌起了几分惆怅,眼前,仿佛又掠过几年前在街头见到的那一幕……
有人撞到我的脚跟上,我一下子从沉思中惊醒。身边,是笑声,是歌声,是脚步声。我不禁哑然失笑了,脑海中,突然跳出几行不知是谁写的诗句来:
你呀,你呀,何必那么傻,
经过一场风寒,就以为万物肃杀……
闻一闻风儿中春的芳馨吧,
生活,总要向美好转化!
我抬起头来,幽蓝的天空,辽远而又纯净——这是春天的晴空呵!一群又一群鸟儿从远方来了,它们欢叫着,抖动着翅膀,划过透明的青天,飞呵,飞呵,飞……
这篇散文写于1980年,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思想开始解放,万物复苏萌生;作者便是描写了那个特殊的年代——从“十年文革”到新一时期开始,积极进取的青年对自由汲取知识的向往、渴求及其理想的实现,表现了作者在对美(小姑娘是这种美的代表)的追求过程中的欢愉、痛惜、焦渴、欣慰和希望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