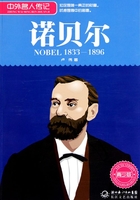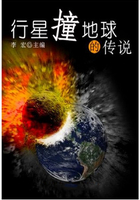“要是没有人搬弄是非,主公是不会作此决断的。”田穰苴说。
“田穰苴。”梁邱据挺了挺腰杆儿,幸灾乐祸地说,“别再用大司马的口气跟我说话,你现在什么也不是了,你可以回家安享天年了!”
“哼,小人得势。”田穰苴轻蔑地说,之后慨叹道:“大齐纲纪不振,全坏在你们这般鬼魅的手里。”
“田先生,这些话就不必说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说是吧?”梁邱据戏谑地说。
田穰苴把将印和佩剑放在中央的案桌上,一转身,愤然走出宫去。
“来人!”梁邱据吼道,“把太祝捆起来!”
几个侍卫上前,将虞如五花大绑。
“哈哈哈哈……”虞如放声大笑。
“你笑什么?”梁邱据问。
“我笑梁大夫太愚蠢。”虞如说。
“笑别人愚蠢的,一定是聪明人。”梁邱据说,“可惜呀,聪明人还是死在愚蠢人的刀下了,你说是不是?”
“这一刀下去,你可是把自己全卖了!”虞如笑道。
“怎么讲?”梁邱据问。
“你杀得了我,你能杀得了田穰苴吗?”虞如反问道。
“他现在已经是废人了,何必要杀他?”裔款插了一句。
“我与田穰苴同车而来,能不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吗?”
梁邱据与裔款顿时愣住了。
“所以呀,我现在提醒二位,杀了我之后,也把田穰苴杀了,这样才能彻底灭口。”虞如说,“不然的话,我的脑袋一掉,田穰苴就会把二位的狼心狗肠全都掏出来,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梁邱据与裔款面面相觑,惊恐万状。
正在这时,晏婴走了进来。他没跟梁邱据和裔款打招呼,却对侍卫们说:“把太祝大人放了。”
声音不高,却很有威势,侍卫立即上前为虞如松了绑。
晏婴径直进了内朝,此时齐景公又吃过一服药,感觉好些了。
“听说主公要杀太祝?”晏婴单刀直入地问道。
“虞如祭祷上天用心不诚。”齐景公答道。
“何以见得?”
“他每次祭祀上天时,都只是双膝跪地,口中却不发一言。”
“倘若让臣做太祝,也会像他那样,一言不发的。”
齐景公惊讶地看着晏婴,问:“为什么?”
“太祝对上天说话,是否要诚实?”晏婴反问道。
“当然要诚实。”
“这就难了!”
齐景公又是一惊,问:“难在何处?”
“主公的种种失误,臣已经说过多次,今天就不必重复了。”晏婴说,“人要乞求上天的护佑,就必须有善德。太祝的职责就是把主公的善德上达天庭,然而,当主公无善德可说的时候,太祝偏要去说,这就是欺瞒上天,而欺瞒上天是罪不可赦的;太祝要是把主公的种种失误如实地报知给上天,上天必不护佑主公,那样太祝也就对不起主公了。不说实话不行,说实话也不行。因此,在主公的手下,做一名太祝就太难了,他只能一言不发!”
晏婴的一席话,使齐景公豁然开朗,说道:“贤相说的,句句在理,都是寡人一时糊涂,只是……”
“主公放心,臣已经吩咐侍卫替虞如松绑了。”晏婴说。
“这就好,这就好。”齐景公喃喃地说。
“臣还听说,主公免了田穰苴的大司马职务?”晏婴又问。
齐景公怒气未消,就把梁、裔二人指责田穰苴的话重复了一遍。
晏婴刚要开口劝说,梁邱据就引着北郭启进来了。梁邱据启奏道:“臣奉主公之命,已将将印交与北郭启。”
北郭启跪地拱手,说道:“微臣北郭启前来领命谢恩。”
晏婴倒抽了一口凉气,全身木然。
原来梁邱据见晏婴进宫,害怕齐景公变卦,便火速派人将北郭唤来领命谢恩。他成功了,生米煮成熟饭,谁也无法更改。
庠序北面的场院,散了学的孩子们又聚集在这里。
“今天我们再玩点新花样。”孙武说,“咱们一共是二十六个人,分成两队,每队十三人。甲队是潜伏队,乙队是搜捕队,甲队潜伏在北边这座小山的丛林里,乙队前往搜捕,每人拿三个石粉袋,三个石粉袋都扔出去,手中就算没有武器了,就必须退出搜捕行动。乙队如果用石粉袋击中甲队中的七个人,就算赢了,不到七个人,就算输;反之,如果甲队中有三个人安全地从丛林跑回到这个场院,也算赢了。”
孩子们仍然用抽取长短树枝来分队,结果是孙武为甲队,田盘为乙队,两人分别被推为伍长。
孙武带领甲队消失在丛林里,各自找了隐蔽的地方藏身。孙武附在缪无忌耳边低语了几句,两人便分开了。
“好了。”孙武喊了一声。
乙队立刻进入丛林,蹑手蹑脚地搜索着……
孙武爬到了丛林边缘的一棵树上,等乙队的人刚过去,就悄悄地从树上下来,从容地跑回了场院,然后回过头来,笑着向丛林望去。
一个甲队学生垂头丧气地从丛林里走了出来,他的胸前挂着一个鸡蛋大小的白印。
远方响起了隆隆的雷声,但没有人在意。
缪不识蹲在一个长满了草的小坑里,看见有四只脚在他眼前转来转去,便把身子使劲缩紧,屏住了呼吸,过了一阵,四只脚的脚尖都转向外边,他急忙把准备好的一块石头向侧面抛了出去,“咚”地一声,那四只脚立即朝响声的位置跑了过去。缪不识“腾”地窜了出来,飞快地向山下跑去,在他身后,石粉袋一个接一个地抛了过来。但狡猾的缪不识跑的是“之”字形路线,因此石粉袋都被他躲过了。
“好好好。”孙武高兴地对缪不识说,“再有~个人安全下山,我们队就赢了。”
“将军,你说这种游戏甲队难还是乙队难?”缪不识问。
“各有难处。”孙武说,“按说,潜伏的一方是被动的,要难一些;而搜捕的一方是主动的,要容易些。但咱们却占了主动,原因在于计谋。我在丛林的最边缘处,他们都意想不到,这是一;我让你明目张胆地向山下跑,是为了浪费他们的石粉袋,即使他们打中了你也值得,刚才我看见,为了打你,他们扔出了九个石粉袋,亏大了。”
“要是你来带领乙队,你会怎么办?”缪不识又问。
“我会在场院附近安排一个人,谁从山上跑下来,就凑近了打,万无一失!”孙武说。
“将军,你的点子就是多!”缪不识佩服不已。
又一个甲队学生走下山来,他的白印是在腿上;接着便是第三个,他的白印竟然在左眼上,几个人看见以后,都朝着他哈哈大笑不止……
雷声更响了,乌云遮住了东半边天空。
“要下雨了。”孙武说,“把他们都喊下来吧!”
“不吃紧,别喊,我们快赢了!”缪不识制止道。
丛林里,乙队仍然在蹑手蹑脚地搜寻着……
田盘搜到了山顶,忽然发现绕树三匝的一根藤条被拉得很直,他顺着藤条看去,藤条延伸到山顶的背面,他知道,那里是悬崖,一定有人抓住藤条藏在后面。这个人真会找地方,藏在这里,是任何人都发现不了的。是谁呢?他横着走了几步,趴在地上,左手抓住一团茅草,然后从悬崖处探出头去,看见了那人垂下去的丝绸腰带,绿色的,一阵风吹来,他看见了腰带的另一面,绣着红色的桃花纹。
梁有稷!田盘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他慢慢地爬起身,环顾左右,周围没有人。他深深地喘了两口气,从腰间掏出匕首,迅速地找到了藤条最细的部分,一刀割了下去,藤条的下半截“唰”地溜下了悬崖……
闪电急促地亮了几下,接着是一串震耳的惊雷。
“田盘……”
田盘吓得魂不附体,向后一仰身,脊背贴在了树干上。
“田盘……”是孙武的声音,“要下雨了,不玩了,咱们走吧!”
田盘定了定神,急忙把匕首藏进腰里,喊道:“噢……来了!”接着便向山下跑去。
雨点密密麻麻地泼洒下来,天色更阴暗了。
学生们纷纷下了山,孙武在场院等着他们,告诉他们赶快回家。学生们都走了,田盘最后一个下山。
“山上还有人吗?”孙武问。
“没有了,赶紧回去吧!”田盘说。
两人一起往回走。走了百十步,孙武忽然问:“怎么没见梁有稷下山?”
“他可能从别的地方下山回家了。”田盘说。
“这不可能!”孙武斩钉截铁地说。
“怎么不可能?”
“我要到山上去找他!”
“找他?”田盘火了,“你还不如去找一条狗!”
“你这是什么话?”
“他的狗爹梁邱据把咱叔父从大司马的位子上扯了下来,你忘了?”田盘激愤地说,“我恨不得亲手宰了他们全家,你还上山去找他,贱不贱哪你!”
“他跟他爹是两码子事儿。”孙武说,“好歹他是咱们的同窗!”
“怎么,你改姓孙了,就不是田家的人啦?跟田家一刀两断啦?”
“我不跟你胡搅蛮缠!”孙武说完,回头就走。
“你别去!”田盘简直是在吼叫了。
孙武愣住了,他回过头来,凝视着田盘。四目对视良久,田盘终于将目光移开了。
“你真的对他下手了?”孙武小声问道。
“父亲做下的孽,做儿子的就应当偿还!”田盘咬着牙说,“再说了,总不能让那个梁邱据太得意,他也该哭几声了!”
大雨“哗哗”地下着,两人浑身都湿透了……
孙武浑身打了个冷战,之后声音颤抖地说道:“你先回去吧,我上去看看。”
“孙武,你……”
孙武头也不回地走了,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丛林中。
“孙武,你不配做田家的人!”田盘吼叫了一声,便抱着头,蹲下身去。
丛林里,孙武在茅草和树木之间穿行着,一面叫喊:“梁’有稷……你在哪里?答应我一声,梁有稷……”
林子里格外黑暗,地面又粘又滑,孙武抱着一根树干,站稳后推开这根树干,再去抓另一根树干,这样不断到往山上爬去……
“梁有稷……你答应我一声!梁有稷……”孙武拼命地喊着,然而,喊声被淹没在雷声和雨声之中。
林子里完全黑了,孙武茫然地站在山顶上,他已经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闪电亮了一阵又一阵,但亮光只是飘浮在天上,总照不到林子里面来,而且每次闪电亮过之后,林子里反而更黑了。
孙武很有些后悔,埋怨自己太粗心:上山的时候为什么不问问田盘在哪里下的手?只要我坚持逼问他,他会说的。要是当时问清楚,说不定早就把梁有稷背回家去了,可是现在……
忽然,他看见山底下亮起了一只火把。奇怪,谁会到这里来呢?哦,一定是梁有稷的家人,他们见孩子这么晚没回家,便去打听他的同窗,同窗一准会告诉他们下午曾经在这里玩过,于是他们就找到这里来了。要真是这样,那就糟糕透了!转念又想,觉得这个猜测不太对头,如果真他家的人出来寻找,就一定是很多人,那就应当有很多火把,对,不是梁有稷的家人!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火把似乎是有目标的,一直向孙武靠近,靠近,再靠近,最后,火把在他面前停了下来。孙武看不见那人的脸,却有一堆乱草般的东西扔了过来,将孙武的头盖住了。孙武一摸,是蓑衣。
“田盘!”孙武惊喜地喊道。
来者果然是田盘。他冷冷地说:“梁有稷就是从这里的悬崖上掉下去的,我们要先下山,然后转到山北面去找他。”
“那就快走吧!”孙武说着,就要下山。
“等等。”田盘一边说,一边却从地上抓起那根被他切断的藤条,将茬口放在火把上烧了一阵,又烧焦了近处的几根树枝,然后自言自语地说:“这样就好了,像是树林遭了雷击而起火,把藤条烧断了。”
两个人跌跌撞撞地下了山,又踩着泥泞的草地从山东面转到了山后,好容易找到了梁有稷。他倒悬地躺在乱石堆中,头朝下,周围的一大片雨水都是淡红色的,一看就知道流了很多血;他的右手抓着一根藤条。孙武吓坏了,浑身打了个激灵,之后扑到他身边,喊道:“梁有稷,梁有稷!”
没有应声。田盘把手指放在梁有稷的鼻孔上,过了一会儿,说:“他死了!”“梁有稷……”孙武号啕大哭起来。田盘咬着嘴唇,思索着,忽然,他转到了梁有稷尸体的右边,要把他手里的藤条抽出来。但尸体已经僵硬了,抽不动。田盘快速眨了几下眼皮,灵感来了,他用手抓住梁有稷的手,将藤条抬起来,用火把将新鲜的茬口烧焦了。
孙武伏在梁有稷的身上呜咽不止……
忽然,田盘从孙武身后将他的嘴捂住了。
“有稷……有稷……有稷呀!”远方传来了隐约的喊声。
田盘立即将火把插进水洼里,火把灭了,周围顿时一片漆黑。
“有稷……有稷……”
“梁公子……梁公子……”
喊声近了,隐约可以看到火把的亮光。
“赶快走!”田盘抓住孙武的手,没命地向西跑去。
已经是深夜了,雨淅淅沥沥地下着。
孙武觉得浑身疲惫不堪,却怎么也睡不着。梁有稷的尸体总是横在他的面前,挥之不去:杂乱的碎石、淡红的水洼、梁有稷紧抓着藤条的右手……他断定自己就是杀害梁有稷的凶手,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不策划这一场游戏,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做游戏也不要紧,只要我嘱咐他们一声不要藏在危险的地方,也不会出这样的意外。
但我最大的失误在于,没有看穿田盘的内心。
要说恨梁邱据,那是自然的,我也恨,恨得咬牙切齿。叔父田穰苴受了不白之冤以后,气得病了两个多月。刚好了些,却偏偏听到了北郭启征讨菖国大败而回的消息,结果又大病了一场。也没法不生气,爷爷征莒国的时候,只带了四千人,全胜而归,现在爷爷告老到乐安采邑去了。这次换上了獐头鼠目的北郭启,带去了六千人,却被小小的莒国打得丢盔卸甲,连帅旗都被人家夺走了,大齐国这点脸面都叫他丢得一干二净。消息传回,临淄城大街小巷骂声不绝,人们在北郭启和梁邱据的府门口泼上马尿,摔上牛粪。也真怪了,国君对此却浑然不觉,依然视那班宠臣如掌上明珠、怀中之宝,这就更叫人怒气难平。
然而这一切,与梁有稷何干?
不错,梁有稷有不少毛病,喜传口舌,好撒谎,又爱占人家的小便宜,有时也暗地里使别人的绊子,或许,这些毛病都是从他父亲的血脉里流传过来的,但这些小毛病难道要用整个一条命来抵消不成?这是多么昂贵的代价啊!
那田盘对梁有稷下手,是临时想出来的主意,还是蓄谋已久?不知道,也许两者都有。他平常说话,其言辞常常是带有攻击性的,咄咄逼人,这与田氏家族的显赫地位不无关系,但此外,却看不出别的什么来。今天,他居然亲手置梁有稷于死地,还那样从容地制造出遭雷击的假象,毁掉了作案证据,他性格中的这种阴鸷狠辣的成分,是我先前从未发现的,一想起来就觉得胆战心惊……
也许,正是他,才真正地继承了曾祖父田无宇的豪强之风,当年曾祖父联合了鲍氏在城东的稷门与高、栾两个家族展开了一场血战,打垮了他们,并分掉了他们的财产,那是需要勇气和狠气的,田氏家族从那以后便名声大噪,在齐国立住了脚跟……
也许是我太柔慈,太懦弱,骨子里怀着一腔妇人之仁?
孙武觉得自己的思维越来越混乱了,理不出个头绪来,是被窝里太热,还是自己在发烧?反正浑身都在出汗……
“稷儿……稷儿……”是女人凄厉的叫喊声。
孙武吓了一跳,急忙竖起了耳朵,仔细倾听。
“稷儿呀,我的孩子!稷儿……”啊,是梁有稷母亲的声音。
孙武赶紧把头蒙起来,全身缩成一团,似乎这样就可以躲开眼前的世界。
咚咚咚!是门环撞击着门板的声音,响极了,在被窝里面都能听得见。过了一会儿,女人的哭声近来了,接着就是叫声:“武公子……”
孙凭披上衣裳,把孙武叫了起来,两人一起来到前厅。在灯笼的微光中,孙武看见了梁有稷的母亲,她像是刚从水里涝出来的一样,头发散乱地贴在脸上和头皮上,鼻尖和下巴都滴着水,两只胳膊由两个女佣搀扶着,膝盖松软地弯曲着,显然,她身体的重量都压在女佣身上了。她一见孙武,就跪了下来。
这时孙武的母亲也来了,赶忙凑上前去拉她,说:“大嫂,你这是做什么?”
“武公子,有稷……有稷是怎么进的林子?”梁有稷的母亲恳求地问道。
“嫂子,稷公子出事了?”孙凭问。
“稷儿……他死了!”梁有稷母亲说,接着便“哇哇”地大哭起来。
“武儿。”孙凭吼叫道,“怎么回事,说!”
孙武朝着梁有稷母亲跪下了,说不出话,泪水夺眶而出……
孙武母亲听说梁有稷死了,也禁不住流下泪来,在场的人哭成一团……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梁邱据的声音刚落,接着本人就进来了,他没有跟孙凭打招呼,只顾呵斥女佣道:“赶快回去!”
女佣们不敢怠慢,搀起梁有稷母亲就往外走,梁邱据也跟着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