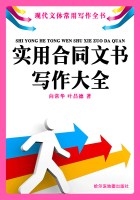“‘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的这些话难道你都忘了?”孙武的话滔滔如流水。
“人说齐国多辩士,果然名不虚传!”
孙武和田盘吃了一惊,回头看去,原来是缪不识来到他们身边。
“我们的话你都听见了?”田盘问。
“没有。”缪不识答道:“我只听了孙武最后一段话,引经据典,老子的话一套一套的,正像你们常说的那样,‘洋洋洒洒,口若悬河’。”
“你怎么没回家?”孙武问他。
缪不识没有回答他,却问:“你们知道姜乙卓今天成绩坏的原因吗?”
“我也疑惑,他的‘五御’本来是学得很好的。”孙武说。
“他父亲昨天刚受了刖刑。”缪不识说。
“啊!”孙武惊叫起来。
田盘说:“听我爷爷说,这次是为了翻修申池加收税赋,凡是拖欠的一律受刖刑,临淄城里,受刑的就有一百多个。这个混账国君,不但昏聩,而且残暴!”
缪不识听了,吓得瞠目结舌。
孙武急忙掩饰道:“走,咱们分头回家拿点礼品,一起去姜乙卓家去看望一下。”
缪不识先走了。孙武对田盘说:“你怎么老是改不了这个毛病?”
“这口恶气,哪个有血气的人能咽得下?”田盘吼叫起来。
“我问你。”孙武道,“你爷爷是朝廷的大夫,他肯定也不满意国君的这种做法,但是他当着国君的面反对过没有?”
田盘语塞。孙武说:“我就知道,他没反对过。为什么?现在满朝文武,除了晏婴以外,没有一个敢于明目张胆对国君提出批评的。只有晏婴敢这样做,但是,即使这样,国君也经常不理睬晏婴的话。你掂量一下,你的分量比晏婴如何?”
“我……”田盘支吾了一声。
“你的分量连晏婴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都不到。”孙武说,“然而你却想做晏婴那样的人!”
“好了好了,今天是你说得对,我听你的。”田盘说,“以后我把嘴封住就是了,不再乱说了。”“那就好。”孙武说。“不过。”田盘说,“你最后一句话说得不对。”“怎么?”孙武问。
“我并不想做晏婴那样的人。”田盘说。
孙武疑惑地看着他。
“你有抱负,这我知道,但你的抱负是为臣之道。”田盘的神情变得诡秘起来,“而我的抱负,却是为君之道。”
“就凭你这副德性,我就不信你能当上国君!”孙武轻蔑地说。
“也许我当不上。”田盘底气十足地说,“但我的儿子,孙子一定能当上。”
孙武惊愕不已,这不是缪不识的父亲缪甲曾经说过的话吗?是的,晏婴也做过这样的预测,真是不可思议!
“我的才能远不及你。”田盘继续说,“但我有做国君的志向,或者叫野心,你没有,你必须屈为人臣,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率兵点将,驰骋疆场,毕竟不是国君的事体,而只能是臣子的本分。臣子的命运是系结在国君身上的,姜子牙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明君。然而眼下列国纷争,如同群兽厮斗,做国君的个个利令智昏,鼠目寸光,像尧、舜、夏启、商汤、周武那样的明君,今天不会再有了,即使我做了国君,也成不了明君。所以,你的结局,可能很悲惨:你打了败仗,会名声扫地;你功业卓着,会引起国君的猜忌。因此你到头来不是功成身退,就是兔死狗烹。”
孙武失神地望着天空,痴呆良久。
晚上,内朝绰约亭,齐景公与晏婴相对而坐。
晏婴一脸倦容,因受了风寒,眼睛有些红肿,他刚才应景公之召,匆匆整理衣冠而来,没来得及梳洗,鬓发和胡须都乱蓬蓬的。
齐景公把白天的事对晏婴讲了一遍,神情颇有些沮丧。
晏婴说道:“去年卫国的东野稷表演御术,主公很想看,但婴子不喜欢看,结果主公就没有到场;今天翟羡表演御术,主公不想看,但婴子要看,主公就看了,而且还依了婴子的意愿,厚加赏赐。臣不明白,主公何以总是为了满足一个嬖姬的心愿而改变自己的主意?听嬖姬之言而赏赐御夫,此乃冷人心、蓄民怨之道也。《诗》曰:‘哲夫成城,哲妇倾城。’难道主公要让这两句话在大齐国应验?”
“此乃寡人之一误!”齐景公悔悟道。
晏婴继续说道:“庠序的测试,乃是为了强国振邦而培养和举拔人才,而翟羡的御术无非是满足人们的耳目之欲罢了。主公将庠序的奖品转赐给翟羡,岂不是本末倒置?依臣看来,这是主公的又一大误。”
“贤相说的是。”齐景公点了点头。
“先君桓公在世时,齐国之地比现在狭小,但桓公能够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晏婴接着说,“而主公即位以来,岁凶年饥,赋税繁重,百姓不堪其苦,更兼用刑严酷,致使临淄之地鞋贱而踊贵,而主公却沉溺于甘醴歌舞、高台深池、钟鼓管弦、禽鸟狗马之中。宫里的牛马多而无处可用,最终老死在棚栏里;车子用不过来,堆得像小山一般高,结果让虫子蛀坏了;锦缎布帛塞满橱柜,因潮湿而生出了绒毛;美酒佳酿喝不尽,一坛一坛地变酸了;粮食也吃不完,放在仓屯里发霉了。另一方面,赋税却在不断增加。长此下去,民心尽丧的时候,主公当置先君遗业于何地?”
晏婴说到这里,已经气喘吁吁了,脸也涨得通红。
齐景公忙说:“贤相身体欠佳,早些回府歇息吧!”
“臣的一片愚忠,都是为了大齐的兴旺啊!”晏婴加了一句。
“贤相的话,寡人记住了,放心去吧。”齐景公说,一面招呼宫人把晏婴送回了府邸。
晏婴走后,齐景公颇有些怅然若失之感。晏婴这个人,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他身材矮小,肚子里却装着永远也掏不完的学问,不管什么问题,他都能说出一番深邃而无可辩驳的道理来,使听者心里的疙瘩迎刃而解。因此,齐景公每当心中有所困惑的时候,就愿意听听晏婴的见解,他知道晏婴是个敢于犯颜直谏的人,说起话来锋芒毕露,毫无顾忌,但在他听来却并不觉得逆耳。今天的情况似乎不太一样,也许是谈话没有结束的缘故,总之,晏婴走后,齐景公心里的疙瘩并没有解开。
是什么疙瘩呢?对了,是田盘。正是这个少年后生让一国之君当众出丑!刚才应当先问问这件事的,然而,晏婴已经走了!
阍人报说梁邱据与裔款求见,齐景公喜出望外,连忙召他们进宫。
刚一坐下,裔款就抢着说:“微臣跟梁大夫挂牵着主公,特来向主公问安。”
“难得你们一片热诚。”齐景公笑道。
“唉,今天要不是梁大夫急中生智,那场面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收拾!”裔款又说。
一句话戳到了齐景公心中的痛处,他吭了吭鼻子,说:“这个田盘太不知天高地厚了,真欠管教!”
裔款向梁邱据使了个眼色,梁邱据说道:“今天的事,看起来,好像是田盘年少无知,一时冲动,不过……”
“不过什么?”齐景公问道。
“微臣想来想去,就是想不明白。”梁邱据继续说,“要说年少无知,决不只是田盘一个人,在场的学生们都是年少无知的,但敢于如此张狂无礼的却绝对不会是别的人!”
“什么意思?”齐景公又问。
梁邱据答道:“微臣觉得田盘说起话来很有底气,不像主公所说的那样不知天高地厚,其实他的心里,是很知道天高地厚的。”
齐景公沉默良久,说:“你的意思是说,田盘心里很清楚,自己有田氏家族这棵大树为他壮胆撑腰?”“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裔款插了一句。
“晏国相早就有预言,齐国的大权早晚要落到田氏手中,主公不可不防啊!”梁邱据把晏婴的话搬了出来。
齐景公摆了摆手,说道:“晏国相的这句话,太有些危言耸听,二位贤卿不必担忧,眼下田氏家族绝无欺君妄上的迹象。’”“单凭某一件事,的确说明不了什么。”梁邱据说,“但是,如果把前后的事连起来,就能见出些文章来。”
“此话怎讲?”齐景公问。
梁邱据看了裔款一眼,裔款说道:“打从田无宇那时候起,就用小量进、大量出的借贷方法蛊惑人心,如今的田乞,仍然实行着这一套把戏;再看田穰苴,上任伊始,就借故杀死朝廷的重臣庄贾,还要处死主公的使者梁大夫,气焰是何等嚣张!庄贾纵然有错,也应押送朝廷任凭主公处置;梁大夫驱车进入兵阵,本是无所谓的事,他偏要小题大做,造出事端来,他这样做,还不是要树立一己之威?主公好不容易从官帑拨了一笔款子,要修熏风台,他硬是要了去补充军需,他这样做无非是为了笼络将士。如今,他的威也有了,恩也有了,军队里面,只知有大司马,而不知有主公啊!这些年,主公对田家的人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才导致了今天田盘的狂妄犯上之举呀!”
“田氏夺齐,现在条件尚未成熟,还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主公觉得自身安然无恙。”梁邱据接言道,“但身为臣子,我等对田氏家族的人可是畏之如虎啊!每次上朝的时候,微臣一见那位司马穰苴,就浑身战栗,连气都不敢喘……”
说到这里,梁邱据忽然涕泪横流,哽咽不止。
“太夸张了。”齐景公说,“至于吗?”
“主公难道忘了,梁大夫差一点死在田穰苴的斧钺之下!”裔款抢言道。
“寡人倒疏忽了。”齐景公说,“那件事让贤卿受委屈了。”
“微臣受点委屈倒是无所谓。”梁邱据说,“只是那田穰苴将罪过加在微臣身上,可是怒气却泄在了主公脸上,微臣心疼啊!”
“梁大夫说得对,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裔款说。
“依二位贤卿看,应该怎么办?”齐景公问。
“削减田氏在齐国的势力。”梁邱据答道。
“怎么削减?”齐景公又问。
“田氏家族中地位最显要的是田穰苴,削了他的职位,田氏的力量就削减了一半。”梁邱据说。
“不不。”齐景公摇摇头,“撤掉他,朝野会引起很大的震动,再说,谁来代替他?”
“微臣向主公保举一人。”梁邱据说。
齐景公神情惊疑地问:“谁?”
“北郭启。”梁邱据回答。
齐景公的神情由惊疑转为失望:“他能担任大司马?”
“按北郭启现在的地位,大司马之职显得重了些。”梁邱据解释说,“但此人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精文韬,通武略,有旷世之才,主公如果不放心,暂且不必授以大司马之职,只让他带兵即可,等一年半载之后再做定夺。”
“这件事以后慢慢计议吧。”齐景公说,“寡人现在心里有点儿乱。”
两人说了声“主公保重”,便退了出来。
事有凑巧,齐景公当夜就患了疟疾,发烧,不住地打摆子,宫医伺候他吃了几服药,稍微轻了些,却不能痊愈,三天两头地闹腹泻。
一天晚上,裔款来到太祝虞如家中。虞如感到很意外,问:“足下屈驾敝舍,必定有所吩咐。”
裔款将一双玉佩放在案几上,说道:“先生太客气了,晚辈哪里敢吩咐先生?只是顺路来看看先生而已。”
“既如此,老朽当有还礼。”虞如说完,便找出了一对玉环放在裔款面前。
裔款尴尬地说:“先生何必如此,晚生今天来,只是孝敬先生,别无他意,先生要是还礼,就太见外了。”
“无功不受禄嘛!”虞如笑道,“足下要是有什么吩咐,不妨直言。”
“是……是这样。”裔款吞吞吐吐地说,“前不久,主公出席庠序测试,被一个叫田盘的少年的无礼顶撞,主公当众不好发作,一股怒气堵在心头,回宫以后,就病倒了,至今未能痊愈。先生是掌管占卜祭祀事务的,望能指明使主公致病的元凶,祭奠上苍,以解主公之病恙。”
“足下的意思是,让老朽指定田盘是主公生病的由头?”虞如问。
“事情明摆着。”裔款说,“若非妖气扑身,主公怎能至今未愈?”
虞如正色道:“但据老朽所知,主公患的是疟疾,田盘纵然无礼,惹得主公的怒气冲心,然而怒气能导致疟疾否?”
“可主公确实是那天回宫以后就生了病的。”裔款说。
虞如反问道:“倘若足下现在回家生了病,是不是也可以说到太祝虞如家里去了一趟就生了病,进而说足下的病是老朽所致呢?”
一句话问得裔款张口结舌。
“以谎言欺君欺世,乃老朽所不敢为也!”虞如站起身来,“足下要是跟田家有什么嫌隙想要借刀,望另请高明。”
裔款面如土色,惶惶然地站起来,匆忙告辞,临走,虞如把那双玉佩递回他的手中。
裔款碰了一鼻子灰,气急败坏地跑到梁邱据家里。
“荒唐!愚蠢!”听了裔款的述说,梁邱据大发雷霆,“老弟,你把自己给卖了!”
“怎么?”裔款茫然地问。
“你想想,要是虞如把你的话说出去,田家的人能饶得了你?”梁邱据吼叫道,“弄不好,我都会受到牵连!”
裔款像遭了雷击,全身麻木,脸色蜡黄。
“田家蓄养的敢死之士不下百人,随便派出一个人来就能抹了你的脖子,之后逃之天天,官兵连个人影子都抓不到。”梁邱据怒气未息。
裔款像是筛了糠,浑身瑟缩不止:“那……那……怎……怎么办?”
梁邱据摩挲着案几的一角,不住地眨巴着眼皮,忽然,手掌在案几上猛地一拍,说道:“一不做,二不休,就这么办!”
裔款像得了救命稻草似的把脸凑了上去,两人如此这般地低语了一阵。
第二天下午,梁邱据和裔款又进宫看望齐景公。昨日齐景公的病情稍微见强了些,今日却又加重了,忽冷忽热,心情格外烦躁。
一见面,梁邱据和裔款便伤心地抽泣起来,对于他们的泪水,齐景公似乎不太在意,他没有动,仍旧闭着眼,躺在红木床榻上。
“主公久病不愈,实在有些怪异,微臣看过宫医所开的方子,没有错。”梁邱据说,“但主公却不见好,必定另有原因。”
齐景公立即坐了起来,看着梁邱据,似在询问。
梁邱据边思索,边说:“这些年朝廷对神灵的供奉比起前辈来要多得多,主公偏偏就生病了,而且药方对路却不见好,原因只有一个。”
“原因何在?”齐景公急切地问。
“太祝祭祀上天没有尽心。”梁邱据斩钉截铁地说。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尽心?”齐景公问。
梁邱据答道:“微臣听郊庙里的童子说,虞如每次祭祀上天时,都只是双膝跪地,口中却不发一言。”
齐景公顿悟似的说道;“哦,寡人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层呢?现在该怎么办?”
梁邱据说:“只有杀掉太祝虞如,向上天谢罪,主公的病方能痊愈。”
“杀太祝?”齐景公吃惊地站了起来。
梁邱据挥泪道:“在性命攸关之际,主公万不可守妇人之仁。主公的命就是齐国臣民的命,为了主公康复,何惜一个太祝乎?”
裔款也掩面泣涕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万一主公有个三长两短,呜呜呜……”
齐景公摆了摆手说:“这件事二位贤卿去办吧!”
梁邱据和裔款得了指令,欣喜若狂,他们生怕夜长梦多,立即带领宫廷侍卫前去锁拿虞如。
再说齐景公本来就发着高烧,邱据和裔款进宫后说三道四地折腾了半晌,他一时兴奋,又是坐又是站的,却忘了披衣裳,结果病情愈发加重了。两人走后,齐景公忽然感到浑身冰冷,牙齿都不住地打颤,用手一摸前额,滚烫,他挪蹭着走了几步,只觉得眼前一黑,便一头栽倒在床榻上。昏迷中,他恍惚地意识到富人给他盖上了被子,而自己的身体,却在旋转不止,一切思维都停顿了,脑海里只留着一个念头:只要悬在虞如脖子上的那把刀砍下去,我就可以痊愈了!
这边,粱邱据和裔款将虞如押至城西点兵场,就要动手行刑。
可巧田穰苴巡视边防返回临淄,见此场面,当即上前喝止。他问明了缘由之后,便命随身将士为虞如松了绑,然后跟他同车前往宫廷。
梁邱据和裔款早就抢在前面进了宫。齐景公听说田穰苴放了虞如,还气势汹汹地带着他进宫要向国君问罪,一时怒火中烧,用干燥而沙哑的嗓音对梁邱据和裔款说:“田穰苴爱惜一介太祝而置国君的生死于不顾,逆臣也!传寡人的旨意,免去田穰苴的大司马之职,将其贬为庶人,军权悉交北郭启。”
梁邱据和裔款刚走到中朝,正碰上田穰苴和虞如,梁邱据口述了齐景公的旨意,并勒令田穰苴交出将印。
“我要见主公!”田穰苴说。
“可主公并没有召见你!”梁邱据答道。
“你想一手遮天吗?”田穰苴吼了一声,便要闯进去。
“侍卫!”梁邱据也喊了一声。
侍卫们双双交叉持戈,挡住了田穰苴。
“杀太祝是你的主意?”田穰苴质问梁邱据。
“是主公的吩咐!”梁邱据强硬地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