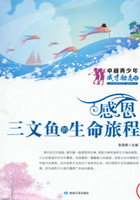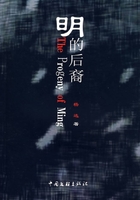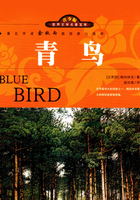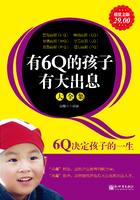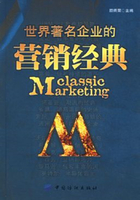经说
在《诗经》作为五经之一而流传的时代里,它的经学意义是要大于它的文学意义的。《文心雕龙·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也。”所谓“经学意义”,主要指的是《诗经》作为“至道”与“鸿论”对于人生的指导意义,也就是它作为一种价值观,对于民族行为的规范与制约意义。一篇平常的诗,一旦被认作是圣典,它的内涵与意义就会十倍百倍的增长起来。《诗经》就是如此,它不仅是中国人的经典,同时也是包括朝鲜、日本、越南等在内的古代东方世界的经典。如日本昭和十二年印行的一部名曰《诗经之研究》(又名《倭满汉三合诗经》)的书,其每部分的扉页上就分别赫然写着“修身齐家之圣典”、“经世安民之圣训”之类的大字。不过作为经典,因所处时代、环境不同,其理解的差异性是很大的。如《关雎》一篇,《毛诗》以为其深意在“忧贤”,表面上是想求美女,而实际上更看重的是内在的“贤”,并不在外在的“色”上,因此诗中虽表现出了“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的刻骨思念,但并不影响他善道之心。这就是所谓得“性情之正”,对人是有表率作用的。《鲁诗》则说:“后妃之制,夭寿治乱存亡之端也。是以佩玉晏鸣,《关雎》叹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离制度之生无厌,天下将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咏淑女几以配上,忠孝之笃,仁厚之作也。”(见王先谦《三家诗义集疏》)这是认为《关雎》是一篇刺诗,是表现臣下对君主“忠孝”“仁厚”行为的。朝鲜十八世纪的学者李瀷则说:“‘琴瑟友之’,夫妇有友道。友者,辅仁者也,不独于此朋友有夫妇之义。凡义合情亲,莫如夫妇,规切不嫌,胜己不妬,安乐必思,灾患与共,古之友道也,盖莫如此。孔子赞之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以迩者不惑,而远者不疑。诗云:‘君子好逑。’逑而称好,不善者远矣。”(《诗经疾书》)这是由“琴瑟友之”而延伸出的对“交友之道”的理解,强调患难与共的人际关系,其中自然蕴有对人情浇薄世风的劝戒。日本皆川愿《诗经绎解》则说此诗是“拟思中德而求实与相配”,并解第一章说:“此章言:人若不常用心内省,而外从物欲,鳏鳏然譬如雎鸠,必失其处,至以离山而越在河洲;君子其必不若斯矣。”这又把诗与“内省”联系了起来。因为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是从经典中发掘藏在文字背后的圣人之意,以及诗尽可能的由象征、比喻衍生出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多是由其与现实人生的联系体现出来的,故一部《诗经》的经学史,也就变成了一部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史。而经的意义,也就体现在了其对现实人生的指导作用上。
《关雎》作为《诗经》的第一篇,而且自古即把此篇的内容与后妃之德联系起来,编诗者自然有特殊的考虑,而且从经的角度来讲,其意义一定非同一般。司马迁在《外戚世家》中,把此篇居首的意义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他说:“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徳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韩诗外传》卷五记孔子与子夏的对话说:“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关雎》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书图,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叹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像这样巨大的意义,我们今天已很难感受到了,但敢肯定,古人的这种领悟一定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
就经学的意义而言,古今大略相同的认识有两点,第一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得“性情之正”。这也是《诗经》作为经学所十分强调的一点。男女之情乃人道之常,如果没有了这种情,人类就有可能绝种,因而绝对不可没有。但人与动物之别在于,人的这种情是有道德制约的,不能放荡不羁,这就是所谓止乎礼义。《诗序》说:“发乎情,人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所谓“先王之泽”,就是指先王的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念制约着人的行为,使人把握着爱情的尺度。《关雎》篇所表现的爱情故事,就是非常有分寸、合于情礼的恋爱进行曲。孔子对《关雎》有两句非常经典的评价,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谓“乐”,是指君子淑女相得之乐,“不淫”,是指虽欢乐但不过度(淫者过也)。“哀”,是指未得淑女时的忧思,“不伤”是指不为过度忧思而伤神。像人在恋爱过程中,“乐”与“哀”都是很正常的,《关雎》所表现的正是这种正常的情感,所以说是“得性情之正”。有相当多的年轻人,为了爱情,要死要活,背弃父母,背弃家庭,乐则相吻于闹市,哀则自杀于密室。这则是“乐而淫,哀而伤”,大背人道之正。对此而言,《关雎》自然是有表率意义的。
第二是正夫妇的意义。《关雎》表现出的是一种和谐的爱情关系,《毛传》说“后妃说乐君子,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虽然“后妃”“君子”之说不见其是,但那种“无不和谐”的气氛却是可以感受到的。《诗序》所谓“风天下而正夫妇”,就是希望化此成俗,让天下夫妇皆能如《关雎》之人,“夫妇正”这是根本,《毛传》说:“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这是古人的逻辑。日本学者仁井田好古《毛诗补传》说:“龚遂曰:《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是也。然举其要,则《二南》为之本。举《二南》之要,则《关雎》一篇为之本。其所以为本者何?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推及于国,及于天下,莫不被熙皞之化者,由此道也。”夫妇正了家道就可以兴,家兴了国就可以治,天下也就可以安。风俗归于纯厚,民皆敦于孝敬,这无疑是人所共盼的。也是《关雎》作为经要承担的文化责任。
葛覃收葛歌。
一
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
维叶萋萋。
黄鸟于飞,
集于灌木,
其鸣喈喈。
葛藤是如此细长啊,
蔓延在山间的谷中,
繁茂的叶子一片青青。
山谷间飞起美丽的黄鸟,
它轻轻地降落在灌木林丛,
婉转的鸣声是这般动听。
[异字]覃,《释文》:本亦作蕈。《鲁诗》亦作蕈。武威磨咀子六号汉墓简本《仪礼》作“葛勝”。维,《韩诗》作惟。灌,鲁亦作樌。
[韵读]谷、木,屋韵;萋、飞、喈,脂微合韵。
【葛】葛是一种藤本植物,有家生、野生两种,藤蔓长可达数丈,葛皮纤维可以织布。
按: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八曰:“葛有野生,有家种,其蔓延长,取治可作絺绤;其根外紫内白,长者七八尺;其叶有三尖如枫叶而长,面青背淡;其花成穗,累累相缀,红紫色;其萸如小黄豆,荚亦有毛;其子绿色,扁扁如盐梅子核,生嚼腥气。”吴其浚《植物名物图考》云:“无论燕、豫、江西、湖广,皆产葛。凡采葛,夏月葛成,嫩而短者留之;一丈上下者连根取,谓之头葛。……凡练葛,采后即挽成网,紧火煮烂熟,指甲剥看,麻白不粘着即剥下,就流水捶洗净,风干露一宿,尤白。”
【覃】长延广被之状。一说蔓延。
按:覃字旧约有四说:一,蔓,延也,蔓延。《毛传》、《朱传》皆曰:“覃,延也。”二,训深。杨简《慈湖诗传》:“覃本义深也。葛叶大而蔓小,故坠焉而深下,俗谓坠下曰覃。”三,训长。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曰:“覃本延移之称,引伸为长之通称。”并以为覃、蕁、古音相通,训长;从寻,寻亦长也。《方言》:“自关而西,秦晋梁益之间,凡物长谓之寻。”四,同诞,训阔,言节之疏阔。俞樾《茶香室经说》曰:“《旄邱》篇:‘旄邱之葛兮,何诞之节兮。’《传》曰:‘诞,阔也。’《笺》云:‘土气缓则葛生阔节。’疑此经‘覃’字与彼经‘诞’字同。覃与诞声近,诞从延声,覃得训延,亦得训诞。‘葛之覃兮’犹云‘葛之诞兮’,以诗说诗,不必泥雅训也。”五,覃即藤之音转。闻一多先生《诗经新义》认为覃、藤一声之转,高亨先生《诗经今注》亦曰:“覃,当读为藤,蔓也。”四说皆通,但细思之,似以马瑞辰说为长。《说文》云:“覃,长味也。”《生民传》:“覃,长也。”是覃之本义为长。在《诗经》中,此类句式较多,如《郑风·缁衣》“缁衣之宜兮”、“缁衣之好兮”、“缁衣之席兮”。《丰》“子之丰兮”、“子之昌兮”,《齐风·还》“子之还兮”、“子之茂兮”、“子之昌兮”,《陈风·宛丘》“子之汤兮”,“之”后一字皆为形容词。“缁衣之宜”是称缁衣之好,“子之丰”是称其丰满,“子之还”是称其灵捷。由此推之,“葛之覃”当是称葛之长,“覃”形容葛藤长延广被、缠绕不断之貌。“之”犹“其”,“葛其覃”是说“葛是那样的长”。至于闻一多所创覃、藤一声之转说,笔者先前曾从其说,后细思之,此当是二字同源的原因,而不能以此定覃为藤。《诗经》言葛者,其实所指的就是葛藤,如“彼采葛兮”,所采者即葛藤;“旄丘之葛兮”,指的是旄丘的葛藤;“葛生蒙楚”、“葛生蒙棘”,指的是葛藤蔓延于楚、棘之上。不必再出一“藤”字。
【兮】语辞,犹“啊”。
按:《说文》:“兮,语所稽(留止)也。从丂八,象气越亏也(段注:越亏皆扬也。八象气分而扬也)。”孔广居《说文疑疑》说:“兮,诗歌之馀声也。从丂从八。丂者,气不得舒也;八者,分也。诗歌所以宣其郁结,故从丂而分散之也。”窃疑“兮”从八丂声,与“可”字声符同。《说文》:“可,肯也。从口、丂,丂亦声。”《集韵·歌韵》:“歌,古作可。”今本《老子》“兮”字,帛书本皆作“呵”,“呵”即“啊”,为语气助词。歌、啊、兮皆一音之分化,故意义上也有联系。
【施】延伸、蔓延。
按:《毛传》“施,移也。”孔颖达云:“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季本云:“施,引蔓相及也。”《东山》“果臝之实,亦施于宇”,《頍弁》“施于松柏”,《旱麓》“莫莫葛藟,施于条枚”,诸“施”字与此用法相同,都是蔓延、引申的意思。施古音如拖,今山西方言中,尚有称“延蔓”为“拖蔓”者,即古音之遗存。山东方言中也有类似的读音,牟庭《诗切》、丁惟汾《诗毛氏解故》皆曾言及。如丁氏云:“今日照人读施为妥音,与古音密合。”又:施、延双声互转,故“施于条枚”,《韩诗》又作“延于条枚”。《皇矣》篇“施于孙子”,笺云:“施,猶易也、延也。”《说文》:“延,长行也。”《方言》:“延,长也。”马瑞辰以为延、易、移皆一声之转,施即延之假借。今人多称藤蔓延伸为“延蔓”,音或转为“引蔓”。何楷别出新意,云:“施本训为旗逶迤之貌,借以为附丽缠绕之义。”张次仲从其说,陈澧《东塾读书记》又说:“《说文》:‘施,旗貌。’‘旖,旗旖施也。’‘移,禾相倚移也。’此经‘施’字乃‘旖施’之‘施’。《传》‘移’字乃‘倚移’之移,皆柔曲猗那之貌。《传》训‘施’为‘移’,葛藟之形状如绘也。”何、陈之说,有锐意求新之嫌。
【中谷】山谷之中。此两句说:葛的藤蔓,蔓延在山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