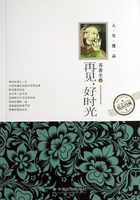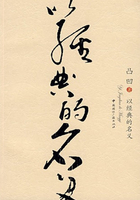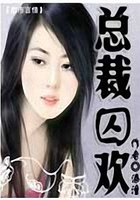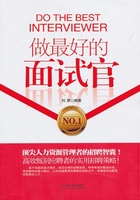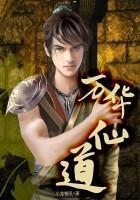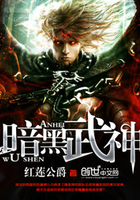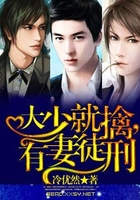当然,这些均属旁证,更主要的,还得看这首杜诗写的是持剑舞,还是空手舞,还是彩绸舞。请看,诗一开头就写出: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这种惊人的艺术效果是一般舞蹈所能达到的么?如不是舞技超群,不会招来四方如山的观众;如果不是惊险异常的舞技动作,不会使观众出现“色沮丧”的表情;如果不是旋风般刀光剑影上下左右舞动,使人眼花缭乱,不会有“天地为之久低昂”——旋天旋地的感觉。
再看:
“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
这不是神奇的剑舞是什么?
从亮度上写剑舞光华莫测,如九日之霍霍发光,如群龙闪鳞之耀眼,如雷霆闪电之刺眼,如江海凝光之炫目;
从声响上写剑舞震耳欲聋,如九日之崩落轰天动地,如龙翔之搅海激浪拍天,如雷霆震怒之隆隆响彻云雷,如江海之涛浪滚滚山摇地动;
从速度上写剑舞之迅猛异常,九日从天降落该多快!群龙矫翔,该多快!来如雷电,该多快!罢如潮退,该多快!
这四句夸张比喻,把剑舞形容得淋漓尽致,声势咄咄逼人,更显出“色沮丧”、“久低昂”的惊险艺术效果。
彩绸是软绵绵的,持彩绸而舞,是要翩翩起舞,起着惊鸿,落如飞雁,具有曲曲流水、飘飘行云之美。彩绸舞是表现不出如此惊险迅疾、气势震惊的艺术效果来的。至于徒手舞当然更难表现出光、声之美的效果。
张旭大草曾因观公孙大娘舞剑而益加神奇飘忽,吴道子的画笔曾因观裴旻舞剑而益加变幻莫测,那么杜甫诗歌也可以说因观公孙大娘及其弟子舞剑而益加奔放无羁,气魄宏大吧?
§§§第16节“白日依山尽”,依东山乎,依西山乎?——读王之涣《登鹳雀楼》诗
唐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鹳雀楼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县)城上。楼高三层。登楼向西南可望云雾中的华山,下瞰黄河滚滚南流。鹳雀楼是有名的登临胜地,唐代诗人李益、许浑等都有登楼眺望的诗。
王之涣这首诗在短小中见大千,被誉为千古绝唱。全诗集中写“登”:头两句写登临所见;后两句写欲见更广则须更登。
向西南遥望:白日依傍着华山即将沉没;向北看,黄河由西北流来经脚下折向东南方滚滚流向大海。这眼前景色已够开阔的了,楼也够高的了,这是现实的客观世界。一个“尽”,一个“入”,把诗的境界点化得何等深远?可是诗人随目力所及想要望得更高更远,白日入山后将什么样呢?黄河流入海又是如何?一个“穷”字使诗的境界陡然上升,一个“更”字直接表达了诗人“欲穷千里目”的决心。“一层楼”非由第一层到第二层,或由第二层到第三层,而是说要登上比此楼更高的一层,再高的一层,直至山无阻挡,海入眼底。
“更上一层楼”,给人以很多联想,极大启发,不只观赏,希望“更上一层楼”,以期“欲穷千里”。我们干什么有益的事业,谁不希望站得高望得远呢?鹳雀楼虽高,还要更上一层;我们不满足于既得成就,也还要更上一层楼。这句诗将永远鼓舞着人们向远处,向高处攀登。
多好的一首诗啊!流传千载,童叟吟诵如流。可是为此诗作解时,却有不少失误之处。请看:《梦溪笔谈》:“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惟李益、王之涣、畅当三篇能状其景。”
由沈括这个“前瞻中条”,后人随声附和者甚多。如《唐代诗评注读本》:“楼前所见者,中条之山。”而且附会说,“其山高大,日为所遮。”《唐诗三百首注疏》也顺着说:“仰而视之,日之所至,无所不见,所不见者为高山阻隔,故曰‘依山尽’。”今日更有给“前瞻中条”作具体解说者,说中条山距鹳雀楼十五里。主峰雪花峰高达一千九百九十四公尺。说诗人远眺的必是此山。由此又解“白日”为明亮亮的阳光,于是把首句解为:“明亮亮的阳光沿着中条山往前延神,一直到目力所及的尽头。”再看王相的《千家诗注》:“登此楼时已薄暮,但见白日依山而欲尽,黄河之水由西滔滔向东入于海矣。”
按:中条山本在蒲州东南。依沈说则王之涣登楼远眺的是东方;依王注则王之涣远眺的却是西方,一东一西,孰个为是?
沈括不是说李益、畅当也有登鹳雀楼诗吗?那就让我们来看看。
李益《同崔邠登鹳雀楼》:“鹳雀楼西有尺樯,汀州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为长。风烟并起思归望,远目非春亦自伤。”
畅当诗:“迥临飞鸟上,高出(谢)尘(人)世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
黄河在蒲西,故李诗首句即写明黄河上的百尺桅樯是在鹳雀楼西。畅诗末两句所写景物和李诗前两句大体相同:汀州、云树、平野、断山。可见登楼远眺的是西方。
实际,鹳雀楼是蒲州城的西门楼,今虽不在,当地人还是能指出旧址的。
既不是向东远眺,而是向西远眺,这就好解释了。“白日依山尽”,就是日快依山而没,是夕阳西下,绝不是什么山为日遮,目力用尽之意。还是《千家诗》讲得对。
也许有人会问,海不是向东流么?其实蒲州黄河段,既不向西也不向东,而是由北向南流。直至风陵渡才折向东流。站在鹳鹊楼上怎会看得见呢?
其实,作诗正不必实见实闻,但也不是说不无触因。触发由实景物而起,经神思遐想,可以写出想像中的境界。这首诗,“海”,不是实见的海,“山”,也不是实见的山。目力所及的实景既无海,也无山;从蒲州城楼所能望见的只能是渺茫中的华山一线而已。山虽不见,但黄昏时谁都知道日落西山;海虽不见,但谁知道河流千转终必入海。正因为这不见或难见,诗人才展开想像的翅膀飞向千里外,逼出个“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来。这里强调的是远望夕阳虽没入一抹的远山之后,望的虽够远的了,但诗人还要往山那边更穷尽一望,这才合乎诗意。
§§§第17节读鹳雀楼诗
现存《全唐诗》中写登临鹳雀楼的诗计有王之涣、李益、畅当、耿伟、殷尧藩、司马扎、马戴、张乔、吴融等九人诗作。这些诗给我们描绘了鹳雀楼昔日的壮丽风光。写楼高:“迥临飞鸟上,高出尘世间。”“高楼日渐低”,“鸟在林梢脚地看”,“危楼高架泬廖天”。写远眺:“鹳雀楼西百尺墙,沙汀云树共茫茫。”“渔人遗火成寒烧,牧笛吹风起夜波。”水有渔舟来往,岸有牧笛悠扬。“黄河行海内,华岳镇关西。”“烟树遥分陕,山河曲向秦。”“树隔五陵秋色早,水连三晋夕阳多。”陕晋风光,尽收眼底。“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是那样空阔:“鸟道残红挂,龙潭返照移”,是那样壮美;“冻开河水奔浑急,雪洗条山错落寒。”早春是如此充满生机;“晴峰耸目当周道,秋谷垂花错落寒。”晚秋又是如此丰登在望。追往昔:“汉家箫鼓随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汉武帝巡视河东曾赋《秋风辞》,魏武侯与吴起曾在此议论过兴邦强国“在德不在险”。“尧女楼西望,人怀太古时。”娥皇、女英在妫、汭水边出嫁给虞舜,传为千古爱情的佳话。“海波通禹甸,山木闭虞祠。”禹凿龙门,舜耕历山,此地让人想起古昔多少动人的故事!于是,这几位诗人骚客,不是生发兴亡之感:“兴亡留今日,今古共红尘。鹳雀飞何处,城隅早自春。”便生归隐之思:“风烟并起思乡里,远目非春亦自伤。”“十载重来值摇落,天涯归计欲如何。”“祖鞭掉折徒为尔,赢得云溪负钓竿。”当然,也有引起鸿鹄之志的:“行云如可驭,万里赴心期。”“云路何人见高志,最看西面赤栏前。”
王之涣的鹳雀楼诗,确实是众芳独妍之作。诗中虽也写楼高,却非孤高;也写远眺,却不见荒远;也写黄昏,却无沉落之感;也写情思,却无伤古哀今之意。对景物,未去精雕细刻;对心境,不抒一时之感。
登楼西望:“白日依山尽”,转而东望:“黄河入海流”。但是,西望的实景却应是百尺帆樯和茫茫的汀洲云树,并望不到雄峙的西岳或秦岭;东望也看不到东海的波涛,而是“雪洗条山”。然而诗人却展开他联想的翅膀,西可观日,东可望海,这较上述诸诗不是境界更加旷远浩渺么?
但是,诗人还不满足于此际的壮观,还要“欲穷千里目”,想望得更远,看山的那边,海的尽头,于是要“更上一层楼”,登得更高,好望得更远。则此楼之高不是无有极限了么?上述诸诗只是夸张描写楼如何高出尘世,却写不出楼高与人的情意来。
从横的看如此,再从纵的看,白日要天天依山而尽,又要冲山而出;河水要时时奔流入海,永无尽时,“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因而人也要永无止境地“欲穷”、“更上”。这就一扫文人墨客的吊古伤怀之情,而给人以前进向上的力量。
王诗之所以高于上述诸诗,就在于他不是单纯地为欣赏美景而写景,也不是消极地借景来抒发一己的哀愁。他是把自己的情思完全融入到山河的壮阔境界之中,山河越显壮阔,诗人便越要“欲穷”其壮阔之美,便于越要“更上一层楼”,以饱览更高更远的美的境界。“更上”,如此上升不已,诗的意境便也随之升华到极为壮美的无限极致之中,这大概就是引人遐想神思,余味隽永无穷的艺术效果吧?难怪此诗流传千古,人人爱吟,而“欲穷”二句竟成为勉人奋发向上的警句名言了。
§§§第18节投诗、“赋得”、“草”及“王孙”辨析
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是白居易早期之作,也是代表作之一,脍炙人口久久流传。但是对于其中几个问题却历来众说不一。笔者愿就较集中的四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一、怀诗谒顾况说
《旧唐书·本传》载:
“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篇投著作郎吴人顾况。况能文而浮薄。后进文章无可意者。览居易文,不觉迎门礼遇曰:‘吾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吾子矣。’”
《唐摭言》更有补充:
“况谑公曰:‘长安物贵,居大不易。’及读《原上草》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难!’”
《古今诗语》又有较详记载:
“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投顾况。况戏之曰:‘长安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原上草》诗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唐才子传》、《白香山年谱》、《白香山年谱旧本》均有类似记述。可是万曼的《白居易传》和文学研究所新编的《唐诗选》注上,都对上述史料持异议。万曼说:“在七八八年(贞元四年)以前白居易到长安是不可能的。贞元五年以后,顾况就因为嘲谑贬官饶州,随即到苏州和苏州刺史韦应物、信州刺史刘太真往还。如果说白居易有谒见顾况的事,在长安不如说是在饶州或苏州更合事实。《摭言》记事多误,并不可靠。”
新编《唐诗选》注上更进一步推断:
“按白居易十一岁(建宗三年)至十八岁都在江南;贞元五年以后,顾况即贬官饶州,不久又转至苏州。他二人不大可以在长安相见,这只是一种传说。”
辨析:白居易从十一岁到十八岁为什么没有到长安的可能呢?我们从白氏年谱看,白居易从十六岁到十八岁一直旅居长安。这是有根据的,他在避难吴越时,曾写诗渴望去长安,“旅愁春入越,乡梦夜归秦。”(《江楼望归》)就在这一年(贞元二年)的四月,淮西牙将陈仙奇毒死了兴兵作乱的军阀李希烈,使淮西的战乱停息下来。而长安经朱泚之乱以后,也走向安定,这是他来长安的客观可能。
其次,他在《与元九书》中曾说过:“十五六始知有进士”,产生了应举求进的思想。唐代以诗文干谒权贵名人以期举荐者,成一代风气,李白上书韩荆州,杜甫上《三大礼赋》,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即在白诗中也有袖诗干谒的记载,如《见尹公亮新诗偶赠绝句》云:
“袖里新诗十首余,吟看句句是琼琚。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
因此,白居易袖诗见顾况,亦意料中事。再者,白诗集中既有他北上的即事诗,也有他在长安写的客居诗,如《长安正月十五日》诗:
“暄喧车骑帝王州,羁病无心逐胜游。明月长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
这很像他求进不利时的失望之作。所以许多研究白居易生平的传记都肯定了白居易确曾旅居长安三年,也确有晋见顾况之举。
再从顾况方面考查,他既是贞元五年以后被贬出外地,那么白居易在此前二三年拜会他的可能性当然会有的。
万曼说《摭言》不可靠。其实《摭言》也并非无中生有,在它以前就有唐人张周的《幽闲鼓吹》的记载:
“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指古原草诗)既叹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古人认为《幽闲鼓吹》一书所记虽失寥寥,而其事多关法戒,有裨考证。张周这段记述恐怕足以抵《摭言》之“多误”吧?
二、“赋得。”
有人说诗题冠以“赋得”二字,应是唐代应举的试贴诗,但是,试贴诗唐制规定很严,限六韵或八韵俳律。其实,诗题冠以“赋得”二字的诗不见得都是应试时的试贴诗。唐代几用成句为题目,常好冠以“赋得”二字,有的是拟试帖的习作,有的是诗会分题之作。这些诗作,有的遵守帖式韵律的规定,有的则自度诗意,长短不限。如白居易集中的《赋得听边鸿》就是一首七言绝句。李商隐的《赋得鸡》也是七言绝句,而他的《赋得桃李无言》就是五言六韵的俳律。
白居易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则是一首五言律诗,说这是一首拟古习作则可,要说是试贴,则是缺乏根据的。《唐诗纪事》记祖咏应试时题为《终南望余雪》,诗题既未冠以“赋得”二字,全诗又只写了四句,这还真是考试之作。交卷后问他为何不按规格写足五言六韵,他答曰:“意尽。”白居易写这首诗也如祖咏一样,没有因形式而害诗意。这是创新,所以也就成了名诗。
三、“草”的喻意
清人俞陛云的《诗镜浅说》谓:
“此诗借草取喻……诵此诗者,皆以为喻小人去之不尽,如草之滋蔓。作者正有此意,亦未可知。”但他转而又说:“然取喻本无确定,以为喻世道,则治乱循环,以为喻天心,则贞元起伏,虽严寒盛雪,而春意已萌,见智见仁,无所不可。”
《唐诗三百首注疏》诗题只标一个《草》字,注疏中完全以草“喻朝中小人”。说“离离”,是小人“相附结而不散也”;“原”,“比君侧也”。第二句言“去一小人,来一小人,言其多也。”三四句“喻言不能彻底除根,蔓延难制。”五六句言“其势直侵古道,喻残害忠良也。”“其妍接入大载,喻欺凌君上也。”最末两句讲成:“王孙,草名,萋萋盛貌。吾目忍待秋霜之日送王孙而归去,殊不知阳春一动。又且满目萋萋,是草将何日除之耶?”
辨析:
这首诗题虽不出自古诗名句,但诗的内容却是触发之于古诗。《诗经》有“有秋之杜,其叶萋萋。王事靡盛,我心伤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归止。”这是借草木萋萋思念征夫不归的诗。又如《饮马长城窟行》有“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也是由茂密的青草起兴,引起对远方人儿的情思。王粲的《王侍中》诗更有“既伤蔓草别”的句子。刘安的《招士隐》更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而谢玄辉的《酬王晋安一首》又化为“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白诗的诗题改“河边草”为“古原草”,正是因人因地而作。“古原”者,长安之乐游原也。何以言之“离离”,在《长庆集》中注曰:“离离一作咸阳。”乐游原正是咸阳(长安)之制高点,乃当时文人学士登临抒情之胜地。李商隐有《乐游原》诗:“驱车登古原。”白居易也正是在乐游原上送别好友远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