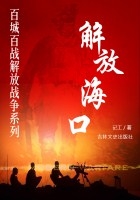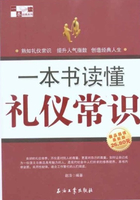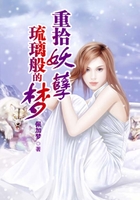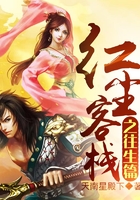就拿过去雷锋来说,我们都知道,雷锋就有一块在当时据说要接近两百块钱的手表。雷锋的时代,普通工人一个月三四十块钱工资已经很不错了,像雷锋这样的小班长,一个月的津贴当时就是六块钱,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他追求时髦、时尚。那个年代结婚的人都需要买几大件,手表算是一大件,他有一块需要花很长时间的津贴才能买到的手表。今天普通人的工资,拿一个政府公务员来说,台面上正式工资大概好几千块钱。假如一个月有七八千的收入的话,像郭长江这种级别的干部也是非常正常的,对他来说一块手表假如是一万多块钱,如果他确实喜欢,花上两个月哪怕三个月的工资给自己买一块手表,应该说是情理之中。
我们要讨论到对于专业来说,什么叫作合理消费的尺度,我觉得应该提倡一种恰如其分的体面的观念。拿我的爷爷奶奶这一辈老人来说,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往往喜欢在能够支付的范围内买高档的东西,譬如说一块怀表、一副眼镜。像我爷爷、奶奶平时从来不买在他们所能选择的范围内质量差的东西,但他们买一个东西就非常爱惜,可以用很多年,甚至我奶奶还把她现在算起来已经用了五六十年的一块老怀表给我,我看那块怀表依然走得很准。相对来说,我们生活中间有的时候形成一种貌似勤俭其实可能是非常浪费的生活习惯,我父母这一辈人,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这样的经历,特别喜欢便宜货,他们经常买很多便宜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往往并不实用,而且不耐用。我母亲有时候看到地摊上大减价卖的那些衣服也会去买,但那些衣服质量差,自己穿在身上也不舒服,穿不了两次就想扔,其实很浪费。那么,相对我爷爷奶奶这些人来说,他们一辈子自己真正做的衣服就那么几套,皮鞋就那么几双,手表就那么几块,但可以用很长的时间,相对来说,他们有了这种体面、追求档次,但是并不铺张和奢华。
过去我们有一种观念,一提起好的干部就恨不得他要衣服上补丁摞补丁,或者说衣服穿得破破烂烂,以至于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腐败分子被抓起来的时候,让大家大吃一惊,平时这个人灰头土脸,一点都不体面,结果在他家床底下掏出来成摞的钱。甚至有些知识分子为了标榜其民间性,恨不得搞得头不梳脸不洗,真是有些过了。
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到这个时候,就像郭长江,他能够戴一块一万多块钱的手表,我觉得他早一点把这块手表大大方方亮出来给大家介绍,可能就没有什么事儿了。社会也应当以一种健康的态度,鼓励我们今天的消费行为。
中国的老百姓也应该有追求恰当的体面的观念,现在就像斯科特说的“弱者武器”,中国老百姓上访都是穿得越破烂越好,以唤起社会的同情。而一百多年前的英国,看那时候的图片,哪怕农民要是请个愿,也是西装革履戴着礼帽的,这才叫不卑不亢。什么时候中国到了这么一天,咱们千万别大惊小怪。
(2012年)
让知识分子走火入魔的心灵陷阱
■
乌有之乡是我经常浏览的网站,并不是因为喜欢——这个网站讴歌“文化大革命”,为江青、张春桥平反,甚至撰文林昭、张志新死得活该,这些都让我对这些人产生生理反感——而是想通过他们,观察这个社会最极端的一群人怎么思考问题。看这个网站不禁让人感慨人性是多么的复杂。而有意思的是,这个网站的精神旗帜,是几个教授,如汪晖、张宏良、崔之元。他们能够十年如一日地干一件事,旁征博引地论证“文革”是好的,大跃进是及时的,“反右”是应该的,朝鲜是进步的。吴稼祥先生曾经评价这种习性“一个行为古怪的大夫,坚持用放大镜要在麻风病人身上寻找一块完好的皮肤,以此证明这人有自我痊愈的能力。他在美国学习这么多年,居然没有发现比《鞍钢宪法》更好的经济管理方式,也没有发现比‘文革’更有制度化潜力的‘大民主’形式”。而且看得出来,他们也确实有一批显然是死心塌地的粉丝。
吴稼祥先生所说的这种“习性”,我发现其实在一些哪怕很优秀的知识分子中都具有普遍性,比如著名的马克斯·韦伯。
虚假的韦伯命题
最近一年多以来,我把“韦伯命题”,即“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理性资本主义”作为自己思考和研究的重点,越来越感到韦伯的结论难以说服我。首先是在事实判断上,他对于新教伦理的赞美并没有太大问题,但问题是他“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态度。韦伯努力旁征博引,想证明新教伦理中“入世苦行”、“天职”观念都是除了新教伦理以外别的文化信仰中所没有的,天主教徒中没有,犹太教也没有,东方的儒家和道家中更没有。这是在我后来更加了解儒家思想以后所完全不能认同的。如余英时先生所言:韦伯所犯的并不是枝节的、事实的错误,而是关于全面判断的基本错误。我后来在温州做研究,接触一些怀有天主教,甚至佛教、道教信仰的商人,谈到韦伯的观点,他们也无不认为这是偏见,甚至感到是彻头彻尾的文化歧视。
一个学者除非是为了抗辩别人的观点,如果要主动对几种文化的比较命题下判断,自身得有一种超然的态度,最好以一个旁观者,甚至“他者”的态度来分析,否则很难不被偏见所左右。要命的是,我自己回溯韦伯命题的思考脉络,发现他存在不可原谅的逻辑跳跃和推理不严密。比如他敏锐地发现了“在近代经济里,基督教新教徒在资本拥有与领导地位上占有较重的分量”,他还发现“天主教徒的毕业生当中,从近代的、特别是为了技术研习与工商职业做准备且一般而言为了迎合市民的营利生活之故,所设的特定的学校——诸如实业高中、实业中学、高等小学——毕业的百分比,同样也远远落后于新教徒”。但在接下来的推理中,韦伯并没有过滤其他可能干扰的变量。他所尤其重点提到的加尔文教兴盛于日内瓦,那里在成为“新教的罗马”之前,就已经是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了。字里行间,韦伯似乎是为了证明新教伦理的优越性而证明其优越性。
实际上,韦伯自己是一个新教徒,而且出生在有深厚新教传统的家庭。而最为吊诡的是马克斯·韦伯的学术文章中几乎只字不提自己的思想经历和家庭背景。对于他自己怀有新教信仰这一事实,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刻意掩盖。也许可以理解为他力图在用客观的、理性化的态度来对待新教传统。这种掩饰并非没有意义,如果公开地作为一个新教徒来赞美新教,当然会有损其在其他宗教信仰者面前的公信力。
“种族主义者”韦伯
在纽约的一次研讨会上,我曾经听一个教授把韦伯称作“racist”,在强调政治正确的美国校园里,大概把人称作种族主义者是最严厉的批评了。当时我很不能接受,把我心目中灵台明澈的智者称为“种族主义者”。
不过,重读韦伯的时候,不得不承认,他的很多论述被称作“种族主义”并不过分。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他前言中就说资本主义唯独能在西方发育出来,“其中决定性关键是在遗传的素质”。这本书里韦伯作了一个在他看来比较谨慎的论述,西方发展出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是因为西方文化的优越,如果他掌握更多的资料,下一步,他就要论证是因为西方人种的优越了。
更让人觉得吃惊的,是韦伯对波兰民族表现出的,几乎不加掩饰的种族仇恨,1895年就任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韦伯发表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其中说“无论到哪里,这些波兰人都会沦为经济和社会地位最低的阶层”。他认为,与日耳曼人相比,“两个民族在心理和体制上的种族差异使他们对经济和社会条件的适应能力不同”。“像波兰人这类斯拉夫民族,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历史形成,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期望都较低。波兰人也就这样在东部战胜了德国人”。
韦伯作为一个国民经济学教授给出的政策主张,也充满“阴谋论”和“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论调,他的经济主张是强化国家干预,甚至建议“要阻止斯拉夫民族涌进东部,就必须把东部大量土地收归国有”,他认为所谓经济自由化,和开放市场的政策最终决定于“是否有利于我们全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利益,以及是否有利于我们民族的担纲者——德国民族国家”。
为什么这样一个智慧而又真诚的人,在他一直提倡的清晰冷峻的理性中会表露出一些像种族主义这样非常不理性的倾向?
进一步了解韦伯的生平和他的著述,会感到他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拧巴”。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他如此强烈地推崇苦行甚至禁欲主义,而他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过着放荡的生活,是一个“粗鲁的,喝啤酒,爱决斗并且吸雪茄”的学生,而一直到他父亲去世前,韦伯都没有停止和父亲之间激烈地争吵。D.G.麦克雷觉得,他的政治立场也是这种情结的延续,韦伯对待德意志帝国的那种态度——既赞美,顺从,又不愿苟同——不仅反映了他对父亲的态度,而且是他这一态度的一种发展。他渴望这个国家进行改革或者干脆寿终正寝,尽管他同时又发现这个国家还有那么一种值得赞美的力量。
韦伯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他试图追求的理性的世界,是他作为学者所倡导的价值中立的科学世界;另一个世界,是他无法抗拒的,深入他潜意识甚至基因的情感依恋的世界,比如对德意志民族的自豪感,对波兰民族的厌恶,对于新教的感情。
显然韦伯希望做一个没有偏见的客观的学者,这也是为什么在韦伯的学术文章和演讲中,几乎只字不提自己的倾向和思想背景。他力图扮演一个“价值中立”的形象,却无法避免,越是用心压抑,越是会甚至更强烈地表现出来的信仰和偏见。
救救教授吧
人格分裂并不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只要有足够的自省意识,几乎每个人身上都会找到人格的自我冲突,只是程度有差别。很多人如果对自己并不较真儿的话,两种甚至更多重人格可以同时存在,人格分裂而互不冲突。
但是,对以思想作为志业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人格分裂带来的折磨就会非常痛苦。对韦伯来说,他似乎是想用理性化来掩盖自己的本我倾向,结果却是他的本我借助理性的包装突破而出。
这个现象不仅在韦伯身上明显,相信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有这种倾向,而在很多德国杰出的、号称严谨的知识分子身上更能看到影子,而海德格尔,一个天主教徒后来索性成为纳粹的辩护士。
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缺陷不像一个卷着袖子上阵的红卫兵或者纳粹冲锋队员,他们的非理性很容易被识别,而知识分子却往往会把其非理性深深地掩盖在理性和学术的包装之下。红卫兵和纳粹冲锋队只会大声喊口号来表达自己立场的坚定,而一个知识分子会写出厚厚的著作,以庞杂的引经据典,以客观的姿态来论证其实像红卫兵一样充满偏见甚至邪恶的立场,并巧妙地掩饰自身的矛盾。
今天出来一些年轻人做新红卫兵和新纳粹,并不太可怕,常常是一些头脑简单的情绪爆发,浇两瓢冷水就好了;而一个教授,一旦走火入魔,爱上“文化大革命”,把一些偏执的个体经验,转化为学术追求,除了指望其内心的自省和超越,别人都无法帮得上忙。
模仿鲁迅绝望的口吻,我想说“救救教授吧”!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