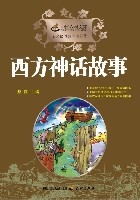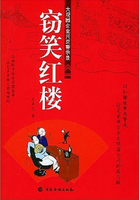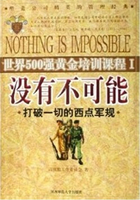“无债不成父子,无冤不结夫妻。”三扁一直固执地认为,她与身边这个冤家今生结下的宿怨,不是前世的因,而是今世的果。她爹齐德福辛勤耕耘了半辈子,她娘这块自留地就是不生长半当中结棒子的玉米,齐刷刷一地头顶上开花的红高粱。而且还不伦不类地造就了她这个雌性和雄性特征各自参半的二杆子。从生理角度上看,三扁是一个发育完全正常的女性,但从体形特征上看,她是那种让爷儿们一看就生畏的五大三粗的女人。村里的小青年没事喜欢拿她的长相逗笑话,说三扁浑身的特征有三粗并三大:也就是腰身粗,眉毛粗,嗓门粗;还有个头大,手脚大,力气大。女人腻歪歪靠在男人肩膀上,那叫小鸟依人;三扁一趴到男人的肩膀上,怎么看怎么像老鹰叼小鸡。更有意思的是,三扁偏偏喜欢在男人面前扭捏作态。稍微有点文化的人很容易联想到东施效颦典故中的那个丑东施。尽管她学起来挺卖力的,但终是弄巧成拙,笑料百出。
在那个精神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山里人最好的消遣方式就是踩踩墙脚根儿,捉捉对子什么的。要是捉对子能捉到一对野鸳鸯,那小小的村庄可就热闹了,茶余饭后不嚼它个月数来天,绝不肯吐出渣来。三扁踩墙脚根,是跟比她大几岁的大翠学的。大翠要叫三扁,是因为三扁生得人高马大,脚底不用垫石头,趴到窗户根上就能舔破窗户纸,窗户纸一破,屋里就有股子骚味儿传出来;摸着黑不用长眼睛,单用鼻子也能嗅得见。这时的三扁常常是紧吸着鼻子,把两只大招风耳朵直楞楞地竖起来,听到绝好处,低下头兜住大翠的屁股一把将她摁到窗台上。有时候自个儿听到入神时,也有把大翠忘了的时候。这时候急得个头只有一米五的大翠直跺脚。跺一会脚,又怕耽误了好事,连忙摸黑去搬石头。由于大翠总是慌不择石,搬来的石头不是上头圆就是下头尖,人还没立稳,就看脚底一摇晃“忽嗵”一下塌了。随着窗外“忽嗵”一声响,屋里顿时悄没声息了。
回来的路上三扁直怨大翠,说都怪你都怪你,一场好戏让你一声给“忽嗵”没了。大翠一撅嘴:哼!谁让你不顾伴儿呢。”当晚二人不欢而散,各回各家。
此时,回到家的三扁像头发情的草驴野性正浓,就想跟她男人操练一遍,可是男人总不配合她。她还没哼唧一声呢,男人就皱着眉头说:这是谁家的猪拱食呢?”三扁一听就生气,光着屁股跟他在床上打仗。可惜男人一点斗志都没有,无论演习还是打仗,男人全不配合。三扁气急败坏地一头撞过去,把男人结实的胸脯撞得“嗵嗵”响,男人紧闭着眼,都懒得看她。三扁愈发气得磨牙:三狗子,你个野种!你当这是造骡子呢!”三扁急了就骂他是野种,其实他不是野种,是他爹在野地里下的种,这话还是她爹齐德福说的。只要她一骂野种,男人就一把推开她独自走了。丢下三扁一个人在屋里绝绝地骂:野种野种野种!还不如我家的那头黑叫驴呢,黑叫驴闻到草驴的味儿,还知道突噜突噜打几声响鼻呢,还知道啊噢——啊噢——地叫两声呢,还知道把蹄子刨得噔噔响呢……”
三扁平生最恨一个人。都说女人的嘴,催命的鬼,灵应着呢。恨来恨去,咒来咒去,愣把个狗妹给咒死了。本来三扁哭丧,那在牛岭村也是一绝,像唱西皮流水似的,你要单听这腔调还是蛮好听的,就是没有多少感情色彩在里面,让人感觉太虚假。三扁每次去到亲友的丧棚底下哭丧的时候,男人总是厌恶地走开了。但是这一次,三扁顾不上做作了,她是真想痛痛地哭一场,哭她恨了一辈子的狗妹。狗妹终于在她的咒骂声中走了,她反而恐慌起来。因为她知道,她男人的心从此死了,死得让她半点希望都看不到。绝望之际,她扑向了男人怀中的狗妹,她的嘴巴刚撑圆了喊出一声“阿——”,阿黄的黄字还未出口,男人便伸出胳膊挡住了她扑上来的身体。她扑得太用力,当男人的胳膊横空拦过来时,她竟被他强大的力量弹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愣怔了片刻后,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她把刚出口的“阿”改成了“啊呀”。在一声叫板之后,她又拖着长腔唱了起来——
啊呀——
我的没活够的妹妹呀
我的苦命的妹妹呀
你这一走可苦了我呀
我哭一声呀、我唤一句
倘若妹妹你能醒转来呀
我情愿、我情愿……
她在“我情愿”这里卡了壳,偷眼瞄自己的男人。倘若她男人怀里的狗妹忽然地醒转来,她能够喊出一声,我情愿把他还给你吗?她不能!但是,男人这一次没像往常一样皱着眉头说她的声音像猪一样难听。男人好像根本没有听见她的哭声,他仍然紧紧地抱着怀里的狗妹,深情地望着那张让他永远都看不够的脸。
就是这张永远让男人看不够的脸,把他带到了不知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今生,还是很遥远很遥远的来世。不管是今生还是来世,故事的开头和结果都是一样的:在苍穹遁入无尽的黑暗,在黎明破开的第一抹腥红中,他知道,有个女孩儿为他而生。这个女孩儿一生下来就是他的亲人——永生永世的亲人。不光是这辈子,还有下辈子,再再下辈子。为了他这个小亲人,他愿意为她做一切,陪她哭,陪她笑,陪她看夕阳,陪她唱一首天不荒、地不老的情歌——
苦藤上开花结苦瓜
爱上妹妹不怕人笑话
不抬花轿来不骑马
摘朵牵牛吹喇叭
一声声欢哟一声声喜
一声声妹子哥想你
晚上想得心尖尖痛哟
白日里等不得日偏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