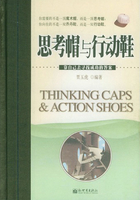建国后,朱元璋即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整套监察机构。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罢御史台。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置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陈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大狱重囚会鞫于外朝,偕刑部、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
都察院下设浙江、河南、广东、广西、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四川十二道监察御史。各道监察御史的职责为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军队行动则监军纪功,各以其事专监察。并且对御史台出巡有具体要求,明代御史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职权行使,颇有雷厉风行之势,并且权限范围极广,每一御史都有权对内外所有机构、官员进行弹劾,并直接对皇帝负责。
除都察院系统外,对应于中央六部,朱元璋还创立了拥有独立监察权的六科给事中,六科即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均设都给事中一人,左、右给事中各一人。给事中,吏科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六科职责为掌侍从,规柬、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六科给事中的创置,对于地位和职权都已提高的六部,起着钳制的作用,同时也分解了都察院的监察权。都察院和六科之间有一定分工,但并不绝对。给事中同御史之间,亦可互相纠劾。
明代的司法机关较前代也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其中央司法机关的刑部、大理寺和拥有一定司法权的都察院与前代不同。明代,刑部掌审判,大理寺则一般不再掌管审判,而专掌复核。因审判归刑部,事务性工作大增,因而刑部规模也相应扩大,由前代的四司扩充为十三清吏司,分别受理地方上诉案件,以及审核地方上的要案和审理中央百官的案件。明代对罪犯的处罚分死、流、笞、刑、徙几等,刑部有权处理流刑以下案件,但定罪以后,须将罪犯连同案卷送大理寺复核。死刑案件必须奏请皇帝批准。刑部的审判和大理寺的复核均须接受都察院的监督。
大理寺为明代中央司法复审机关,设有大理寺卿一人,左、右少卿各一人,左、右寺丞各一人。所属有司务厅和左、右二寺。案例审理完毕,凡未经大理寺复核者,诸司对罪犯均不得擅自发遣,否则即追究责任。
为保证案件审理无误,明代中央还建立了“三法司”联合审判制度。三法司即指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凡遇有大狱重囚,均由三法司联合审理,称“三堂会审”。
地方司法机构,如府、县一级仍与行政机关结合在一起,由知府、知县等地方行政最高长官掌握辖区司法审判工作。省级则专设司法机关——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有权处理徙以下案件,徙以上重案就必须报送中央刑部审理。从司法审判系统看,明朝自县、府、省以至中央刑部、三法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最高司法权则仍属皇帝。
此外,明朝特设的厂、卫特务组织,虽然不是正式的司法机构,但也被皇帝特令兼管刑狱,赋予巡察侦缉、专理诏狱和审讯的权力。特务司法是明代司法独具的特点。
断章取义,大兴文字狱
朱元璋虽然明白治世用文的道理,但他对读书人并不是没有猜忌,朱元璋尤其对元朝遗臣常常持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态度。在朱元璋这个新皇帝和元朝的旧臣之间总是有种微妙的关系。
元朝的士大夫文化人,他们如果要出仕新朝,就是对元皇帝的背叛,按照封建礼仪,就像再嫁的妇人一样失节;倘要守身不出,拒不应召,就是对新皇帝的蔑视,很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朱元璋既要他们忠贞,又要他们从命,这实在是强人所难。
危素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老臣。危素是元代翰林学士,精通史学。元朝灭亡后,被明朝政府继续留用,在翰林院供职。当时也很受朱元璋器重,但是后来越来越受到猜忌。
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危素应召到大内东阁,朱元璋听到脚步声,问道:“是谁?”危素回答:“老臣危素。”朱元璋随口说道:“我只道是文天祥。”危素感到羞辱,却又无法反驳,只能跪在地上连连叩头。
不久,朱元璋对这个年近七十的老翁再加羞辱。元顺帝有一头会舞蹈朝拜的驯象被送到南京。这一天,朱元璋朝会群臣,让大象跳朝拜舞。大约是整个环境条件改变,这头大象就是不跳,只是伏地不起,大有不事二主的气概。朱元璋就成就了它的“忠义”之志,命人把它牵出去杀了。然后,拿来两块木牌,一块写着“危不如象”,一块写着“素不如象”,挂在危素的两肩上。这帮御史大夫见皇帝如此,便一哄而上,纷纷上书,说危素是亡国之臣,不适合做皇帝的侍从。朱元璋便打发危素到和州,为元朝忠烈余阙去守庙。危素不久就因为羞愤而病死。
正是朱元璋的这种心理,加上武臣对文臣的成见,终于导致了明朝一场非常严重的文字狱。
在武将看来,明朝的这份天下是他们在沙场征战中用血肉换来的。皇上却常在他们面前反复说,乱世用武,治世用文。武将们听了心里非常不高兴,心想:这些人在皇帝面前摇头晃脑哼上几句,就成了皇帝的座上宾。但是,不管是一般武将还是勋臣权贵,谁也不敢贸然在皇帝面前说什么。但是,他们仔细观察着朱元璋的举动,猜测着他的心理。
一天,朱元璋大宴群臣,并让群臣当场做诗。大家正在冥思苦想做什么的时候,有一个武臣突然高声说道:“我先来几句。”于是念道:“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筵宴正阳宫。大明日出明天下,五湖四海春融融。”群臣立即明白,这是皇帝特意安排的,于是都不敢再把自己的诗拿出来。这件事使武臣们很得意。他们渐渐明白了皇帝对文化人用尽管用,但并不信任。不管朝里的还是朝外的文臣,几乎很少有人做官做的长的,常常是没几年,就被频频升降调换,不少人朝着紫袍,晚服囚衣。他们这批老兵旧将,尽管经常被训斥,但高的成为皇亲国戚,低的也能按时升迁,子孙世袭,禄位常在。勋臣们便尝试着在皇帝面前讲文臣的坏话。
明太祖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的一天,几个武臣又向朱元璋说道:“诚如皇上教诲的,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只是这些文人善于用文字骂人,不知不觉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
朱元璋心里一动,说道:“是吗?”
武臣接着说:“当年张九四原本是礼重文人的。他请文臣给起个大号,文臣就给起了士诚这个名字。”
朱元璋说:“这个名字不是很好吗?”
武臣们回答说:“《孟子》有‘士,诚小人也’这样的话,岂不就是骂他张士诚是小人吗?张九四一辈子蒙在鼓里,哪里知道上了这些读书人的当?”
朱元璋命人取过《孟子》一查,果然有这句话,不觉把脸一沉,说道:“我知道了,你们去吧!”
朱元璋越想越觉得疑心,越想越觉得这些文臣们奸险狡诈。
朱元璋认为,越是文人写的歌功颂德的文字,越是陷阱,越是不能大意。从此以后,朱元璋十分注意臣下的奏章表笺,仔细阅读,并展开联想,只从坏处琢磨。果然发现,许多地方都有和尚、盗贼之类的文字,好像都与自己有关,越疑心就越像背地里骂自己,就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好像是在损自己。加上许多文人持不合作的态度,更增加了朱元璋对一般文人利用文章反皇帝的疑心。朱元璋用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凭个人的文化素养来读大臣的文章。只要有触犯忌讳,不合他的意思的,便派锦衣卫把作者押来,杀头泄愤,这就是朱元璋时代著名的文字狱。
朱元璋读表文,把所有的“则”都念成“贼”,十分恼怒,说:“则音贼,骂我作过贼,用心险恶,一律处死。”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因文中有“作则垂宪”一句,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祝万寿表》,因文中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被杀;福州府学训导林伯壕为按察使撰《贺冬至表》,因文中有“仪则天下”一句被杀;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吏使作《正旦贺表》,因文中有“建巾作则”一句被杀……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文中没有“则”字,但有“睿性生知”一句。朱元璋看了,把“生”字破读成“僧”。于是大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立即处斩。”
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因文中有“遥瞻帝扉”一句,被杀。朱元璋说:“帝扉就是‘帝非’,他诽谤朕不是,乱言惑众,不斩留他无益。”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其中有‘取法象魏’一句,朱元璋读成“去发象魏”,说:“去是落发,说我是向秃子,立即处死。”毫州训导林云为本州作《谢乐宫赐宴笺》,因文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一语,被杀。朱元璋认为“式君父”就是“失君父”,这是诅咒王朝,不杀还留他做什么?德安府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文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两句。朱元璋说:“‘有道’就是‘有盗’,‘青门’就是‘和尚庙’。文人变着法儿地揭我短,讽刺我。”于是下令,一律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朱元璋看文章,也从鸡蛋里挑骨头,对遇到自己不理解的词语、句子,也认为是别有用心,对这些作者必杀无疑。
陈州州学训导为本州作《贺万寿表》,其中有“寿域千秋”一句,朱元璋念不出花样来,却认为此句恶毒,还下令把做表的人杀了才放心。象山县教谕蒋景高因为表、笺笔误,被逮至京师处斩。
明代首屈一指的诗人高启善写豪宕凌厉、奔放驰骋的歌行体诗,为世人所推崇。高启作了一首《题宫女图》,其中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朱元璋看了,认为是讽刺他,怀恨在心,寻找借口把高启逮到南京。高启自问无愧,一路吟咏,有“枫桥北望草斑斑,十去行人九不还”、“自知清澈原无愧,盍倩长江鉴此心”的名句。到京后,未加审问,高启便遭到腰斩,当时他才三十九岁。高启的弟子吕勉悲愤之极,遂迁居城外,绝口不谈读书做文章的事。到明成祖永乐年间,吕勉才将高启的文稿刊刻传布。
就这样,朱元璋通过严酷的文字狱控制了文人儒士,让他们乖乖按照大明朝的要求做事,进一步加强了朱元璋对全国的控制。
党同伐异,诛杀功臣
胡惟庸案是明太祖洪武四大案之一,死于此案的公侯爵位者近20人,被诛杀者有3万人之多。按说朱元璋生性多疑,平生最忌别人对自己有隐瞒,但怎么会发生如此一个案狱连绵:酿成一场骇人听闻、空前绝后的浩劫呢?
胡惟庸,定远人,不但是李善长的同乡,而且也算是朱元璋的同乡。胡惟庸虽然跟随朱元璋挺早,但一直不得志。胡惟庸从最低的元帅府奏差、迁宣使、宁国主簿进知县、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经过李善长的举荐,胡惟庸被调为太常寺少卿,又进官至太常寺卿。到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时,胡惟庸入为中书省参知政事。次年正月,李善长告老,嗜酒而无能的汪广洋升右相,胡惟庸为中书左丞。汪广洋受淮西集团的排挤,于明太祖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正月左迁广东参政,胡惟庸得以独揽大权。
胡惟庸没有李善长那样的大功,但是却有李善长那样的专断。胡惟庸贪财而露骨,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胡惟庸打击每一个不迎附自己的人,只要他不顺眼、不顺心的,便置之死地而后快。
胡惟庸深知自己做得太绝,被朱元璋抓住把柄将会处以极刑。于是,胡惟庸用手腕在几年之中,便把许多朱元璋的功臣拉上了自己的贼船。
胡惟庸为相七年,大权独揽,专断独行,使朱元璋觉得大权旁落,除了翦除,别无选择。于是,朱元璋开始找胡惟庸的茬儿,谁知胡惟庸不但不收敛,而且更张狂。在明太祖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九月胡惟庸又私藏占城国贡品,结果被中官发现。御史中丞涂节又告发胡惟庸,说他密谋害死刘基……令朱元璋龙颜大怒,赐胡惟庸死。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当朱元璋对胡惟庸案深挖,以至于新证、人证的不断扩大,牵连众多的功臣,诛杀了多年才淡息下来。
胡惟庸原以为被自己拉下水的人越多自己也就越安全,哪里会想到朱元璋竟能真的诛杀这么多功臣。从这个案件的结果来看,怪就怪胡惟庸持权太重,架空了朱元璋,这是朱元璋所不允许的。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罪状杀了胡惟庸,趁此机会取消了中书省,由他直接管理,集大权于一身,成为一个真正的独裁者。
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宣布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在情理之中,要以它来罗织一个“胡党”,株连一大批功臣宿将却是为了把罪网罗织得更大。在胡惟庸死后,朱元璋的黑暗面状逐步升级,显然是要置那些“胡党”于死地。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虏南倭”,由此着手制造罪状最具杀伤力。于是,胡惟庸死后罪状升级为“通倭通虏”,用它来株连开国元勋。胡惟庸的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但受胡惟庸牵连被杀的大批功臣完全是无辜的。胡案实际上成为朱元璋整肃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认为心怀怨恨、行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党”的罪名,处死抄家。
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即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罪状又升级为“谋反”。朱元璋安排亲信精心策划,唆使李善长的家奴卢促谦无中生有地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看得出来,朱元璋要借此除掉李善长,朱元璋冠冕堂皇地说:“(李)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77岁的李善长及其一门七十余人被杀,纯属冤案一桩。一年以后,解缙上疏为其申冤,他起草的《论韩国公冤事状》,由郎中王国用冒死呈上,大意是:李善长为陛下打天下,是第一勋臣,假使帮胡惟庸成事,也不过如此,况且他已经年迈,根本没有精力再折腾,何苦如此!朱元璋看了以后,无话可说,可见他也默认是枉杀了李善长。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策划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一场“肃清逆党”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株连被杀的功臣及其家属共计达三万余人。为了平服人心,朱元璋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株连蔓延达数年之久。连一向与胡惟庸关系疏远的“浙东四先生”也未能幸免,亦以“胡党”被杀,宋濂的孙子宋慎也牵连被杀,宋濂本人则贬死于四川茅州。
后世史家对胡惟庸党案颇持怀疑态度。王世贞就对胡惟庸“谋反”之说表示难以相信;谈迁说的更加明确:“惟庸非判也”,乃“积疑成狱”,可谓一语道破。
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在常遇春麾下勇敢杀敌,所向披靡,堪称常胜将军,战功显赫。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朱元璋升蓝玉为大将军,两年后晋封谅国公。皇恩浩荡之下,蓝玉忘乎所以、骄横跋扈,使朱元璋感受到了将权与皇权的冲突。于是,朱元璋又精心策划了一场大屠杀,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又扣上了“蓝党”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