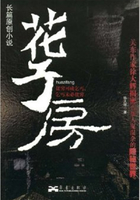邵士喜说:“省长就这么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邵士喜说这话的时候,高银凤已经脱鞋上炕,倚在了被垛子上。邵士喜伸过手去,紧紧握住高银凤的手,握了一会,又摇了摇,还是不肯松开。高银凤就说:“看把你兴得。”
邵士喜依旧满脸的兴奋,他唾沫飞溅地说:“省长握完我的手,又在我肩上拍了两下。”说着,他又探过身去,使劲在高银凤肩上拍了两下。高银凤被他拍得不由地呲了呲牙。高银凤说:“看把你兴得。”
邵士喜也脱鞋上炕,坐在离高银凤一咋宽的地方,眼珠子骨碌地转着说:“你知道我们每顿饭吃几个菜?”
高银凤笑得眯缝了眼,说:“几个?八个。”
邵士喜轻蔑地扫了她一眼,说:“八个?你再猜?”
高银凤猜了几分钟,邵士喜嫌她猜得慢,就替她说:“你可能猜十二个吧,错了。十六个。”
高银凤咂舌瞪眼地仰望着邵士喜,说:“看把你美得。过去有钱人家过年,也就四碟八碗,你们就吃十六个?你说说,这十六个菜都是些啥。”
邵士喜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光顾吃了,也不知道吃了些啥。对了,有鱼,你知道吧?”
高银凤说:“鱼?鱼是啥东西?”
邵士喜不屑地,说:“鱼,你都不知道。不过,我也是第一次吃。不好吃,味道咱吃不惯,腥不叽叽的,我吃了一口,还吐了。”高银凤说:“你真傻,我听人说,越是不好吃的,越贵,你真傻。”邵士喜又说:“大会完了,又开座谈会。省长坐得就离我这么近。”他伸开手划了一下,又说:“省长说,你叫啥名字呀,我说,我叫邵士喜。省长高兴得直点头。说好哇,大庆有个王进喜,我们煤矿有邵士喜。省长又说,王进喜说过一句豪言壮语,叫什么,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邵士喜同志,你有没有豪言壮语呢,会场上的人都看着我,我急了,就说有。省长就笑眯眯地望着我,说,邵士喜同志,那你快给大家说一说,我当时傻了眼,我那有什么豪言壮语呢。可省长看着我,全场的人都望着我,我不说也不行了。我就咬了咬,说煤矿工人一声唱,西方不亮东方亮,我刚说完,省长就给我鼓掌,接着全场的人都给我鼓掌。鼓了一会,省长说,邵士喜的豪言壮语好哇。西方不亮东方亮。太有意义了,西方是资本主义,它们是一片黑暗。我们东方是社会主义,亮堂堂呀。于是,大家又鼓掌。”
高银凤说:“你这不是骗省长么?”
邵士喜朝门口看看,见没有人,就说:“你咋这么说话呢。不是我要骗省长,省长就这么坐在我跟前,看着我呢。”
高银凤说:“说了半天,你的奖品呢。”
邵士喜跳下地去,从布包里拿出一张奖状,一个茶杯,一件背心。他把这些都递在高银凤手里。高银凤说:“就这些?”
邵士喜说:“可不就这些。”
高银凤便惋惜地,说:“还不如给五斤粮票哩。”
邵士喜说:“你的觉悟咋这么低,这是用粮票能买来的。”
高银凤想想,说:“也是”。
邵士喜说:“解放呢?”
高银凤说:“上学去了,老师昨天又来了。说不行,明年还想让留一年级。”
邵士喜说:“他已经上了两年一年级了。这个龟孙子,也是下井受苦的料。真是生成教不成,合作呢?”
高银凤说:“领上跃进耍去了。还是合作行,还没有上学,就把解放的课本全背下了。”
邵士喜就笑了,说:“你看看,我说合作行吧,他刚生下,我就看出他行,他一直不说话,可心里做事呢。”
高银凤瞥了他一眼,说:“屁,你一直说他是野种哩。”
邵士喜“嗬嗬”地笑了,说:“我现在倒怀疑解放是野种了。”
高银凤脸就耷拉下来,拍拍自己的大肚子,说:“他们都是野种,这下你满意了。”
邵士喜便翻了翻眼,说:“你看你,人家刚开完劳模会回来,你就这么说。”
高银凤说:“你快给我捎信去吧,我这,说不定那天就要生呀。”
邵士喜说:“叫玉凤来伺候你月子来吧。”
高银凤说:“叫月凤来。”
邵士喜说:“还是叫玉凤来。月凤毛手毛脚的,不稳重。”
高银凤瞪了他一眼,说:“你就惦着玉凤,快成了白永祥,吃着碗里的,盯着锅里的。”
邵士喜又“嗬嗬”地笑了说:“我是劳模哩,现在还是省劳模哩,我去上班去呀。”
高银凤说:“你刚下车,连饭还没吃一口。”
邵士喜说:“我拿块窝窝就行。按说,我一下车就该去井口,我怕你生了,才回来看看的,我走呀。”说着,去锅灶里取了块窝窝,出门走了。
高银凤在他背后唠叨,说:“看把你兴得,一当劳模,连婆姨也不管了。”
高银凤腆着肚子也跨出门槛,她老远就看见排房那头有几个女人站着说话,蹒蹒跚跚地走过去了,她先“呀”地叫了一声,然后就高声说:“你们知道不知道,省里开劳模会每顿都吃十六个盘盘碟碟。”
那几个咂咂嘴,说:“十六个?能吃了那么些。”
高银凤说:“咋吃不了,我家士喜一个人就吃那七碟八盘,你们知道他吃甚来,鱼,你们知道鱼么。”
有个女人说:“咋不知道,就是河里游的虫虫呗。”
高银凤盯住那女人看了半天,有些泄气,说:“你知道呀,我以前可是没有听说过。省长和俺士喜握手来,握住还不放。”
合作领着跃进从汾河滩里灰头土脸地回来了。那些女人看见合作就使劲地眨巴眼,脸上就没有了好奇。
有一个女人走了,接着又有一个女人走了。高银凤没有看见合作,还是说:“省长还拍俺士喜的肩膀来。”
一个女人眨巴着眼说:“真的?”
高银凤说:“我还能骗你。”
合作的眼光就在剩下的女人脸上来回巡望。
又有一个女人走了。
高银凤接着说:“开会的时候,省长就坐在俺士喜身边。”
合作看着娘说:“你别说了,回去吧。”
一个女人往后退着,说:“你家合作让你回去呢。”
高银凤回头看了一眼合作,说:“他让我回去就回去,我倒听了他的。”
一个女人往后退着说:“银凤,你回吧,你家合作让你回去呢。”
那女人又说:“你家合作眼神太毒了,这孩子也真是怪了。”
合作看着娘说:“你不用说了,回去吧。”
最后留下的一个女人,突然“哎呀”了一声,说:“我锅里还熬着米汤哩。”说完,急急慌慌地走了。
高银凤望着她的背影,对合作说:“她鬼说呢,刚才就不熬得了。她们是见不得人家得势哩。”
合作又说:“娘,你别说了,回去吧。”
高银凤说:“你们先回,娘还要走走哩。”
邵士喜很长时间没有去白永祥的办公室了。白永祥传他去的时候,他心里象塞了只鸽子“扑腾扑腾”跳个不停。他边往井口走,边自言自语:“我最近没说错什么话吧,没有呀。我最近没做错什么事吧,没有呀。那他叫我干啥。”他就驼着腰进去了,走进去就站在门口,一脸受了委屈的样子。白永祥还在看报,邵士喜心里说,看你娘的球哩,你识几个字,老子能不知道。他就咳嗽了一声。
白永祥扔下了报纸,抬起头笑着向他招手说:“你站球得那儿作甚,坐球下吧。”
邵士喜便知道自己这一段没说错话,没做差事,他往椅子那边走,发现白永祥的椅子也变了,就“呀”了一声,说:“白主任,你也有了沙发?那我就不敢往上坐了。”
白永祥看着他还穿着下井的衣服,就说:“你咋还没换了衣服?”他皱皱眉头,指指门口的一个木凳,“那你坐这儿吧。”
邵士喜就又退回到门口的木凳上。刚坐上去,又站了起来,圪蹴在地下。白永祥看见了,也没说话。
白永祥拿起电话说了一句什么,又把电话放下,说:“一会儿记者就过来了,人家要采访你。”
邵士喜说:我有球啥采访的?
白永祥的脸色便严肃起来,说:“右派向党进攻,记者要听听煤矿工人的态度。”
邵士喜惊得险些跌坐在地上,说:“右派是什么东西?”
白永祥猛地拍了一下桌子,说:“邵士喜同志,你怎么连右派也不知道呢。你还是劳模哩,就这觉悟。”
邵士喜耷拉下头,说:“白主任,你批评我吧,我的觉悟真是太低了。”
白永祥说:“我当然要批评你,我听说你婆姨走东家,串西家,说你在省城吃十六个盘子了,说你连鱼也吃过了。看看,你骄傲得尾巴要翘到天上去了。”
邵士喜脸涨得象猪肝一样,说:“我回去扇她,我一回来,她就非要问我开会吃什么了。”
白永祥说:“扇她到不必要,这主要暴露了你的骄傲自满情绪,你这个劳模,是我树起来的,可不要给我丢了脸。”
邵士喜忙说:“我不会给白主任丢脸,肯定不会。”
他们说话的时候,记者已经进来了,记者戴一幅白眼镜,左手拿一支笔,右手拿一个本,很有知识的样子。
白永祥和记者很热烈地握手,记者问:“那个劳模来了?”
白永祥就指指蹲在门口的邵士喜。记者就急慌慌地跑过来,热烈地和他握手。
记者说:“你坐呀,咋在这儿蹲着呢。”
邵士喜便摆手,说:“蹲着舒服哩,我就习惯蹲着。坐下反而难受人哩。”
白永祥说:“就让他蹲着吧,你不知道,井下工人就爱蹲。”
邵士喜心里说:“放你的屁哩。井下工人就不知道坐沙发舒服了。”但说出来的却是,“是的,是的,我们下窑的人就爱蹲着。”
记者打开本,又拨出了笔,热情地望着他,说:“师傅,贵姓?”
邵士喜忙说:“贵姓甚哩,我叫邵士喜。”
白永祥介绍说:“邵士喜同志是省劳模哩,他是我们煤矿工人的代表。”
记者不停地点头。记者说:“邵士喜同志,我这次来,主要是想听听工人同志对反右的态度和看法。邵师傅,你说说吧。”
邵士喜又挠头,苦笑着说:“我连右派是球啥东西也弄不清哩。”
记者一怔,窘困地盯着白永祥。
白永祥站了起来,不满地看着邵士喜,说:“我刚才不是给你说了,右派要向党进攻么。”
邵士喜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忙说:“我们工人最恨的就是这些右派了。他们和国民党,闫锡山一样坏哩。”
记者在本上飞快地写着,一边鼓励他道:“邵师傅说得好,你继续往下说。”
白永祥也笑着说:“士喜,你不是会说顺口溜么,你给记者同志说两段。”
邵士喜又挠挠头,说:“我那顺口溜,瞎编呢,让记者同志笑话。”
记者说:“邵师傅,你说,你说。”
邵士喜低头想了想,然后咳嗽一声,说:“记者同志,你千万别笑话我们这些大老粗。”
记者忙说:“那会呢,我们就是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哩。”
邵士喜又看着白永祥,说:“那我就说了。”
白永祥说:“你快说球吧。”
邵士喜就一边眨咕着眼,一边念道:
“右派右派你真坏,白得说黑黑说白,煤矿工人不答应,一锅端掉臭妖怪。”
记者惊得瞪起了眼,忙说:“邵师傅,你说得慢一点,让我记下。”
邵士喜就又缓慢地说了一遍。
记者记录完,拍着手里的本子,不迭声地赞叹:“好,说得好。我们工人阶级就是觉悟高,有水平。”
白永祥咧着嘴笑着说:“士喜,你再给记者同志来一段。”
邵士喜也喜滋滋地笑着,说:“那我就再来一段,记者同志,你记吧。”
“右派分子野心狼,妄图推翻共产党,煤矿工人不答应,一锹攉到他太平洋。”
记者写完,又是一番感叹,说:“这是什么,这是诗呀,邵师傅,你是煤矿诗人哩。”
邵士喜“嗬嗬”地笑了,连忙摆手,说:“甚球诗人哩。在井下瞎编着玩呢。”
记者说:“这两首诗我拿回去发表,稿费我给你寄来。”
邵士喜看着白永祥,说:“啥叫稿费?”
白永祥就看记者。
记者笑着说:“就是给你钱哩。”
邵士喜“哦”一声,说:“还给钱哩?”
记者说:“这是你的劳动报酬么。”
邵士喜忙问:“能给多少报酬?”
记者说:“给六七块吧。”
邵士喜猛劲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说:“呀,六七块呢。明日我就坐在家里多编几首。”
白永祥瞪他一眼,说:“看把你兴得,你以为随便编两句,就给你六七块。梦你的吧,编得有意义,才给钱呢。记者同志,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记者说:“是,是。编得有政治意义,报上才给你发表哩。”
邵士喜顿时象泄了气的皮球,软软地靠在了墙上。记者再问他,他就说得少了。
记者走后,白永祥拍了桌子,说:“邵士喜,我看你这个劳模是不想当了。”
邵士喜一下圪蹴在地上,他仰头望着白永祥,感觉到自己脑袋里撞钟似的“嗡嗡”响。
白永祥很生气地说:“你就知道钱,刚编了两句顺口溜就想着挣钱,就这觉悟。”
邵士喜哭丧着脸,说:“白主任,我是说着玩哩,我要那钱干什么,国家给我的工资也够我活了。那稿费我不要了,谁要给谁吧。”
一个月以后,白永祥又把邵士喜叫到办公室,说:“有个事,要和你说,士喜,给你一个右派吧。”
邵士喜又惊得跌坐在地上,他结结巴巴说:“白主任,我没做错什么事吧。”
白永祥“嘿嘿”地笑了,说:“看把你吓得,你以为让你当右派,你还没那资格哩,右派都是有文化的读书人。”
邵士喜直直地望着他。
白永祥说:“是给你一个右派,让他去你们班劳动改造。”
邵士喜说:“那我也不要。”
白永祥说:“不要不行。这是给你们的政治任务,你们要好好地监督他、改造他。”
邵士喜抹了脸上的汗,脸弄得更黑了,说:“不要不行,就来球吧。”
白永祥说:“你明日来领人吧。”
邵士喜说:“这个右派是谁?”
白永祥说:“刘鑫,就上月采访过你的那个记者。”
邵士喜惊得张大了嘴,说:“他咋也成了右派?真是的。”
白永祥斜了他一眼,说:“邵士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邵士喜忙干笑一声,说:“没意思。我说,这刘鑫咋这么胆大,竟敢推翻共产党。看把他兴得,他还要发表我的诗哩,他到成了右派。”
邵士喜看着刘鑫攉煤,刘鑫是个带眼镜的小白脸,攉一锹煤扶一下眼镜,擦一把脸上的汗,把白脸擦成了黑脸。
邵士喜说:“刘记者,你咋敢反党哩,你不是大学生么,书都念到狗肚子哩啦。”
刘鑫扶了一下眼镜,说:“我咋敢反党呢,我就说了一句,外行领导内行,这一句,也是他们千动员万动员,我才说得,我以为人们把我这句话早忘了,结果,他们又想起来了。”
邵士喜说:“你真是念书念到狗肚子哩啦,外行领导内行就让他领导吧,与你球相干。”
刘鑫说:“他们硬动员我说么。”
邵士喜说:“他们动员你就说,那张嘴是你的,还是人家的。”
刘鑫说:“邵师傅,你批判得对。”
邵士喜有些得意,又说:“不是我批判得对,是我爹给我说的。我还没有来这窑以前,我爹就给我说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吃不对得病咧,说不对惹祸咧,你以后记住,人长得这张嘴,主要是吃饭哩。”
刘鑫说:“邵师傅,你批判得我心里很舒服。”
邵士喜就“嗬嗬”地笑了,说:“没人了,我才跟你这么说哩。来球吧,我帮你攉吧,让你一个人攉,攉到明年也完不成任务。”
邵士喜就爬了过去。
邵士喜说:“我不能帮你攉了。昨天有人告了白主任,说我同情你这个右派。我不帮你了,我就坐在这儿看你攉。你可是快点,人家井也出了,和老婆也睡了。你看看我这劳模当得,还得陪你这个右派。”
刘鑫说:“邵师傅,你是个好人。”
邵士喜笑了。
刘鑫攉一锹煤,扶一下眼镜,擦一把汗。
邵士喜说:“你把眼镜脱球了算啦,看你,也不嫌麻烦。”
刘鑫哭丧着脸说:“一脱我就啥也看不见了。”
邵士喜说:“那你就带着吧。”
刘鑫说:“我一边攉,一边向你汇报思想行不行?”
邵士喜把腿盘了起来,仰坐在煤帮上,说:“你汇报吧。”
刘鑫开始汇报。说了几句,他便听见邵士喜的呼噜声,就不说了。
邵士喜突然醒了,说:“刘记者,你汇报,接着汇报。”
刘鑫说:“我汇报完了。”
邵士喜说:“你再汇报一遍,我还得给矿上汇报哩。”
刘鑫又说了一遍,他很快又听见邵士喜的呼噜声。
邵士喜猛地又醒了,他跳了起来,头撞在煤帮上,疼得直跺脚,刘鑫想笑,却没敢笑出来。
邵士喜揉着自己的头,说:“你说怪不怪,我梦见白主任了,白主任去我家串门了。”
邵士喜看看四周,说:“来球吧,我再帮你攉一阵吧,谁让我要你了呢。”
刘鑫说:“你千万别帮我,要不白主任又要批判你了。”
邵士喜拿着锹爬了过来,说:“你不说,我不说,谁球知道。”
刘鑫直腰的时候,从裤裆那儿掉下一本书,邵士喜看见了,说:“你掉球东西了。”
刘鑫急忙将书捡起掖进怀里,邵士喜说:“啥球东西,那么金贵?”
刘鑫说:“书。”
邵士喜就横了他一眼说:“下窑还带书,你真是个吃书虫。”
刘鑫说:“邵师傅,你千万别跟白主任说。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一天不看书,睡觉都睡不着。”
邵士喜说:“屁,我活这么大,一天书没读过,睡得也挺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