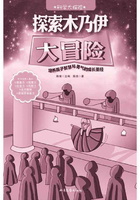7月11日,天气十分炎热。从昨天起开始拉肚子,只觉着浑身乏力。
白天找张凉席,一直躺在实验室的地板上。
阿七来找我,通知今天启程。
车票只购到三张,一行四人,我的票还没有落实。
半年前就张罗着新疆之行,本打算一人游遍全疆,调解一下近来不畅的心境。快要决定时,又冒出阿七的朋友粒粒以及粒粒的女友。想着旅程漫漫,有几个伴也未尝不好,就同意和他们一道出发。
临行前做了许多准备,托在日本的朋友购买了40卷彩色翻转片,又将仅剩的2万日元兑换成近800元人民币,这便是此行的全部费用了。
躺在地板上想着要在火车上度过三天三夜,况且由于车票没有落实,说不定要一路站着去,心里不禁有点儿发毛。
科里有两个同事家在新疆,据说每次乘火车探亲回来时腿都肿了,好几天缓不过劲儿来。健康者尚如此,我拖着病体弄不好要死在路上。
晚上8点30的火车,西安至乌鲁木齐148次。下午5点多,阿七他们便来叫我。这么热的天,连件合适的短裤都没有。匆忙之际,情急生智,把一条牛仔裤剪了半截穿上,顿时凉爽了许多。
阿七是个十分讲究的人,他本人长得就像老外,从头到脚一体名牌“耐克”。我穿一双解放鞋,自制牛仔短裤,像瘪三一样尾随在他后面。
到车站后,阿七张罗着“吊票”。转了一圈,连个硬座都没有。最后他竟然买了一张站台票塞给我,或许是拉肚子把我拉昏了头,我竟同意冒险一试,上车再说。
西安的7月份,已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室外温度40℃以上,即使不活动,浑身的汗液也不停地淌。
我背了一只很特别的通讯兵用的大背包,里面放几件内衣。除身上穿的一套四不像的短打扮外,只多带了一件灯芯绒上衣和一条牛仔裤。行李里最沉的便是我那套宝贝摄影器材和三脚架。
7点多的时候,粒粒“夫妇”出现了。同样的精神抖擞,穿戴洋气,就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
虽说头一次见面,大家倒十分热情。我比较怕生,加上身体状况不佳,只是在一旁默不作声。粒粒再三安慰我说没有关系的,他有办法解决车票问题。他告诉我,他经常是一包香烟加套近乎,诸如老乡类解决问题。这下提醒我,忆起出门时连包香烟都没带,真是糟糕透了。
晚上8点钟,随着滚滚人流像逃难似的爬上148次火车。上车后,阿七和粒粒们立即开始行动。我抱着摄影包坐在窗前,顺便给他们看行李。
两眼漫无目标地向外望着,车窗外天色渐暗,站台上依然是百年不变背大包小裹的人潮匆匆来往穿行的情景。看来无论如何人们还是有勇气向这漫长的旅途挑战的。
其实安排这次旅行是我对自己施加的压力。临行前,倒是有朋友愿意出钱赞助,我都谢绝了。我只有800元押在这里,想试一试能否实现这次圆满的旅行,即便是没车票,也就毫不犹豫地登车了。这样的开始对我并不意外,为什么不能尝试一下毫无前提、由命运安排的前程呢?
正想着,忽见站台上有人跑来冲着我喊,细细一看,原来是田儿。田儿是我的挚友,本说好要送我启程,因为有实验耽误了。
他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条已经开封的“万宝路”香烟,同时再三解释因为走得急,只好把所剩的七八盒给我带来。另外还送给我一些面包及饮料等等。
我顿时感受到一股暖流。受人照顾和体贴是人生一种额外的福分,况且我知道田儿自己的生活并不宽裕。他再三嘱咐我,路上要多加小心,“万宝路”的广告形象正好是勇猛无畏的美国西部牛仔,现在想来,田儿果然用心良苦。
正聊着,阿七几人返回车厢。田儿似乎也认得他们,非常礼貌地冲他们点点头,然后和我又聊了几句,便匆匆离去。
看着田儿离去的背影消失在站台上,内心里不由感慨万千。这些年遇到许多艰难,若不是像田儿这样众多朋友扶持,恐怕坚持不到今天。
阿七此时正与两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交涉着,不一会儿,那两人走开了。阿七来到我跟前,用平静的语气对我说已经搞到两个卧铺号!
我真是由衷地叹服他的本领,因为有了卧铺号就等于有了车票,再办手续补张票就可以了。天助我也!
火车上的第一夜睡得十分踏实。列车在黑暗中行进,中途经过哪些站我没有任何印象。
次日清晨醒来,精神恢复了许多。阿七唤我到他的下铺坐着,并拿出带来的食物4人共享。他和粒粒不光带着主食面包,还带着鸡爪和大蒜之类的零食,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有备而来,而且定是常出远门的。大蒜的味道令人不敢恭维,可是我的腹泻需要这玩意儿。大口嚼了几颗之后,就嗅不到任何异味儿了。
乘火车旅行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件大事。火车上单调乏味,长途旅行更加辛苦。如果食欲再不好,到站后等于大病一场。看着阿七他们吃得那么起劲,自然唤起了我的食欲。一顿大餐下来,顿觉精力恢复了很多。
吃罢饭漱漱口后,大家围坐一起开始甩老K。阿七不时拿粒粒“夫妇”打趣儿。我还与他们不太熟悉,只是在一旁乐着。一边玩儿的同时,大家顺便探讨此次旅行计划。既然一道行动,凡事应有分工,把任务明确一下。依据个人特长,阿七被委任为外交部长,粒粒任财务部长。我最无能,担当内务部长。粒粒女友一到乌市就回家,所以不在任命之列。
财务部长责任重大,必须掌握好钱财的使用,重大支出项目(超出10元者)必须由3位部长一致表决才能实施!而且每天要把支出情况向部委会汇报。外交部长的责任比我们两个都大得多。本着能不花钱就不花钱的原则,每日的住宿、食物、交通费用不得超过50元(其实这对于我的支付能力已经严重超标)。每人每天的食宿是硬指标,可以灵活发挥的是交通费。外交部长必须解决的是交通问题(叫交通部长或许更合适),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搭便车。还有很多细则,我一时也记不起来了。
谈话中间,阿七时常下意识地拿出一小罐精致的瓶子优雅地往两侧腋下以及临近床面喷洒,一边自己解释说那是杀虫剂。我觉得十分新鲜,欲讨来用一下,可是看上去阿七非常珍贵那玩意儿,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我只带了一小盒清凉油,略显寒酸,倒也实用。不过这是被动治疗,为了节约,我只能等虫子叮咬之后涂抹。
分工明确之后,粒粒回去与女友小聚,我和阿七对面坐着各干各的事。阿七取出日记本,很认真地在上面记着什么。我实在佩服他的细致,过去虽然相识,但仅限于认识而已,从未有太深交往。印象中他是个十分洒脱的人,虽然和我同龄依然单身闯荡,一个人独来独往。他的办公室里时常有小姑娘光顾。这不,临上车之前还与一小妹手牵手购物,把我晾在一边不知所措。他不愿住宿舍,整天就待在办公室里用一只电炉烧饭,动不动还要改善一下。我第一次去他的办公室时,见他正端一盆清水出来,见着我也不搭理,在楼道的地板上两脚站定,把水顺势往自己多毛的腿脚上一冲,大理石地面上瞬时倒映出他滑稽的身影。后来才知道这是他一贯的洗脚方式。
阿七的确有讨人喜欢的地方,不过给我的第一印象却是个行为不检点的家伙。此次一同行动倒让我不得不刷新印象,发现他其实是个心灵十分细腻的人。
我们是各怀着一份思绪登上火车的。阿七一口气写了几大篇后,表情显得越发忧郁,两只大眼飘忽而茫然若失,流露出如同粒粒所描述的“迷途羔羊”特有的那种耐人寻味的神情。
现代生活中可爱的程度往往和是否着人心疼联系在一起,有时学会表现无助本身就是力量的聚合。我似乎更明白阿七的魅力所在。
阿七停下笔对我说,他这次出来是想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寻找一种全新的感觉,他是背着一付“忧伤的担子”上路的。为了那个“她”,阿七“挂靴”两年多。可她却在近日里无情地抛弃了阿七。听着他辛酸的讲述,我内心中不由泛起同情的涟漪。但我也知道,感情这东西是外力所不能相助的,只祈望他能有一番新遇,不虚此行。
列车出兰州后,窗外的视野越来越开阔,“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这与内陆西安24小时不间断萧瑟混沌的天地形成鲜明的对比。铁路两旁的丘陵上经常可以看到一小撮一小撮聚集的羊群,仿佛挂在上面的云朵,羊儿们小心翼翼地吃着零星散布的青草。远近的田垄上,齐齐整整地排列着一个个收割后的麦垛,麦梗映着鲜亮的阳光闪闪发亮。大地的开阔和动物们的从容很容易唤起人们与生俱来的安全舒适感,那种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的开放、自由、清新,是常在都市里待着的人无法体味到的。
渐渐地视野变得无垠无际,干结平坦的地面上散漫着大小不一的石子,这大概就是常常听说过的戈壁滩了。大戈壁此时正处在一年中草木最茂盛的季节。那沁着自然之源的气息,一下子把内心中积郁多年的浊气涤荡得干干净净。
我的肚子也不闹了,一开始就令人觉得舒畅,的确是个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