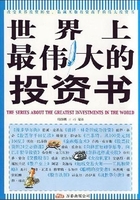大鸿为人处事心态平和,不争不抢,不慌不忙。除了男人们都有的喝酒抽烟习惯,挑不出什么毛病。一天到晚,笑弥勒似的。不紧不慢的幽默,哄的人们只是笑。所以勘查设计院上上下下,不论是大头头儿,还是小喽啰儿,都喜欢坐他开的车。一来不论遇上怎么难走的道儿,碰上什么难处理的故障,都可以放心不着怕。特别是野外勘查,都点名要大鸿开车。二来可以一路开心。还有的专为开心上他的车。他说,我年纪大,开得可是慢啊。人就说,慢才好呢,多听你说笑话儿。有什么办法呢?招人喜欢不是错。所以,上班的时候,大鸿总是很开心。
可是一下班,他就觉得空落落的,没个去处。人们大多不知道他的这个处境。只知道,他原来的老婆和他离婚了。又娶的老婆比他小十几岁。而且他取得老婆都很漂亮。这很正常,因为大鸿就是勘查设计院公认的美男子。别看现在已经55岁,依然高大挺拔,不胖不瘦,腰不弯,背不驼,脸红扑扑的。走在街上,回头率依然很高。许多年轻女孩喜欢开他的玩笑:“大鸿师傅,你没结婚多好啊,那我就可以追你了!”大鸿一乐:“别别别,你别害我回去跪搓板儿,腿脚经不住了!”
大鸿招人喜欢是真的。可他不花心也是真的。许多哥们经常揶喻他浪费资源。他笑:“资源不能随便开发。滥采滥伐破坏环境。我为保护环境作贡献,该奖励才对,你说是不是?”
大鸿对生活,对别人都没有太高的要求。少小离家,缺少家庭温暖。工作是常年玩轮子。大部分时间总觉得在动荡中忽悠。所以对一个稳定温暖的家很渴望。他常年出勤,工资不低,车补不少,单位效益好的时候,奖金也不少。多会儿发了钱都是只留几个零花钱在身上,其余的一概交给老婆保管。怎么花怎么用也不过问。除了歇班时候喜欢喝两口儿,出车时候抽点烟以外,也没什么特殊花销。在他看来,劳碌几天之后,回到家里有一个顺眼的人儿,能吃碗顺口的饭,洗个热水澡,睡个安稳觉,行了。可是先后娶了两个老婆,这会儿离这点向往是越来越远了。
也许就是这个命?可命是个啥?还不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坐在厚絧絧的草地上,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在草原上的兵团生活。要是当初不听老妈的摆布,不放弃自己初恋的女朋友,说不定这会儿就不会这么落寞了。可是也难说。谁也没长后眼,怎么能知道三十年以后的事情?说句心里话,这会儿连下一分钟要发生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唉,管他呢!骑驴看唱本儿,走着瞧吧。不知不觉,酒又下去了一瓶。兔子也吃得只剩了个脑袋和前腿了。那个算命的还说,不能吃本命所属的动物的肉。大鸿属兔,应该是不能吃兔子肉的。可那是当年在草原上打猎养成的习惯。大家都吃,他也就吃。刚回到内地那几年,很少能吃到兔子肉。没有就不吃。这几年物质丰富,商品齐全,想吃啥都可以买到。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喜欢一个人喝着酒啃兔子。好像自己把自己吃到肚子里一样。别看大鸿幽默开怀,真正心里的事情,是轻易不对人说的。
就像这结婚离婚又结婚的事儿,他可是连骨头带肉都吞在肚里,别人轻易看不出来。大鸿和第一个老婆结婚的时候25岁。姑娘23岁,属蛇。那年大鸿才从草原回到内地不久。家里人和朋友们都张罗着给介绍对象。那姑娘长得百里挑一,端庄秀丽,皮肤白里透红,很是漂亮。人们都说他俩很般配。还有的说,人要富,蛇盘兔。属相般配,好着呢。大家都说好,大鸿也觉着好,就登记结婚了。举行婚礼的时候,才发现两个家庭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处事做派,纯粹差异的离谱儿。商量操办婚礼的事儿,没一件能对卯窍。
大鸿的父母都是艺人出身,当时又是突出政治的年代,对于操办婚礼希望从简热闹就行了。姑娘的父母则是地道的城市居民。许多古老的讲究很多。像什么,见面礼,梳头礼,压箱礼,戴花儿礼,开门礼,认亲礼,送亲礼,回门礼……一大嘟噜。要说数字也不是很多。现在看也就是讨个吉利。可当时社会不让行这个。大鸿父母说,这么多,也记不住,干脆说个总数,一次给了就行了。姑娘的父母就说大鸿父母不懂礼,小看人。人还没过门儿,俩亲家先闹了一大堆意见。磕磕绊绊好不容易办完了婚礼,把相亲的那点儿高兴都磨没了。
婚后,两口子住在大鸿父母的身边。大鸿父母演艺生涯,夜做日睡。媳妇和大鸿都有工作,日出夜睡。婆媳互相影响,互相看不惯。大鸿和老父亲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好不容易等到单位分了房子,就赶紧分开住了。
分开以后,大鸿经常出车跑长途,一走好多天。老岳母常年有病,媳妇就回去住娘家照顾母亲。大鸿出车回来,妻子经常不在家。家里冷冷清清的。妻子说:你回来就到我家来,一块儿吃饭挺方便的。开始几年大鸿出车回来准是先去老岳母家。说白了,也就是奔着老婆去呗。可是老母亲不乐意,说儿子只认老岳母不认妈。这话不知怎么就传到了老岳母耳朵里,老岳母更不干了。一去就催大鸿回家。说我自己有儿子,不需要霸占人家的儿子。一来二去,大鸿觉得去哪儿都不舒坦。自己有家,干吗要去别人家找不自在?可是老婆在娘家住惯了,从不好好打理自己的家。大鸿回来,叫她,她有时也没空回来。
这使大鸿很郁闷。就从那时候开始,大鸿经常一个人喝酒啃兔子。那时候他们的女儿央央已经10岁了。到央央15岁的时候,上中专住校。大鸿夫妻基本上就各管各了。谁也懒得问谁什么事儿。回来就回来,走就走。家和住店一样。
那几年单位和社会上都时兴跳舞唱卡拉OK。大鸿受父母遗传和家庭熏陶,多少有些艺术细胞。人又聪明感觉好。加上经常跟着单位领导到处参加应酬活动,因此跳舞唱歌水平绝佳。许多喜欢跳舞的女子,专门找他做师傅。大鸿随和,教就教呗。出车回来没事的时候,就被舞迷们叫走了。
大鸿的妻子则是绝对的正统。对唱歌跳舞一类的活动深恶痛绝。这种感觉也可能与对大鸿的家庭成员有成见不无关系。她认定大鸿在外面跳舞一定是有了外遇。铁了心要离婚。其实那会儿早有人在追大鸿。但大鸿确实没动离婚的念头。让妻子这一招惹,倒也真的想离婚了。冷冰冰的日子,有什么过头呢?大不了就是一个人过。何况也不见得呢?于是就同意离婚了。
离婚的时候,大鸿觉得,好歹他们有个女儿,说把房子留给妻子吧。没想到妻子不要,说凡是留有他大鸿痕迹的东西一概不留。连结婚时买的戒指项链耳环也一样不剩地给他放下了。婆婆劝说,哪有你这么傻的女人?你就为女儿留下这些东西不行?你又不是很富裕。谁知媳妇说:“人我都不要了,东西算个啥?我看见这些东西会恶心!”大鸿这前妻真算是万里挑一的有骨气人。由此也可以看出两个人感情决裂的程度。妻子的这些做法,让大鸿很不舒服。做了十大几年夫妻,落了个让人恶心的结局。我究竟错哪儿了呢?
大鸿这里刚动议离婚,马上就有几个女人盯上了。其中一个,就是现在的妻子吕梦平。这个女人是大鸿在晨练的舞场上认识的。长相身材都和大鸿的前妻很相似。唯一不同的就是喜欢笑,一付小鸟依人的样子。舞跳得很好。说的准确一点,是跳得很默契。身体软软的,总是柔柔地贴在大鸿的身上。大鸿是男人。那年42岁。正是性情旺盛的年龄。因为和前妻闹离婚,很长时间没碰过女人了。和梦平跳舞,让他感觉很舒服。而且想入非非。梦平则是有备而来。在和大鸿跳舞之前,她已经在旁边看了好多天。并且从人们的闲聊中知道了大鸿正在闹离婚。一下子就盯上了他。
梦平是一家轻纺工厂的职工。那年29岁。有一个4岁的儿子。单位效益不好,经常被迫停工休息。丈夫是一个画画儿的,收入也不固定。而且整天蓬头垢面地钻在画室里画画儿,儿子有病也不管。夫妻经常闹矛盾。后来丈夫跟一个同行的女人相好,就抛弃梦平和儿子到外地去了。此时梦平正好离婚住在娘家。晨练的时候看到这个漂亮的男人,心里很激动。连着看了几天,就过去搭讪:“师傅你舞跳得真好,可以教教我吗?”大鸿看到这个年轻女人时,也感觉眼前一亮。打趣说:“我是瞎跳,你要不怕我把你带瞎了,就过来。”
这样两个人很快就熟悉了。闲聊中也知道了相互的情况。梦平说:“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你是我一直要找的那个人。”这样的话,大鸿在前妻的口中从来没有听到过。感觉很激动。带着梦平回到自己住的房子,梦萍进门就开始打扫。把一向凌乱的家收拾一新。开了洗衣机,给大鸿洗了一大堆脏衣服,又下厨房给大鸿做饭。把个大鸿乐得找不着北。更让大鸿着迷的是,梦平委在他的怀里,要多温柔又有多温柔,让他觉得做男人很美。没有几天,两个人就住在一起分不开了。
结婚的时候,母亲和家人出来打拦。说这女人和大鸿大象不合,那么年轻,还带着病孩子,不合适。大鸿很气恼。和前妻离婚很大原因就是母亲乱打拦。和梦平结婚的事情,他决计不准任何人干预。顶撞说:“和央央他妈倒是大象很合,怎么离婚了?人家带孩子,我不是也有央央吗?我的事情不用你们管。”不管别人怎么说,他还是和梦平像模像样地举行了婚礼。
梦平和前妻不一样,最喜欢布置家。这让大鸿很开心。他特别喜欢自己有个漂亮舒适的窝。这下可以如愿了。
婚后不久,单位新集资了房子。梦平就忙着装潢新房子。大鸿出车不在,她就自己忙活。忙前跑后几个月,房子倒是装好了,她却病了。开始以为是累着了,休息几天就会好。结果越来越严重。到医院全面一检查,是肾脏出了问题,已经出现尿毒症状。这下子抓瞎了。多年的积蓄都弄了房子。每月的工资不够梦平母子俩吃药。梦平儿子也是肾病。好像是有遗传。
肾病不能劳累。梦平什么活儿也干不了。新装的家照样还是乱七八糟。梦平倒是很想收拾。可是一劳累,病情就加重。与看病的花费比起来,豆腐折成肉价钱,横竖不值。
有了这样的病,夫妻间的床笫之欢,就更成了天方夜谭。连和前妻那会儿也不如。前妻身体很好。她只是伺候他母亲的心比照顾大鸿的心重。两口子只要在一起,妻子总还是会满足他的。想起这事儿,大鸿说不上是什么滋味。从他选择长相和前妻很相似的梦平这一点看,大鸿其实还是很在乎前妻的。
不知不觉再婚已经十几年了。梦平的病三天好,两天歹,始终没见根本好转。她自己也觉得很对不起大鸿。大鸿出车一回来,她就很歉疚地说自己拖累了他。甚至告诉他,只要他不离婚,在外面找谁她也不干涉。可从大鸿这边看,因为有病就和人家离婚,大鸿算什么人儿?守着老婆出去打野鸡,这算什么档子事儿?你说,大鸿除了喝酒啃兔子,还能干什么?
就这么想着喝着,另一瓶酒也底儿朝天了。兔子连骨头也被他吃下去了。大鸿的脑袋真正成了糨糊,怎么也清楚不起来。干脆就在草地上睡过去了。
朦胧中听见小梁子喊他:“师傅,师傅,你怎么在这儿睡着了?快点儿吧,师母昏迷了,正在医院抢救呢!”
梦平的肾透析已经不能继续再做了。这么年轻眼睁睁看着死去,大鸿不忍。如果有把握换肾成功,大鸿曾打算把房子卖掉。只要把人治好,总会有几天好日子过。可是医生说,她有先天遗传的基因,成功的希望很渺茫。所以就这么拖下来了。每次出车回来,大鸿都害怕面对梦平病危的情况。所以总要喝点儿酒,单独呆一会儿,再回去。今天喝了足有二斤多白酒,怎么也回不去了。小梁子找到他,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
梦平是算准大鸿应该在午夜时分回去的。结果等了一宿没见大鸿的人影儿,知道大鸿受不了了。她虽然一直说大鸿在外找谁也不干涉。但大鸿真的没有按时回来,她还是绝望了。精神一垮,立即就昏迷了。
大鸿跌跌撞撞跟着小梁子来到医院,急救室的门还闭着。梦平还能活过来吗?他不知道。脑子依旧一盆糨糊……
2006-9-23
15、退休女人
晚上钻被窝的时候,想到今天什么也没做,那种感觉就像守着个空桶过了一天一样,真的很糟糕。其实这一天她做了很多事情。早上起来带着孩子她姑去看病,用去三个小时。整理家里的卫生用去两个小时。上超市买东西用去两个小时。到急救中心看因为收费被打的弟弟用去两个小时。三顿饭连做带吃用去至少四个小时。看晚间新闻加天气预报用去四十分钟。还有和朋友电话唠嗑说话等等,其实是忙得不亦乐乎。可是她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什么也没做。是的,一事无成。
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了。暖暖地照着阳台。她像往常一样收拾好屋子,喝下一袋儿牛奶,吃下两块饼干,算是吃过了早餐。暂时没有什么急办的事情,就坐在阳台上静静地晒太阳。
太阳晒得挺舒服。想起村里那些赋闲的农民经常一堆一堆地摆在街上晒太阳扯闲话叨故事很有意思。可城里的太阳不能到街上去晒。只能在自己的家里晒。冬天的时候,开了窗户晒冷。关了窗户晒闷。夏天不说晒太阳,说乘凉。现在有空调了,乘凉也用不着说了。春天的太阳到野地里晒才有味道。秋天的太阳是打谷场上最好最惬意。现在那种集体的很大的打谷场已经没有了。大宗的庄稼收割时,联合收割机一步到位,机器走过,粮食就进了口袋,省事的很。可是这样一来,那打谷场上,窝在谷草里切谷穗儿的乐趣也就没有了。呵呵,干吗总是想一些过去的,已经被淘汰了的物事呢?是不是真的已经老了呢?
拿起镜子,对着窗外的阳光,仔细地看额头和两鬓冒出来的白发。又该焗头发了。电视上说总焗头发不好,容易患癌症。想起孩子她姑并没有怎么焗头发,可是已经得了癌症。焗头发和得癌症真的有关系吗?现在的事情,好像谁也说得有道理,又好像谁也是在胡说。说不说在人,信不信由己。到了儿一笔糊涂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