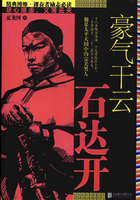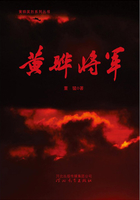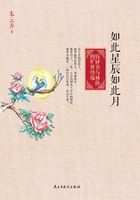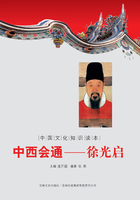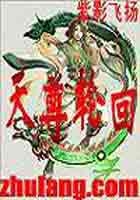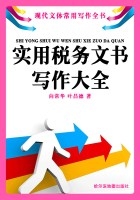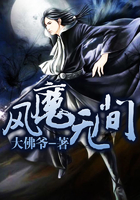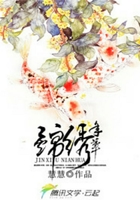事情是萧伯纳到中国访问时,鲁迅曾去拜访。而美国黑人作家休士到中国后,鲁迅却没有前去。傅在这篇文章中说道,“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鲁迅见到这篇文章后十分伤心。他认为,既然是同人,就应该更多一些了解和支持,却万万没有想到,射向自己的带有造谣和污蔑性质的冷箭正来自自己的阵营。于是,他给《文学》月刊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见萧伯纳,“是招待者邀我去的。这回的招待休士,我并未接到通知,时间地址,全不知道,怎么能到?”他说,“给我以污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并不为奇:惯了。但那是小报,是敌人。略具识见的,一看就明白。而《文学》是挂着冠冕堂皇的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为什么无端虚构事实,大加奚落,至于到这地步呢?”为此,鲁迅宣布退出《文学》月刊社。傅东华的文章虽然使鲁迅十分伤心,并且受到了鲁迅的反批评,但鲁迅并没有因此而以私害公。一九三四年后,《文学》月刊受到了反动势力的压迫,鲁迅重又为该刊撰稿,以示对困境中的《文学》以支持。由此可以看出,鲁迅虽然敏感,容易受到伤害,但绝不是一个没有气量的人。他是很能分得清应该怎么对待同志,怎么对待敌人的。
为了共同的目标,他能够放弃个人的私怨。而对傅东华本人,鲁迅更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过,他的“出手”不是予人以击,而是予人以力。一九三五年秋,傅的儿子突然患病,高烧昏迷。有人提起到北四川路底的福民医院治疗。因为鲁迅先生认识那里的院长,傅即托鲁迅先生代为联系。傅在他的《悼鲁迅先生》一文中回忆到,“鲁迅先生表示非常关切,立即在烈日灼晒之下亲自步行到医院接洽一切,并且亲自陪同院中的医生远道我家来先行诊视。进院之后,他老先生又亲自到院中去探问过数次,并且时时给以医药上和看护上必要的指导。”鲁迅在自己的日记中对此事也有记载。
日记中说,“下午傅东华待于内山书店门外,托河清来商延医视其子养浩病,即同赴福民医院请小山博士往诊,仍与河清送之回医院。”从鲁迅日记中不称傅东华为“东华”来看,先生对傅还是心有芥蒂的。既然有伤了感情的经历,鲁迅不管这事也在情理之中,能说得过去。如果要管,写封信,捎个口信,也算办了事。可鲁迅却偏偏不是这样。他办什么事都是一片赤诚,非办好不可。因而先要接洽关系,又要亲带医生去傅的家里,后又多次到医院探望。
从前的伤心事,在这时好像并不存在。傅东华在他的文章中说,“鲁迅先生对于我本人,我自己明白,是憎的成分居多,或许只有憎也说不定;然而事实已经证明,他绝不能憎我而连带憎及我的儿子;相反的,鲁迅先生之爱我的儿子,实比我自己爱他更甚。因为他的爱也是有主义的,是作为时代的儿子之一而爱的;我的爱他则只出于私情,只作为我自己的儿子而爱。”也许,傅东华是深懂鲁迅的人。鲁迅对人的爱心,以及助人的热心,容人的气量又有多少人能比及呢?
如果说傅东华和鲁迅的关系是属于同路人,但不属于朋友的话,高长虹和鲁迅的关系就有点分道扬镳的意思了。尽管他们之间曾经比一般人要密切得多。高是在一九二四年冬天的时候认识鲁迅的。后来和鲁迅一起办《莽原》,不论是工作上,还是个人的交往上,都非同一般。有人曾统计,那时的高长虹最少一星期要到鲁迅先生家去一次,有时还会更多。而鲁迅对这个有朝气,肯干事,才华横溢的青年也的确喜欢。有的书说,鲁迅曾为校对高的书稿而累得吐血。的确,鲁迅对高长虹的支持、帮助是很大的。如高的《心的探险》一书即是在高离京赴沪后,由鲁迅亲自编辑、设计、校对才出版的。
关于高鲁冲突,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一桩公案,有其复杂的历史、文化、人际关系的背景。对于此,董大中先生曾有专着细论。我要说的是,高长虹对鲁迅的误解、失望,以及后来的谩骂和群起而攻之,确实伤透了鲁迅的心。高的“骂”是真正的骂,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辩驳、批评。他的确是用了最粗俗、下流的语言来攻击鲁迅。如“世故老人、瘟臭、呕吐”等等。以至于和高在一起的向培良、尚钺等都参与其间。对高长虹们的攻击,鲁迅也写了《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等文章进行辩驳和回击。总之,通过这次冲突,高、鲁之间的个人感情是被彻底地消解了。
但是,鲁迅并没有因为他们之间的私怨就否定事实,否认高长虹和“狂飙社”在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中所作出的贡献。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写到,当时为编辑《莽原》“奔走最力者为长虹,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是被推为编辑的”。在这里,鲁迅充分肯定了高在《莽原》时期的贡献。至于自己,只说是一个编辑。而事实上,《莽原》是鲁迅发起的一个刊物,对它负有最为重要的责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为人的谦谨。对于在当时影响很大的“狂飙社”,鲁迅指出,其重要人物是高长虹。“长虹一流,便在上海设立了狂飙社。所谓狂飙运动,那草案其实是早藏在长虹的衣袋里面的,常要乘机而出。”对尚钺、向培良等,鲁迅也做了非常客观的评价。他说尚钺的小说“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其创作态度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但手段生涩。而向培良的创作不矫揉造作,内心热烈,使我们能够感到“生活的色相”,并认为向是狂飙社最重要的小说作家。可见,鲁迅是不会因一己之私情而害事实之真相的。即使是像高长虹这样的曾经严重地伤害了自己的人。
要说气量,鲁迅是我们中间最有气量的人。有谁能够像他那样遭受了许许多多的误解、攻击、谩骂而又心持平常呢?在那样的环境中,鲁迅常常遭人通缉,需要去避难。他的作品不能出版,要靠改换笔名才能发表。他不能到社会上做公开的工作,以至于生活没有保障。他遭到了太多的不平,却总是心存希望,永远保持着前进和战斗的力量。他的心中常常含有痛苦、委屈,但总是充满了对生活,对人们的博大的爱意。他曾经说过,一个也不宽恕。也许,这只是他战斗的姿态的表达,是他不屈服于黑暗和丑恶的信心。而在他的内心,是早已宽恕了人间的许许多多的对自己的误解和不公。这是智者和圣者对人间的宽恕和大爱。与他相比,我们的气量又在哪里呢?
14、鲁迅知错即改
鲁迅当然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尽管他的一生常常在辩驳、论争中度过,却从来也没有屈服、退缩。他与封建保守势力论争,与军阀黑暗势力斗争,与国民党反动统治抗争,他是一个在各种各样的争战中保持了最坚决的韧性和战斗性的真正的战士。他的所谓不屈,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对一切黑暗和反动的不屈。他的坚忍,乃是对光明和希望的满怀热情的坚忍。从斗争性来说,鲁迅确是最为坚决、最具有战斗力的。不过就做人来看,鲁迅并不是一个固执己见,背着牛头不认账的人。他虽然比较敏感,有时也可以说是多疑,但绝对是一个知错即改的人,而且从不羞羞答答。手头就有两个很好的例子。
熟悉鲁迅生活的人都知道,一九二四年的时候,鲁迅已经搬出了八道湾,住到了宫门口的西三条。有一天,一个自称是“杨树达”的青年闯入了鲁迅的家,向鲁迅要钱。他在鲁迅家里闹了半天后扬长而去。鲁迅对此人的行径十分不解,以为是自己的论敌故意派人来他的家里捣乱。于是,在当天夜里写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一文。他在文中写道:“我历来对于中国的情形,本来多已不舒服的了,但我还没有预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于用了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假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读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于这位自称为“杨树达”的青年的所谓“疯”,在内心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鲁迅觉得他不像疯子。所以就“敏感”地怀疑他为受人指使的“假疯子”。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文章发表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语丝》周刊第二期。谁知在文章还没有发表出来的时候,即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时候,就有几位同学告诉鲁迅,那天到他家的学生是一个真正的疯子,本名为杨鄂生。自那天发病闯到鲁迅家后,病就一天一天地加重起来。知道了这事的实情后,鲁迅感到非常内疚。于当天又写了《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三天后又给《语丝》的编者孙伏园写信表示自己的歉意。后来,这封信与前面的那篇文章放在一起发表。
其主要的意思是:一、承认自己的错误,知道了那天的事的确是一个神经病人所为。二、认为自己那“神经过敏的推断”意外地暴露了由自己而及于人与人之间“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三、希望杨君能够从速回复健康,并给自己表示歉意提供机会。四、表示自己的愧悔,认为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并且说道:“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由此我们看到,鲁迅不仅承认了自己的不对,而且还表示了自己内心的愧疚,并且要为自己的不慎和多疑承担责任。谈这件事要特别注意一个时间的问题。杨姓青年是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闯入鲁迅家的。鲁迅于当夜写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一文。该文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语丝》发表。但是在十一月二十日的时候,鲁迅已经知道了自己的错误,并于当夜写下了《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后交《语丝》发表。估计这时他的前一篇稿子已经难以撤回,所以作此文以更正。十一月二十四日,鲁迅又给《语丝》的编者孙伏园写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封信和“辩正”一文同时于十二月一日发表在《语丝》周刊第三期。也就是说,是紧接前一期的下一期。可见鲁迅对自己错误的纠正的急切心情。他是把这一纠正非常地当做一回事的。
如果说所谓“杨树达”事件是鲁迅在对人的问题上的差错的话,鲁迅对自己知识或者说学识上的一些错误也是乐于更正的。他有一篇着名的文章《论雷峰塔的倒掉》。这篇文章作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发表于当年十一月十七日。其中说到,“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作保叔塔,其实应该写作‘保俶塔’,是钱王的儿子造的。”雷峰塔原在杭州西湖净慈寺前面,因建在名为雷峰的小山上,通称雷峰塔。而保叔塔在西湖宝石山顶,它们虽然可能都是为吴越王钱叔所建,但保俶塔并非雷峰山上的雷峰塔。据《鲁迅全集》注释,该文最初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其中写道:“今天孙伏园来,我便将草稿给他看。他说,雷峰塔,并非就是保俶塔。那么,大约是我记错的了,然而我却确乎早知道雷峰塔下并无白娘娘。”这就是说,鲁迅在文章发表的同时,也发表了对自己文中错误的更正。奇怪的是,孙伏园到鲁迅家的时候,鲁迅让孙看的还是文章的草稿,据原附记说,那天是十一月三日。一般地说,鲁迅应该在原稿上改正自己的失误,以免自误误人。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在文后附了一段说明。也许,就鲁迅来说,写段附记比修改一下更为“方便”?还是还有其他的意义在其中?但不能否认的是,不改原文而写附记,肯定会把自己的错误、短处暴露出来。可是鲁迅却不在乎这些。他的不在乎不是坚持自己的错误,而是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并让它大白于天下。这样的勇气恐怕是世人少有的了。
15、鲁迅不言谢
知恩必报,用人必谢,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然这是就受到恩惠和得到别人帮助的人而言的。如果是反过来的话,施恩不图报,助人不求谢,当然更是品格奇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就更多的情况来说,人们还是希望施之与人当有所回报的。更有那世故无比的人,只要给别人做了一点点好事,就时刻挂在嘴上,唯恐人们不知道,使那得到了帮助了的人欠下了永远也还不完的人情债,他的这一点善行也就在世故的绳索中变成了讨债的账单。最近读了一些关于鲁迅的书,发现鲁迅正是一个不言谢、不图报的人。这里且举几件事例来说明。
鲁迅在上海的时候,曾和傅东华等一起编《文学》月刊,过从较多。一九三五年的秋天,傅的儿子高烧发病,以至昏迷。因为鲁迅与当时北四川路福民医院的院长认识,所以傅托鲁迅代为联系。鲁迅对此事非常重视,步行到医院接洽,又陪同大夫到傅东华家给孩子看病。孩子住院后,他又多次到医院探望,可以说关怀备至。傅东华的儿子病愈出院后,傅曾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说儿子庆得更生,全仗他的力。所以请鲁迅指定日期,将带儿子登门道谢。当时鲁迅住在北四川路的大陆新村。因为他在国民党的通缉中,所以很少与人在家中见面。一般的联系都是通过附近的内山书店转达。傅不便贸然上门,故先写信联系。但鲁迅并没有给傅回信,也就是说他不愿让人对他的帮助表达谢意。而傅东华也就始终没有带孩子去鲁迅家道谢。
给别人联系医院,或者帮别人联系出版和发表文章、着作,这样的事鲁迅一生不知办了多少。他是从不求谢的。如果说这还只是出出力的话,那么,他常常给别人以经济上的帮助,也是同样不言谢的。三十年代初,葛琴还是一个文学青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一九三三年的时候,她把自己写的小说编成一个集子,准备出版,并请鲁迅先生为书作序。鲁迅很快就把写好的序交给了葛琴,而且把自己当天得到的稿费一百元借给她。葛琴在自己的回忆中说,“他很关切的询问我的生活状况,又对于我的私人事件上做了一次难忘的帮助。”这里的所谓帮助即指鲁迅借钱给她。当时,鲁迅的生活也很紧张。他的文章很难公开发表,书也常常不能公开出版。许多文章是给同人报刊写的,并没有稿费。但当他知道了葛琴的生活很困难时,便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稿费“借”给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