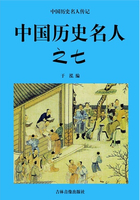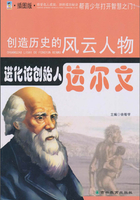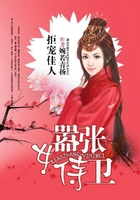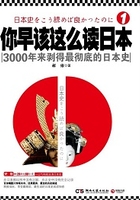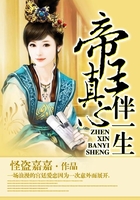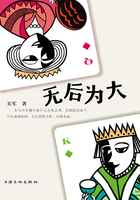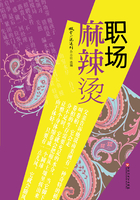大概是在鲁迅十三四岁的时候,周家发生了巨变。先是他的祖父因科场案入狱,后是他的父亲病重乃至去世,家里失去了支柱。从此,作为长子的鲁迅就开始了一段与母亲相依为命的艰苦生涯。也许是作为长子,遭受了许多的白眼和难堪,因而鲁迅也就十分理解母亲的不易。所以在许多事情上,主要是生活方面,鲁迅是不愿意违逆母亲的。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自己婚姻的态度。他在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后,当然不愿意走旧式的无爱的婚姻。但因为这一婚姻是母亲所订,他就只好牺牲自己,作出妥协,为母亲娶了一位儿媳,权当是母亲送给自己的一件礼物。而这妥协的结果是造成了他和朱安两人在感情和婚姻上的悲剧。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母爱如同湿棉袄,脱了感到冷,穿着感到难受。这的确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感受。当然,对没有接受正式教育,对新的思想和观念毫无了解和认同的鲁瑞来说,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和承认自己儿子的事业和劳动,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在思想和观念上,鲁迅和他的母亲的确是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的。
但是,思想上的隔膜并不能使他们的母子之情隔断,鲁迅对母亲尽了自己最大的责任。
鲁迅是一九一二年随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的。行前曾返绍兴安顿家事,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安排好自己母亲的生活。到北京后,他住在绍兴会馆,过着独居在外的生活。后来,周作人也应邀到北大任教。就经济而言,鲁迅,包括周作人,是周家的顶梁柱。绍兴老家只留下了他们的母亲和三弟。所以到了一九一九年,鲁迅便买了八道湾的住宅,自己亲自动手设计、整修房屋,又回到绍兴把老母及全家都接到了北京。那一年,鲁迅的母亲已经六十了。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六年鲁迅离京南下的不到十年间,是鲁迅侍母最突出的时期。此前,或者因为年幼,或者求学远游,或者在外地为生计而忙碌,鲁迅总是不在母亲的身边。而经过了多少的离别,终于全家生活在一起,这一点对鲁迅来说是十分高兴的。
鲁瑞女士虽然没有受过正轨的教育,但却能识文断字。据曾经长期在周家帮忙的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认得字很多,但是不大会写。曾经教他识字,学诸如《实用杂字》等入门读物,并且给他讲《水浒传》、《西厢记》等,使王鹤照懂得了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后来竟能记账、读书。到了北京后,鲁老太太有了更多的时间看小说,鲁迅便常常为她买书。鲁迅曾对荆有麟说:“因为老太太要看书,我不得不到处收集小说,又因为老太太记性好,改头换面的东西,她一看,就讲出来:说与什么书是相同的,使我晓得许多书的来源同改装。”到了上海以后,鲁迅不在母亲的身边,便从上海买了之后邮寄到北京。
一九二三年,周氏兄弟失和,鲁迅从八道湾迁出,借居到砖塔院。先是他带着朱安借居。但是鲁老太太在八道湾并不痛快,常常弄到没有饭吃的地步。据王鹤照回忆,鲁老太太曾劝王离开八道湾,说“还是离开这里好,免得受闲气。”可见周作人夫妇的确是容不得人的。鲁迅见母亲在八道湾处处受制,便借钱买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子接母亲来同住。虽然工作忙,他总要抽空与老太太坐坐聊天。他们母子间谈些什么,现在已难以索考,但首先,日常家务肯定是少不了的。在八道湾的时候,先是鲁老太太主家,后来是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管事。
鲁迅除了往家里交钱外,可以说是不管家事的。到了西三条,家里只有他们三人。人少了,但家事还是要商量的。另外,讨论鲁老太太所读的书也应该是经常的话题。据荆有麟说,鲁迅做中国小说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鲁迅为自己的母亲多方收求小说话本,对这些东西有了许多具体的了解。这应该是他们之间经常的话题了。此外,据周作人讲,鲁老太太移居北京后,开始看报,“日备大小报纸两三份,看了之后与家人好谈时事,对于段张冯蒋诸人都有批评。”那么母子俩在一起谈谈时事也是很有可能的。鲁迅在领了薪水之后,也常常买一些点心什么的东西拿回来,让家人改善改善口味。他总是先把点心送到母亲的房间,请鲁老太太选用,然后再送到朱安女士的房间,请朱安选用,剩下的拿到自己的房间。在鲁老太太的房间里,一年四季都备有点心什么的零星食品,这些大都是鲁迅在街上购买的。
据王鹤照说,当年鲁迅返绍兴接全家北上,一路上鲁迅让老太太坐卧车,自己坐二等车。到了南京,刚刚在旅馆住下,鲁迅就到外面买了南京有名的小吃肴肉和羊膏请老太太吃。一九二六年,鲁迅被章士钊解任,又遭到军阀政府的通缉,只得南下谋生,辗转来到上海。不在北京,不能亲侍母亲,但他对自己的家还是挂念万般。除了经济上的负担外,常常写信寄书。他曾两次返平,均为探望母亲的病况。
虽然鲁迅在生活上对自己的母亲十分关照,但并不能说他们母子之间在思想上就非常认同。事实是他们在思想上还存在着非常大的距离。鲁老太太爱读小说,却不喜欢“鲁迅”的作品。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的《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女士曾将《呐喊》送给鲁老太太看,而且告诉她《故乡》一篇最好。可是鲁老太太读完这篇小说后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所以荆有麟说,在思想上,母子是相离太远了。但先生对于家事,多半还是依了老太太的主张。鲁迅曾对荆说过,“她们的成见,比什么都深,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顶多只能改变十之一二,但没有多少时候,仍旧复原了。你若再想改革,那他们简直不得了。真没办法。”但是,思想上的距离并没有影响鲁迅对母亲在生活上的关心。他对自己的母亲尽了一个儿子应尽的孝心。
12、鲁迅的绰号
鲁迅先生的笔名是很多的。着名的如巴人,是他发表《阿Q正传》时所用。又如唐俟、何家干、封余、晏之敖、隋洛文、阿二等等。仅《鲁迅全集》所收,就有一百一十多个,而且据说这还不是全部,有人认为,鲁迅先生的笔名有一百六十多个。但是对于先生的“绰号”,恐怕知之者甚少。关于绰号,据许寿裳先生说,鲁迅自己就是很爱给别人起绰号的。比如在日本留学时,曾受业于章太炎先生门下。那时一同听讲的有许寿裳、周氏兄弟以及钱玄同等八人。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讨论。而每每此时,钱玄同最为活跃,一边说话,一边爬来爬去。所以鲁迅就给钱起了一个绰号叫“爬来爬去”。严复是二十世纪初最着盛名的翻译家。他译《天演论》,自称“达旨”。而鲁迅亦特别称道他的功力,所以给严复一个轻松的绰号叫“不佞”。当时一位着名的维新人物蒋智由,有一次谈到服装问题,说清朝的红缨帽有威仪,而西式礼帽则无威仪。于是鲁迅便给他也起了绰号叫“无威仪”。鲁迅给人起绰号,总是事出有因,一般来说充满善意。这从一个细小的方面可以看出他做人的风趣和幽默。
说鲁迅的绰号容易使人联想起一些鲁迅的论敌对他的攻击,以及因此而进行的谩骂式的称谓。如“世故老人”,大概高长虹就这么指称过鲁迅。鲁迅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深刻当然没人能比,但在做人和处事上实在是单纯甚至幼稚得厉害。说他“世故”,真有些风马牛不相及。至于“堕落文人”则是国民党的通缉令中所称。不知为什么鲁迅一生生命不止,奋斗不息,而国民党却说他“堕落”,也许实在是找不出更好的罪名,只好以“堕落”来侮辱他,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只是这样的罪名显得过于拙劣。当然,这种带有人身攻击和诋毁、侮辱性质的东西,与我们所说的绰号是截然不同的。
鲁迅比较早的一个绰号是“富士山”。据沈瓞民在《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一文中所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对大清帝国的留学生不求上进、不学无术的现象十分不满,因而对他们的衣着打扮也很看不惯。特别是对那些留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把学生制服中的帽子顶得高高耸起的样子感到十分滑稽,所以称他们是“形成了一座富士山”。这样的内容,鲁迅在他的《藤野先生》中有很生动的描写。但沈瓞民说,在日时,鲁迅即常常和他们说起,“大家听到他描摹留学生盘在顶的丑态形如‘富士山’时,都不忍喷饭。我有一位同学王立才,为人风趣……就因此叫鲁迅为‘富士山’,‘富士山’的诨名,在同学中传得相当广,当时这诨名传开的原因,还因为富士山原蕴藏着火山,很能象征鲁迅革命斗争的精神。”沈早年与鲁迅一道留学日本,并且同住一个宿舍,他之所言,应该说是可靠的。
一九零九年,鲁迅由日返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新任学监夏震武无礼于教师,引起学校教师的强烈不满,要夏辞职,并且终于获得成功。因夏氏不明时务,木然逞强,鲁迅等一般教师皆呼夏为“木瓜”。夏辞职后,鲁迅、许寿裳等二十余人曾为纪念合影一张。当时的参与者张宗祥称此次行动为“木瓜之役”。后来,凡在这张照片上的人,相遇都互称“木瓜”。鲁迅当然也被这些同志戏称为“周木瓜”。
沈尹默在《鲁迅生活的一节》中提到鲁迅的另一个绰号即“猫头鹰”。他说“有人替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猫头鹰。这个鸟和壁虎,鲁迅对于它们都不甚讨厌,实际上,毋宁说还有点喜欢它,这个替鲁迅起绰号的人,大约是了解这种情况的,恐怕就是钱玄同这类的熟朋友作的怪吧?”沈氏在别的地方也提到了这件事。他在《忆鲁迅》一文中写道:“豫才的话不甚多,但是每句都有力量,有时候要笑一两声,他的笑声是很够引人注意的。玄同形容他神似猫头鹰,这正是他不言不笑时凝寂的写真。”说鲁迅神似猫头鹰,应该说比喻得非常准确。他似乎是这样的人,时刻准备着,与一切的黑暗、丑恶、不公作斗争,而且迅猛有力,一针见血,决不犹豫。
说一个人的绰号,也许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我以为从这样一个小小的侧面,也可以使我们了解一位伟人,了解他的精神、情操,为人和品性。这样来看,也许就是很有意义的了。
13、鲁迅的气量
在许多人眼中,鲁迅是一个爱走极端的人。他敏感,易怒,不饶人。还有人以为他是一个十分爱骂人的人。连他的母亲在给他辩解时也说,鲁迅是被人逼急了的时候才骂人的。鲁老夫人对自己儿子的了解究竟有多少,我们还不敢持过于乐观的意见,仅从她的这种辩解中也就可以看出她对鲁迅的不了解。当然也有许多人认为鲁迅是个锱铢必较的人,直到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还说要一个也不宽恕。由此种种来看,鲁迅似乎是一个褊狭、记仇、气量很小的人。然而其实大大地不然。所有这些理解都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事实上鲁迅的气量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
冯雪峰在他对鲁迅的回忆中,曾谈到了他和鲁迅的交往。一九二八年的十一月间,冯雪峰因被国民党通缉,从家乡来到了上海,和他的同学柔石来往密切。这时冯、鲁还不认识,但相互知道。柔石告诉冯雪峰,鲁迅对他写的一篇叫做《革命与知识阶级》的文章很反感。事情的起因是,在当年创造社和鲁迅的论争中,创造社的人认为鲁迅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冯雪峰虽然感到了创造社的小集团主义和宗派思想,但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鲁迅的革命性。所以他的文章替鲁迅辩护,说鲁迅只是不革命,而绝对不是反革命,并且认为鲁迅对革命是无害的,是所谓的“同路人”。加上冯文在态度上的轻浮,鲁迅当然不高兴。不过柔石也对鲁迅做了解释,认为冯的文章旨在批评创造社的小集团主义,鲁迅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不说什么,并不等于没什么。
对一般人来说确是如此。但对鲁迅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柔石和鲁迅住得比较近,私人关系好,所以他常常到鲁迅的家里,也曾谈到了冯雪峰。这时的鲁迅似乎逐渐对冯有了一些了解,并肯定冯翻译日本升曙梦介绍苏联文学和艺术的书,对中国的文艺界是有好处的。鲁迅还让柔石给冯带了一本日本文译本的关于辩证法的书,并说,“你去送你那个同学去吧,省得他再买了。”
由此开始,冯雪峰说他改变了过去对鲁迅先生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他说,“由于我自己的一些片面的印象和主观的偏见,我以前是并没有应有地尊敬鲁迅先生的。我从前在北京时凭我自己的片面的印象所构成的鲁迅先生的性格,就和柔石所说的很不相同。”“在柔石的心目中,鲁迅先生简直就是他的一个慈爱的塾师,或甚至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柔石是经常和鲁迅来往的人,因而他对鲁迅的了解是非常直接、具体的。
而冯雪峰则主要靠的是间接的了解和印象。问题就出在这印象上,对鲁迅的偏见也来自这所谓的“印象”。随着冯雪峰和鲁迅之间的接触,两人终于结成了终身的友谊。这友谊的成功,与鲁迅对一个青年人的“大气量”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鲁迅在了解了冯雪峰后,就不再计较冯对自己的误解。后来他们在一起办刊物,讨论社会、文学,常常通宵达旦。鲁迅去世后,冯又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秘密参与了鲁迅先生后事的安排。他们两人之间,可以说既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情趣相投的朋友。
如果说鲁迅对冯雪峰是在逐渐了解之后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并忘记了过去曾经有过的不愉快的话,鲁迅和傅东华则是属于另外一种情况。
即有共同的目的、共同的事业,却不一定有良好的私人感情。尽管如此,鲁迅也给了傅以极大的帮助。傅东华是浙江金华人,一九三零年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等学校任教授。一九三三年起,任同人文学刊物《文学》月刊的编辑。当时鲁迅先生是该刊的同人,为该刊撰稿。但是,傅东华在《文学》月刊的第一卷第二期却发表了一篇《休士在中国》的文章,涉及到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