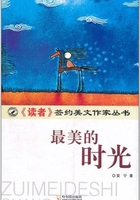芳草见母亲一颗接一颗地吸烟,满屋浓烟缭绕,不知她心里在想什么。莫非,她在以吸烟的方式排解心中的感伤与不舍?还是别的什么?大概,只有做了母亲的人,才知道即将与女儿天各一方,是何种感受!
平日,芳草曾记恨过母亲。分别之际,她反而对母亲充满眷恋和不舍,恨不得让母亲再痛打自己一顿。望着张文华孤单的身影,满面的沧桑,还有她郁郁寡欢的满面愁容,一股天高地厚的恩情,漫过芳草的躯体,在她周身涌动。芳草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背过脸去,拭一把早已模糊的泪眼,尽力使自己的情绪保持平静。她心里顿悟:母亲是个多么刚强的女人!她从不轻易落一滴眼泪。自父亲去世,在那动荡而冷峻的年代,她独自支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不辞辛劳,忍辱负重,艰难而顽强地生活。她有一肚子话,无处倾诉,有满腹苦楚,无处宣泄。她只好把一腔委屈宣泄在孩子身上。这些,未必是她所情愿。在离别的时刻,张文华眼望自己倔强、不服输的女儿就要离开自己,远嫁他乡,天南地北,相见无日,肯定别有一番感触在心头!
芳兰在一旁急着催促:“快点,咱们赶紧走吧,不然就误车了!早晚得走,还是早走时间打出点富余好。”
芳草偷眼望了望张文华,又自顾自地坐在炕沿上没动,也没说话,她眼里滚动着伤心、难过、不舍的泪水。心想谦和生性懒惰,不爱干活,家里家外,都要母亲操心受累。我走了,我干的那部分活计,谁来操持?母亲肩上的担子,可想而知,更重了。母亲,你活得好累,好苦!芳草心里缠缠绵绵,凄凄切切。
“走吧走吧,赶紧走吧!”芳兰和淑琴上前拽住芳草的手。
芳草喉管里,有一团热辣辣的东西,猛烈地冲向喉头口,她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哇”地一声,芳草嚎啕大哭。离别母亲,芳草的生身之母,世界上最亲的亲人。此时此刻,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只有泪水,比任何语言都热、都纯、都真、都厚。上天,你可知道,此刻的芳草,她要把对母亲的眷恋和歉疚,一并哭出来。把20几年受的委屈和忧伤,发泄出来。她的内心,隐隐也在为自己迷茫的前途和未知的命运,而哭泣!
淑琴拉着芳草的手,红着眼圈道:“走吧,不然,真的晚了,火车不等咱们。你们结婚以后,和杨茂森一起,回来一趟,让我们大家伙都看看杨茂森长得啥样。”
芳草大声哭泣。内心,缠绵悱恻,不能自己。她想上前拥抱住自己的母亲,眷眷地说一声:“妈,我走了。感谢你的养育之恩,过去,女儿竟惹你生气,原谅我,妈妈!你多保重,女儿一有空儿,就回来看你。”
然而,芳草没有那样做。历来,她就恐惧张文华那张威严的脸。她只怯怯地说了句:“妈,我走了。”
一边走,芳草一边哭,一直哭到火车站。坐在列车上,芳草的脸贴着玻璃窗,望着车窗外,窗外的景色亲切得使她再一次潸然泪下。窗外那片热土,是她生长、生活了23年的地方,她多想跳下车去,亲吻一下自己熟悉的热土!望着那片自己熟悉的土地,望着像流星一样,在她视野里,一闪而过的树木、村庄和学生时代曾经与同学们一起去高山台栽的早已果实累累的苹果树,芳草的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像泛滥的洪水,像奔腾的江河。甚至,脚下的铁轨,她也倍感亲切。她曾无数次从铁轨和火车之间钻来钻去,还曾趴在上面,不肯起来!芳草在心里呐喊:铁轨,我爱你!铁轨啊,你给了我太深刻、太沉重的回忆!
铁轨的另一端,有一双手,他要把芳草接向未来。未来,令她恐惧。未来,也令她向往!
列车啊,你快些跑,快快把我载向美好的未来。列车,你慢些走吧,我要把这熟悉的景色,记在心怀。再见了,亲人!再见了,家乡!芳草心里,翻江倒海!
芳草离开那个家,满腔热情地走向这个家——杨茂森的家。她不会想到,自己怀着一颗滚烫的心,来与杨茂森结合,却没能立刻举行婚礼。还像上次一样,杨茂森赖在芳草住的小屋,不肯离去,他试图以肢体行为走捷径,这是他及全家人的意图。为了减免经济开支,糊里糊涂“睡了觉”就算结婚了!芳草心里,愈来愈清醒,愈来愈没了主张。善解人意的芳草,虽然理解杨茂森全家,而来时的热情,一落千丈。
芳草在杨茂森家的一举一动,都有眼线监视,她实实在在被困在杨茂森家了。芳草开始后悔。而她,年纪轻轻,单枪匹马,走,是走不成的,她一度束手无策,左右为难。而芳草聪明,坚决,倔强,任性。在她的执拗坚持下,杨茂森家只好答应先领证,之后,可以给芳草400元钱买几身衣服。然后,准备办喜事。
杨茂森没有一件象样衣裳,他说他结婚典礼时,穿已漏脚趾的旧黄胶鞋,再和别人借一身衣服,与芳草拜堂成亲。芳草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如此“成亲”,婆婆家的人说她嫌贫爱富。芳草心想说我嫌贫也好,说我爱富也罢。反正,结婚得像个结婚的样子。她用给自己买婚服的钱,给杨茂森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又买了枕巾枕套、洗漱用具,还讨好地给全家每人买一双袜子。她想人的一生,正常情况,只结一次婚。再怎么说,也得过得去!即便婚后用汗水来偿还,结婚,也要像个结婚的样儿!为了这种思想,芳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全家老少为此事,对她产生了沟壑。这一沟壑,纵横在全家人心里,许多年不能平复。由此,芳草背了多年“嫌贫爱富”的“美名”!
终于,芳草与杨茂森,面朝八仙桌上的白面馒头,拜堂成亲三鞠躬了。边鞠躬,芳草心里边想北京人结婚,为何向白面馒头三鞠躬?莫非,是想借此神圣之机,乞求上苍永远赐予我们食物,赐予我们白面馒头?
那是一个无丝毫喜庆色彩的婚礼,所有的地方不见一个红喜字,新郎新娘身上,无一丝代表幸福吉祥、红花、红字之类的东西。每个人的脸上,更无一丝添人进口的喜庆笑容。只有八仙桌上的10几个馒头,和杨茂森、芳草的三鞠躬,证明他们正在举行结婚盛典!没有誓言,没有承诺,没有拥抱,没有亲吻,没有一丝快乐的心情,他们就这样结合了!
洞房花烛,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而成了新娘子的芳草,望着贪杯而脸色通红、像猪一样鼾睡着的新郎,委实使她望而却步。芳草不敢在洞房多停留,悄悄来到室外,独自在外面徘徊了一夜。她的梦,她的人生新篇章,就此展开了!
拂晓,芳草忐忑不安地走进洞房,坐在炕沿上。杨茂森酒力已过,他睁开惺忪的睡眼,二人四目相视,他们各有窘态默默相望,彼此相对无言。杨茂森未说话拽了芳草一把,芳草本能地抗拒没有动。花烛之夜,如此过去。这事,成了日后杨茂森与芳草发生摩擦的话柄。想一想,杨茂森有道理。洞房花烛,理应交合,古往今来,大多如此。但,对于芳草这个骨子里一向追求浪漫的人,与一个理想、志向、语言、思想认识、情趣爱好、生活习性,一切尚未达到统一,而且,只见两次面并不了解之人,发生两性关系,那真叫难,难于上青天!芳草知道杨茂森是喜欢自己的,是那种偏僻而闭塞的农村,土得掉渣的庄稼汉,一见到女人就喜欢的那种喜欢,而非实质的更深层次的情爱。这种意义的喜欢,芳草有能力、有魅力,让所有的庄稼汉都喜欢!接连3日,悄无声息,安安静静。第4日夜,芳草继续重复前几日的话:“不行,我例假还没过去。”
杨茂森早已忍耐不住,他面带怒色,说道:“我倒想看看,到底过没过去!”他边说,边动手……
“杨茂森,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咱们商量好了,再做不迟。”芳草用被子紧紧裹住自己的身体,红着脸对杨茂森说。
“商量什么?你说。”杨茂森面无表情,声音不大。
“我想,咱们刚成家,生活境况一定艰难,咱们没有心理准备和足够的经济基础,肯定没有能力抚养孩子。”芳草目光呆滞,突然,她望见顶棚上,不知是哪位有情调的人粘贴的唯一一张有喜庆色彩的红色剪纸花,她长出一口气,娓娓地说:“我觉得咱们应该齐心协力先把日子过好,等以后有了经济能力,再要孩子。如果,我们有了孩子,一定让孩子过最好的生活,上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我想,我想先避孕。”
嗫嗫嚅嚅地把话说完,芳草的双眼,依然不忍离开那张漂亮的红色剪纸花。她双目迷茫,满脑子浪漫主义幻想和罗曼蒂克思维。因为她也算是个文学青年。至少,她是半个文学青年,抑或是半个的半个。尽管,她没读多少书。尽管,她还没能弄懂婚姻在传统文化或现实文化中,充斥着语言交流、性爱、沟通、相互吸引之类的内容,而她冥冥之中感觉到,如此交合,不叫性爱,只叫性交。
“我哥像我这般大,都有两个孩子了,我都27岁了才结婚,你还不要孩子,这不行。”
芳草含蓄中有一份矜持,柔和中有一份刚烈,幻想中保持着极大的冷静。“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明白,不是我不要孩子,是现在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心理准备,我只想晚要几年,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行么?”。
“我没听说过,生孩子,还要有准备!我们这边的人,结了婚,就要孩子。我们村儿,有好几个媳妇还先怀孕,后结婚呢。我也没看人家做什么准备。”
怪不得你婚前想和我耍花招,我就知道你们的目的不纯,想先斩后奏。哼!到底看错了人!芳草心里骂。
“那你看着办吧,反正,我先不要孩子,你也别和我做那种事。”芳草边说,边把头缩进了被窝。她感觉超越一些话题谈孩子,总不那么光彩,不那么自然。因为,他们一直未到谈孩子的程度。芳草羞涩而恐惧。她嘴上说着不配合的话,心里,却无一丝底气。她深知,结婚证都领了,堂也拜了,婚也结了,自己还能怎样?拖得了今天,能奈何得了明天么?对她而言,结婚证就是性行为的通行证!杨茂森用手举着它,向她实施暴力,并义正辞严地大声说:“告诉你,任你怎样不情愿,我都是合法的!”芳草都没有脾气,她还敢有什么脾气?
还好,杨茂森终于想通了。他不情愿地说道:“那你说,怎样避孕?”
芳草欣喜而羞涩,她探出头,忸忸怩怩道:“有一天,我在大姐家衣柜里找东西,发现了一个盒子,盒子里装许多避孕套。一开始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还以为是气球。后来,看了盒上的说明,我才知道,便偷偷拿了一些。”
芳草神秘兮兮、不自然地把话说完,用被子又蒙住了脸。好像新婚行房,变成了向陌生人提某种先决条件的筹码,她又窘、又羞、又惶悚!
“那就用避孕套。”矜持片刻,杨茂森讪讪的说。他僵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二人一番“讨价还价”,勉强达成了协议。
上天知道,他们在谈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是怎样的一对夫妻?!芳草迟迟不能如杨茂森之愿,都到这会儿了,她还在做梦!芳草梦想保住自己的贞操,有一天她好把它完整地献给自己的梦中情人。内心深处,她总觉得自己不该是眼前这个男人的媳妇。她犹豫着,矜持着,心神不定,迟迟疑疑。眼前,像弥漫了一层薄雾,根本看不清连她自己在内的两个人,究竟在干什么!也完全进入不了与杨茂森那次接吻的状态。自那次心动,见到杨茂森,芳草再也没有心动过。
自己就要告别女孩,变成女人了!芳草心里酸酸涩涩,没有一丝即将与异性交合的欣喜和好奇,完全被不安、恐惧、惋惜和担忧,所包围。她问自己:“你爱他吗?他是怎样的人?这个大家庭每个人都是怎样的性格?你能否做个好媳妇?他们能否友好地对待你?如果不能,你该怎么办?”芳草想到这里,刚刚谈到的“避孕”,似乎有了更深层的意义。
被窝很闷,芳草探出头,目光呆滞,她望了望顶棚那张剪纸花,深吸一口气,向四周瞥视一眼,又把头缩回被子里。她的心,抖的厉害。
“你怎么了?”杨茂森茫然不解并急不可奈,他问。
“我怕。”
“你怕什么?”
“我什么都怕!”芳草哭了,哭得可怜兮兮。
“行了,你不用怕,不会有事的。”杨茂森笨手笨脚,红着脸,终于,他如火山一样爆发了。像个骑士,更像一头笨猪。这是他的第一次,也是她的第一次,在他27岁过去一个月,她即将24岁的时候,他把她造就成一个女人。
他们新婚的炕上,铺着个黑网套。黑网套是家人用了几十年的棉花套重新又弹了弹,地位陡然升级,升级成了芳草新婚的“新”铺盖。黑网套上面,躺着对新生活充满幻想的新娘子芳草。
那一晚,杨茂森紧绷面孔爬上爬下,他笨手笨脚,自己忙的不亦乐乎。芳草像一片沉默中荒凉而贫瘠的土地,任由这个刚刚上阵、且浑身散发着土气味的农夫羞赧地耕耘着……她一声不吭,睁着畏惧、惶恐的双眸,望着陌生的杨茂森,心里七上八下,苦苦哀鸣,泪,如雨……
如果是非常了解、非常相爱的新婚夫妇,首次的身体交融,一定似仙似神,欲仙欲死。彼此双方一定会热烈地给予和疯狂地占有,像迎接天神到来一样燃烧生命中沉睡已久的激情,无比激动好奇、无比幸福快乐地走进身体的迷宫,坠入内心狂喜狂欢的美妙境界,像到达九重云霄一样兴奋和迷醉。
如果是两情相悦、情投意合的自然夫妇,燕尔新婚,他们一定会回到亘古洪荒那久远的年代,做一个反璞归真的自然人,把美妙绝伦的男欢女爱做得尽善尽美,发挥得淋漓尽致。当岩浆冲出地面,他们一定忘乎所以。当女人望着心仪已久的男人赠予她的玉液琼浆、当男人望着自己心爱的女人美丽的芳容,彼此二人一定会飘飘然……
人,有血有肉,有爱有欲,一双爱恋的人一定不会掩饰自己,他们一定会尽情地爱。这是人类最原始、最真实的情与爱,为什么要掩饰?而芳草在掩饰。她上穿一件线衣,像一根僵硬的木头,僵直地躺在黑网套上,双眸停滞,面无表情,更没有活力和激情,只是在无助而难为情地默默迎受。说到底,她对他很陌生,感觉像与不认识的人在做爱!芳草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地流淌。那泪,有惋惜、有遗憾、有不舍,交织在一起,搅动着她那颗追求真爱的心!
不知是避孕套型号不符,还是杨茂森在耍小聪明,首次交合,就失败了。尽管,以后每次都用那玩意儿,芳草还是怀孕了。制造生命,实在是世界上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不用技术,不用文化,无论懒汉懦夫、阿飞混混,无论男女双方有否感情,任何情况的交合,有意无意,谁都能制造出生命。尽管,生命是神圣而至高无上的;尽管,制造生命的人对生命的认识很浮浅,对保护生命的责任和义务的认识很模糊。
孕育生命是女人最得意、最伟大的壮举。而处在被动中的芳草,却无一丝欣喜。她得知这一情况,只有不安和沮丧。这与杨茂森的心情似乎相反,杨茂森虽然没显出多高兴,而他肯定不沮丧。芳草把所有的避孕套,用剪刀剪的稀巴烂。从那一刻,芳草才深切领会“生米已做成熟饭”的深刻含义。
这一日,芳兰来信了,信上说:“……自你走后,母亲每天都在念叨你,她非常想念你,希望你和杨茂森能回家一趟。那晚你走后,母亲哭了一宿。哥哥也流着泪说他对不起你……”
一股酸楚,涌上心头。过去了,该过去的,都过去了。该来的,也来了。一切,都是命!人,不能和命争!